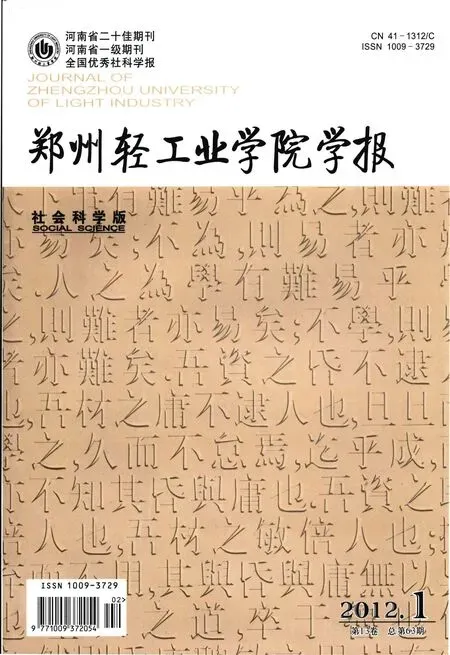論國族-國家的憲法與宗教
吳禮寧
(華北水利水電學院法學院,河南鄭州450011)
“國族-國家”一詞是從英文nation-station翻譯過來的,用來指稱與傳統(tǒng)國家相對應(yīng)的現(xiàn)代國家,特別指向在歐洲近代革命基礎(chǔ)上建立起來的近代化或現(xiàn)代化國家,它是當今世界一種普遍的政治組織形式。國內(nèi)學者多將其表述為“民族-國家”,然而這一表述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nation-station的本意,并容易引起歧義而將其等同于中心民族或單個民族的國家。事實上,state或nation-station本身已經(jīng)超出了民族的范疇,并指向了國際法意義上的國家。因此,本文采用“國族-國家”概念。
國族-國家是用來描述現(xiàn)代國家及其政治文化的關(guān)鍵詞語,國族意識是其文化基礎(chǔ),世俗化是其主要特點,而憲法則是其合法性基礎(chǔ)。英國思想家托馬斯·潘恩將憲法定位為“政治圣經(jīng)”和社會團體的章程。他認為:“憲法是一樣先于政府的東西,而政府只是憲法的產(chǎn)物。一國的憲法不是其政府的決議,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決議。”[1]從歷史經(jīng)驗來看,憲法也恰恰是現(xiàn)代國族-國家得以建立的基礎(chǔ),尤其是西歐,其國族-國家的建構(gòu)過程正是世俗政權(quán)合法性基礎(chǔ)由教會轉(zhuǎn)移為憲法的過程。國族-國家的形成及現(xiàn)代憲法的誕生不僅標志著現(xiàn)代國家政權(quán)世俗化的實現(xiàn),還標志著政教關(guān)系的根本性變革,并且決定了政教關(guān)系的歷史走向。
在現(xiàn)代社會,建立在憲法基礎(chǔ)上的國族-國家首先表現(xiàn)為具有現(xiàn)代性的民主憲政國家。民主法治的建設(shè)過程同時也是國族-國家的建構(gòu)過程。就我國而言,隨著綜合國力的提高和國際地位的攀升,國族意識也在不斷覺醒。然而我國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國族-國家,國家現(xiàn)代性的獲得以及民主與憲政建設(shè)的開展,都要求繼續(xù)推進國族-國家建構(gòu)這一歷史任務(wù)。尤其在農(nóng)村地區(qū),傳統(tǒng)的宗法關(guān)系和宗族組織這種帶有宗教性質(zhì)的社會存在,在改革開放后呈現(xiàn)出復(fù)萌的態(tài)勢,并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合法的村民自治機構(gòu)。因此,我國國族-國家建構(gòu)的重點應(yīng)是對農(nóng)村社會進行現(xiàn)代性改造。然而傳統(tǒng)的法學研究,在強調(diào)法治與憲政的價值的同時,更多的是對具體制度設(shè)計的關(guān)注,多少忽視了法治與憲政建設(shè)的政治社會結(jié)構(gòu),尤其忽視了中國獨特的宗教背景。基于對傳統(tǒng)研究的理論反思,本文擬對現(xiàn)代國家及其同憲法、宗教之間的關(guān)系進行梳理,并提出推進中國政治社會變革的具體思路。
一、國族-國家及其政治話語
國族主義是當今世界最為引人注目的政治和文化現(xiàn)象之一,國族-國家是國族話語的核心。自1990年代以來,隨著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zhàn)的結(jié)束,兩大陣營各自的堅持均土崩瓦解。在紛至沓來的各色思潮中,國族主義異軍突起、風靡一時,成為許多國家政治統(tǒng)治的合法性依據(jù)和進行社會動員及社會控制的工具;各國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活動乃至國家之間的競爭、對抗和沖突,也往往是圍繞著國族主義展開的。在各國的政治生活中,特別是在慶典、教育、文化、體育、表演等場合,都可以體驗到國族主義情緒。可以說,當今時代的任何政治運動,至少是西方世界以外的政治運動,如不與國族主義情結(jié)攜手,就不大可能取得成功。[2](P3)
所謂國族主義,與慣常所用的民族主義有著某種程度的區(qū)分,前者以國家為載體,后者則以民族為載體,不過二者都屬于民族意識的范疇。民族意識或民族觀念是一個民族在繁衍、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自我意識和政治文化認同[3],對歸屬于某一民族的人們來說,對本民族的利益及與他民族關(guān)系的認識[4]構(gòu)成了民族意識的主要內(nèi)容。說到底,民族意識是關(guān)于本民族立場和利益的觀念。據(jù)此,可以將民族意識劃分為三個層次:(單一、狹隘的)民族主義、國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往往以本民族為中心,尋求本民族的獨立、發(fā)展乃至擴張,建立單一的民族-國家是其主要追求。近代歷史上存在的狂熱的民族主義通常是狹隘民族主義的表現(xiàn),二戰(zhàn)時期所謂的“日爾曼民族”、“大和民族”等是其典型代表。國族主義則在尋求本民族與他民族的團結(jié)與合作的同時,積極尋求現(xiàn)代國家即國族-國家的建構(gòu),并追求本國在國際上的獨立與平等,包容和尊重是其主要特點。我們的“中華民族”是在這一層含義上提出的。至于國際主義的表現(xiàn)則存在著兩個相悖的向度:一個是追求全世界的大同,一個是追求本民族對世界的統(tǒng)治。后者其實是狹隘民族主義的極端發(fā)展,是當代社會中的文化殖民主義,如二戰(zhàn)時期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基于普遍人權(quán)理論所衍生出的干涉主義如“人權(quán)高于主權(quán)論”是其具體表現(xiàn)。
從民族形成的過程來看,一般總是先有民族的形成,后有通過交往產(chǎn)生的民族意識與民族認同。民族認同因其具有強大聚合力而成為人們普遍重視的一種政治資源。[5]民族認同是建立在民族意識基礎(chǔ)之上的,不同的民族意識指向不同的民族認同。以民族意識為起點,產(chǎn)生了三種不同的民族認同:一是狹隘的民族認同,二是建立在尊重他民族基礎(chǔ)上的國族認同,三是國際主義的民族認同。以國族認同為基礎(chǔ),近代西方的世俗權(quán)力逐漸擺脫了教會的束縛,并實現(xiàn)了其政治合法性基礎(chǔ)的有效轉(zhuǎn)移。從教權(quán)統(tǒng)治下獲得獨立的西歐世俗政權(quán)是近代國族-國家的最初形式。
對于現(xiàn)代國族-國家的政治權(quán)力而言,政治認同是其合法性的重要基礎(chǔ),這一點區(qū)別于以教會或血統(tǒng)為基礎(chǔ)的傳統(tǒng)國家。哈貝馬斯認為,所謂合法性“意味著,對于某種要求作為正確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認可的政治秩序來說,有著一些好的根據(jù),一個合法的秩序應(yīng)該得到承認。合法性意味著某種政治秩序被認可的價值”[6],“政府的合法性取決于社會成員的認同”[7]。只有獲得公眾的同意和支持,政府的公共權(quán)力才具備合法性。不過作為現(xiàn)代國族-國家文化基礎(chǔ)的國族認同,從一開始便被注入了一種新的因素——政治認同,現(xiàn)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礎(chǔ)也逐漸變得更加依賴于政治認同。所謂政治認同是指公民對某種政治權(quán)力的承認、贊同和同意,并且自覺地以該政治權(quán)力的要求來規(guī)范自己的政治行為。[8]政治認同的主體是一個穩(wěn)定政治共同體的成員,或者說是一個國家的公民;政治認同的客體是在穩(wěn)定的政治體系中執(zhí)政的政治權(quán)力——某一政治主體依靠一定的政治強制力,為實現(xiàn)某種利益或原則而在實際政治過程中體現(xiàn)出的對一定政治客體的制約能力。[9]
政治認同之所以被提出,主要是基于這樣的客觀事實,即現(xiàn)代國族-國家主權(quán)的合法性早已為國族認同所證明,進而需要通過政治認同來為政權(quán)提供合法性論證,其內(nèi)容表現(xiàn)為民主、法治的良性運行是否獲得保障,人民的民主、法治、憲政訴求是否得到滿足,其標準則是憲法和法律。因而,現(xiàn)代國家內(nèi)部的公民抗議活動更多的是指向決策者而不是國家。但這并不是說國族認同已經(jīng)為政治認同所取代,說到底政治認同還是國族認同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至少它是建立在國族認同基礎(chǔ)上的。況且國族認同因其自身的特點而具有無可替代的優(yōu)越性。國族認同首先是民族認同的存在形式,民族認同的基礎(chǔ)是本民族的共同文化,不同的群體在不同的歷史環(huán)境中創(chuàng)造了不同的文化內(nèi)容,并且從這些文化的不同中感悟自我,認識自己的民族歸屬。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礎(chǔ),也是民族認同存在的根基,這一特點使得民族認同比其他認同有著更為持久的聚合力。最原始的民族認同往往以血統(tǒng)淵源為基點,但民族的構(gòu)成要素并非一定包含血緣關(guān)系,尤其是現(xiàn)代社會的民族。在這里,現(xiàn)代民族已經(jīng)在無形中進化為國族形態(tài),民族認同也升華為國族認同。于是,國族認同繼承了民族認同的文化因素,而成為現(xiàn)代國族-國家牢固的政治文化根基。至于國族認同的獲得,則是世俗政權(quán)與宗教神權(quán)進行持久斗爭的結(jié)果。
二、政教分離與國族-國家現(xiàn)代性的獲得
不同的民族認同導(dǎo)出不同的國家認知,國族認同直接指向現(xiàn)代的國族-國家。國族-國家與傳統(tǒng)國家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美國學者邁克爾·羅斯金等[10]認為,國族-國家應(yīng)當具備領(lǐng)土、獨立、人口和政府等要素。但是這樣的界定并不能在國族-國家與傳統(tǒng)國家之間做出有效區(qū)分,因為一個傳統(tǒng)國家往往也會具備以上幾個要素,且不論其形式如何。如傳統(tǒng)國家也有著自己認可的地理區(qū)域,即便沒有十分明確的邊界,其疆界內(nèi)都有一定的人口,這一點在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國家表現(xiàn)得更明顯,如傳統(tǒng)中國的政府通過戶籍制度對人口信息進行較為準確的統(tǒng)計,并對人民進行相對嚴密的控制。很多傳統(tǒng)國家也有著類似主權(quán)的東西,雖然這一特征在中世紀的西歐社會表現(xiàn)得不太明顯。任何一個傳統(tǒng)國家都有一個最高的統(tǒng)治機構(gòu),表征本國政權(quán)的存在。顯然,依據(jù)上述標準很難對傳統(tǒng)國家與國族-國家進行準確的界分。
法國學者吉爾·德拉諾瓦[11](P65)認為,國族-國家是與重商主義的世界經(jīng)濟同時出現(xiàn)的,在原始資本主義時期的重商主義即將消失時形成。國族-國家的形成須經(jīng)歷四個階段:第一,確定邊界,并在此邊界內(nèi)控制居民的活動及內(nèi)部與外部的交易;第二,通過語言、宗教及隨后的教育統(tǒng)一,建立政治認同;第三,建立有參政黨、執(zhí)政黨及在野黨的政治體制,不論其形式是威權(quán)的還是民主的;第四,在地區(qū)間、社會各階層間建立互助經(jīng)濟聯(lián)系,這些分配程序建立在國土整治和重新分配機制之上。與羅斯金等人對國族-國家的界定相比,德拉諾瓦的國族-國家理論又向前邁進了一步。例如他指出國族-國家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產(chǎn)生的,這就在時間上將國族-國家同傳統(tǒng)國家區(qū)分開來;并且其關(guān)于國族-國家4個階段的劃分也大體反映了近代國族-國家建立的過程:從領(lǐng)土的確定,到政治認同的建立,到近代政體的確立,再到統(tǒng)一市場的形成。其中第二個階段值得特別注意:在這里德拉諾瓦指出了國族-國家的產(chǎn)生同西歐社會世俗化之間的關(guān)系,也就是教會與國家分野對于國族-國家形成的重要影響。例如他借用了羅坎對歐洲歷史的劃分方法,指出:“法國大革命失敗之后,國家教會作為政權(quán)形式受到質(zhì)疑。教會失去了政治權(quán)威或經(jīng)濟特權(quán),所有歐洲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實施政教分離,由此產(chǎn)生了民族-國家與普世國家或教會之間的利益沖突。”[11](P70)可以說,國族-國家概念在西方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用來同普世國家相區(qū)分的,用以指稱從教會的統(tǒng)治下獲得獨立的世俗國家。在教會一統(tǒng)天下之時,世俗政權(quán)依附于教會,因此獨立的國族-國家并不存在。只有在教會統(tǒng)治被瓦解之后,才產(chǎn)生了真正意義上的國族-國家。在這一點上,德拉諾瓦闡明了西歐國族-國家得以建立的基礎(chǔ)性條件:正是在同教會的矛盾沖突中,西歐各國的國族意識逐漸形成,并在此基礎(chǔ)上建立了國族-國家。可以說,國族-國家之所以產(chǎn)生,是因為過去的那種以宗教為政治合法性淵源的結(jié)構(gòu)被打破,而代之以新的建立在國族主義基礎(chǔ)上的政治認同。
但是德拉諾瓦的理論同樣存在著一些瑕疵,例如他沒有辦法解釋為什么存在于資本主義時代以后的國家并不都是國族-國家,雖然重商主義在那里也有著體現(xiàn),對于那些后發(fā)國家(或者說是第三世界國家)而言,更多的是在二戰(zhàn)以后才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近代意義的國族-國家,比如中國;并且即便是政教分離這一對于西歐社會具有根本性意義的原因,在解釋大多數(shù)東方社會的國家建構(gòu)問題時并不完全適用。同時,德拉諾瓦關(guān)于國族-國家建立的第三階段暗示了國族-國家并不一定是民主國家,也可以說并不一定是法治國家,比如希特勒統(tǒng)治下的德國由于缺乏憲法根基,顯然稱不上民主國家或法治國家,雖然它是一個民族-國家,但稱不上國族-國家;又因為它缺乏對他民族的包容與尊重,我們很難說它是一個具有現(xiàn)代性并實現(xiàn)了合法性基礎(chǔ)現(xiàn)代性轉(zhuǎn)化的國家。
另一個關(guān)于國族-國家概念同樣具有說服力的解釋來自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吉登斯[12]認為現(xiàn)代社會的國族-國家與傳統(tǒng)國家有著某些不同:(1)國族-國家的發(fā)展預(yù)示著傳統(tǒng)國家中相當基本的城鄉(xiāng)關(guān)系的消解,同時也內(nèi)含著(與國界相聯(lián)系的)高度密集的行政等級即韋伯式的科層制結(jié)構(gòu)的誕生,所以國族-國家可以有效地對全國進行統(tǒng)治;(2)傳統(tǒng)國家的本質(zhì)特性是它的裂變性(segmentary),其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如此有限,以至于政治機構(gòu)中的成員并不進行現(xiàn)代意義上的“統(tǒng)治”,致使傳統(tǒng)國家有邊陲而無明確的國界,而國族-國家正相反;(3)國族-國家存在著與非個人的行政權(quán)力觀念相聯(lián)系的主權(quán)觀念以及一系列與之相關(guān)的政治理念,而傳統(tǒng)國家則不是這樣;(4)國族-國家與國際關(guān)系同時起源,從而才會有人權(quán)與主權(quán)之爭;(5)國族-國家合法地壟斷了暴力工具,而傳統(tǒng)國家在這方面總是力不從心;(6)國族-國家實現(xiàn)了軍事工業(yè)化,而傳統(tǒng)國家則還沒有自己的現(xiàn)代軍事工業(yè)。此外,當然還存在著其他方面的區(qū)別。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吉登斯的分析顯然是正確和有效的,其中前五項可以說是任何一個國族-國家都必須具備的,并且指出了嚴密的官僚制、與非個人的行政權(quán)力觀念相聯(lián)系的主權(quán)觀念,指出了一系列與之相關(guān)的政治法律理念以及國族-國家產(chǎn)生于近代國際關(guān)系形成之際等,這幾點恰恰是近代國族-國家區(qū)別于傳統(tǒng)國家的主要特征。雖然他沒有過多地討論政教分離對于西方近代國族-國家形成這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原因,但是他指出了國族-國家的產(chǎn)生同近代國際關(guān)系形成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其實二者是同一個問題,因為只有在基督教一統(tǒng)天下的格局被打破之后,近代的國際關(guān)系才有可能形成。
三、民主憲政與國族-國家的政治合法性
吉登斯的解釋具有較強的說服力,但是他忽略了另外一個至關(guān)重要的標志,那便是國族-國家有憲法(包括成文的和不成文的)和在憲法基礎(chǔ)上建立起來的法律體系及政治認同。在普世國家神話破滅之后,無論是政治認同還是以參政、執(zhí)政及在野黨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政治體制,以及與非個人的行政權(quán)力觀念相聯(lián)系的主權(quán)觀念和一系列與之相關(guān)的政治理念的產(chǎn)生,都是以憲法為基礎(chǔ)的。進一步講,由于憲法是民意的體現(xiàn),甚至可以認為是對國族認同的文本確認,合憲性便成了近代國族-國家合法性的重要基礎(chǔ),脫離了教會統(tǒng)治的國族-國家只有建立在憲法的基礎(chǔ)上才會被認為是合法的,因此,憲法就是國族-國家的認同基礎(chǔ)。據(jù)此可認為,西歐國族-國家構(gòu)建的過程,實際上是政治合法性基礎(chǔ)由人與上帝之間的契約——圣經(jīng)——轉(zhuǎn)化為人民與國家之間的契約——憲法——的過程。這一過程帶來了一個顯著的后果,即教會勢力的衰落;憲法開始獲得尊崇的政治地位,法治和憲政成為了人民的世俗信仰。
通常,國族-國家的基本制度便是憲政民主制度,這是由國族-國家和憲政國家自身的特點決定的;并且國族-國家的論證方式已經(jīng)不再僅僅是國族認同,更有建立在憲法基礎(chǔ)上的政治認同。這一前提決定了非民主國家最終會被從國族-國家的行列中剔除,因此,法治和憲政就成為現(xiàn)代國族-國家建立的基石,憲法則是其政治合法性的文本契約。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1.國族-國家以一部憲法為標志
近代以來產(chǎn)生的國族-國家一般都有一部憲法,這是國族-國家區(qū)別于傳統(tǒng)國家的一個重要標志。無論把憲法看成是革命的成果,或者認為憲法是一樣先于政府的存在,它都宣示了現(xiàn)代國家同傳統(tǒng)國家的決裂。對于西方國家尤其是西歐的國族-國家而言更是如此。雖然歐洲的國族-國家是經(jīng)由不同渠道建立的,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經(jīng)歷了從教會的統(tǒng)治下獲得解放的過程,也就是世俗化的過程,且不管他們借助于哪種力量——國內(nèi)的民族主義運動或?qū)ν鈶?zhàn)爭。另外一個共同特點是,這些新獨立的國族-國家,它們的政權(quán)都是建立在憲法基礎(chǔ)之上的,是憲法賦予了它們的世俗政權(quán)以合法性地位,而不是教會。相反,在中世紀時期,政權(quán)依附于教權(quán),民族附屬于教會,二者都不是獨立的。導(dǎo)致中世紀統(tǒng)治體制瓦解的原因之一便是民(國)族主義的興起,這一瓦解反映了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和國家政權(quán)組織方式變革的必然。但新政治秩序的建立需要有力的理論論證以建立其合法性;人們也不能僅僅主張國家主權(quán)至高無上,或主張重新構(gòu)建政治秩序,而必須以一種對多數(shù)來說較容易接受、且比較便利的方式論證國家主權(quán)為什么至高無上,它的建構(gòu)路徑為何以及它的基礎(chǔ)是什么。只要我們回顧一下15—18世紀的這段歷史就會看到,此時在歐洲社會中出現(xiàn)的一系列思想家,面對傳統(tǒng)國家逐漸喪失合法性基礎(chǔ)的現(xiàn)實,開始以世俗理性為指導(dǎo),利用不同的思想資源進行新的社會設(shè)計和合法性論證,并試圖以這些新方案重新塑造社會和國家。社會契約論的國家學說,從霍布斯的《利維坦》、洛克的《政府論》到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chǔ)》和《社會契約論》,都是這一時代背景下社會-國家思想設(shè)計的大手筆。所有這些思想家都在提出各種新的國家學說,都在為國家存在的合理性、為國家權(quán)力行使的范圍和程度提出某種論證。[14]通過這種論證得出的國家觀,就是法治和憲政規(guī)制下的國族-國家,并由此發(fā)展出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法治和憲政理論。因此,新興的國族-國家將政權(quán)的合法性建立在憲法的基礎(chǔ)上也就不足為奇了。
2.法治是國族-國家官僚體系的基本原則
學者們通常把領(lǐng)土看做國族-國家的重要表征,徐迅[2](P55)曾提出,國族-國家的政府必須在其領(lǐng)土范圍內(nèi)對民眾行使有效的權(quán)力,這一點在學術(shù)界基本上已經(jīng)達成共識。而政府要想對其領(lǐng)土范圍內(nèi)的民眾有效地行使權(quán)力,就必須借助現(xiàn)代管理的必要條件和一整套嚴密的官僚結(jié)構(gòu),即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科層制,也叫做官職層級制,指的是一種以分部—分層、集權(quán)—統(tǒng)一、指揮—服從等為特征的組織形態(tài),亦即現(xiàn)代國家實施合法統(tǒng)治的行政組織。從純技術(shù)的觀點來看,科層制是效率最高的組織形式,政府、軍隊、宗教團體以及早期的企業(yè)采用的都是這種組織形態(tài),它是一種高度理性化的組織機構(gòu)的“理想類型”。作為傳統(tǒng)統(tǒng)治類型的對立面,科層制是現(xiàn)代社會理性化的標志,因為它代表了能夠滿足現(xiàn)代社會復(fù)雜且有秩序的經(jīng)濟需要的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方式。[14](P310-322)
嚴密的官僚體系不僅是國族-國家得以存在的重要條件,同時也是法治國家的基礎(chǔ)。根據(jù)馬克斯·韋伯的劃分,社會支配的類型主要有三種,即卡理斯瑪型、傳統(tǒng)型和法理型。其中法理型的統(tǒng)治是這樣的:確信法令、規(guī)章必須合于法律,以及其行使支配者在這些法律規(guī)定之下有發(fā)號施令之權(quán)力(法制型支配)。[14](P303)我們當前所談的法治國家其實便是馬克斯·韋伯所言的法理型國家的具體形式,且這種法理型國家與科層制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在馬克斯·韋伯看來,科層制的發(fā)展是衡量當今社會現(xiàn)代化的一個決定性標準,家長制或世襲制的行政體制向科層制的轉(zhuǎn)換,也即傳統(tǒng)權(quán)威向法理權(quán)威的轉(zhuǎn)換,是不可逆轉(zhuǎn)的趨勢。科層制要求官員履行公務(wù)時公正、審慎,不帶任何偏見或個人情感,不管社會地位、身份等級的差別,對一切人實行同一的法規(guī)。其中體現(xiàn)出來的原則有:科層制下的最高行政首長的支配權(quán)只限于在法律規(guī)定的管轄權(quán)限范圍內(nèi);行政官員所處的每一個職位都由法令清楚規(guī)定;官員與行政工具的所有權(quán)完全分離,而且不得將該項職位據(jù)為己有;官員在辦理公事時必須遵從組織嚴格、有系統(tǒng)的紀律和控制;形式化的、不受私人因素影響的職業(yè)精神取得主導(dǎo)地位。必須承認,以上列舉的這些方面同時也是法治國家所應(yīng)具有的特征。馬克斯·韋伯討論這些問題時主要以行政機關(guān)為例,其中體現(xiàn)出很明顯的行政法治色彩,但是我們不能認為此理論僅僅適用于行政機關(guān),因為對于司法機關(guān)甚至立法機關(guān)而言,有很多要求也是適用的。例如司法獨立這一要求,便有利于在官僚體系之中明確劃分行政機關(guān)與司法機關(guān)的體系設(shè)置,并對各自的職權(quán)進行界定,從而確保行政機關(guān)和司法機關(guān)各司其職,彼此不得逾越,進而保障官僚體系的高效率,并通過將其納入法治的軌道而防止其發(fā)生異化。也就是說,現(xiàn)代官僚體系的有效運作要靠法治的各項基本原則來保障,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法治國家與國族-國家獲得了一致性規(guī)定。
3.國族-國家對暴力工具的合法壟斷
暴力工具主要是指軍隊、警察和監(jiān)獄等,國族-國家必須壟斷暴力工具,否則其獨立、主權(quán)、有效的治理及政治合法性都會受到質(zhì)疑。然而在傳統(tǒng)社會中,世俗政權(quán)并不總是能夠有效地壟斷暴力工具。如在中世紀的歐洲,教會掌握著自己的軍隊,有自己的監(jiān)獄,從而分享了世俗世界的權(quán)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導(dǎo)致了世俗世界對教會的依賴。在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中,國家也從來沒有完全實現(xiàn)對軍隊的壟斷,即便到了清末、民國時期,也還有民團等形式的民間武裝力量存在。這一點在司法權(quán)力的行使方面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由于當時司法權(quán)隸屬于行政權(quán),而行政機構(gòu)的權(quán)力資源極其有限,于是各級官吏極力壓制訴訟、打擊訟師,并不得不把大量案件的處斷權(quán)交給宗族組織,從而導(dǎo)致家長、族長權(quán)力坐大。
暴力總是同特權(quán)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在國家不能壟斷暴力工具的情況下,那些分享這一權(quán)力的主體勢必會享有某種程度的特權(quán),甚至是分裂國家的力量,這不利于國族-國家的形成。而國族-國家要壟斷暴力工具就必須有一定的依據(jù),即憲法、法律的授權(quán)。如同其他任何一項行政權(quán)力,根據(jù)法治的原則,國家機關(guān)行使這些權(quán)力都必須依據(jù)法律的授權(quán)并嚴格遵循法律規(guī)定的程序。征稅權(quán)便是如此,在法治國家絕對不允許私人行使稅收的權(quán)力,國家稅務(wù)機關(guān)也必須依據(jù)法律規(guī)定的程序、方式和標準征稅。行使暴力的權(quán)力當然也應(yīng)遵循這一原則。
此外,主權(quán)在民是法治的主要原則,主權(quán)在民的一個重要體現(xiàn)便是包括軍隊在內(nèi)的各種權(quán)力由國家代表人民統(tǒng)一行使,如果國家不能壟斷暴力工具,則同這一原則的要求根本相悖。于是,國家壟斷暴力工具的行為就通過法治的原則性要求獲得了合法性。
總的來說,國族-國家和法治國家的建構(gòu)在現(xiàn)代社會呈現(xiàn)出合流的趨勢,雖然曾有一些民族-國家以反法治和憲政的姿態(tài)出現(xiàn),但畢竟不能左右歷史的發(fā)展趨勢,由于在這些政治共同體中存在著政治認同的危機,就注定這種發(fā)生了異化的政治權(quán)力不可能長久。現(xiàn)代國族-國家的政治認同主要建立在憲法或者說是憲政和法治的基礎(chǔ)之上,既然政府的合法性取決于社會成員的認同及公民的同意,而那些能夠獲得公民認同的政府必然是體現(xiàn)法治和憲政精神的政府。在一個權(quán)利和自由得不到保障、人民生活在混亂和無序之中的社會,其政府是無法獲得公民認同的。因此,國族-國家要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就必須進行民主憲政建設(shè),以獲得成員的認同。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之初便致力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構(gòu)建,即便存在無數(shù)的誤讀、遭遇諸多的挫折,但是對于國族-國家的構(gòu)建仍然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四、政教分離與國族-國家的宗教信仰自由
出于對傳統(tǒng)宗教專制的現(xiàn)代反思,多數(shù)國族-國家的憲法對政教關(guān)系均作出了規(guī)定,政教分離成為一個基本的憲法原則;與此同時,宗教信仰自由成為公民的一項可選擇的憲法權(quán)利。只有在政教分離的前提下,宗教信仰自由才成為可能。憲法文本對宗教信仰自由的規(guī)定,可以看做是對政教分離的一種文本確認。這是因為,宗教信仰自由的獲得使人民有了選擇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內(nèi)自由傳播,但不能成為國教進而分享國家的政治權(quán)力,否則便違背了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政教分離的原則。要探討宗教信仰自由同政教分離的關(guān)系,以及對于國族-國家構(gòu)建所具有的價值,還應(yīng)當回過頭來從宗教的本質(zhì)談起。
關(guān)于什么是宗教,有學者曾經(jīng)匯集了50多個有影響的宗教概念。[15]筆者傾向于將凈空法師對佛教的界定作擴張性解釋。在談到何謂佛教時,凈空法師[16]認為佛教乃是佛陀的教育,是智慧、覺悟宇宙人生的教育。在筆者看來,我們所說的宗教,就其實質(zhì)而言皆是教育,是對特定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的一種思考或傳播。當然,這里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其主旨應(yīng)是勸人行善,目標應(yīng)是實現(xiàn)個人心靈上的升華,促進社會的和諧,否則即為邪教。當然,也有學者指出,宗教并非必然為善,也有可能極其邪惡,在個人的宗教經(jīng)驗之中,其所信仰的神可能會是破壞之神。[17](P2)不過,本文中之宗教,主要是指以善為宗旨的宗教。
宗教不同于世俗教育之處,在于其對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如日本學者在討論儒教是否屬于宗教的問題時提出,關(guān)乎道德和社會秩序的“禮”,體現(xiàn)了儒教世俗的一面,“孝”和祖先崇拜則是其和諧價值,而這一點恰恰賦予生命以超越現(xiàn)世的連續(xù)性,并且其在形式上也具有超越死亡的恐怖與不安,從而具有了宗教的色彩。[18]當然,早期的世俗教育之中有時也會滲入對超自然力量的敬畏,這說明當時的世俗教育并未與宗教完全分離,甚至是作為宗教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宗教與世俗教育相區(qū)別之處還在于,宗教的前提和基礎(chǔ)乃是信仰,而世俗教育的基礎(chǔ)則是懷疑。誠如懷特海所說,就其教義而言,宗教可以被界定為一系列具有普遍性的道理,只要人們篤信不疑、深刻領(lǐng)會,這些道理便具有了使人品格發(fā)生轉(zhuǎn)變的效力。“長遠地來看,人之品格、人如何駕馭生命,均取決于其內(nèi)心的信仰。”“宗教實為人在幽居獨處時的經(jīng)驗。……集體的宗教狂熱、布道活動、種種宗教習俗、各種教會、儀式、圣典及行為準則,通通是宗教的裝飾,是它的不固定的外部形式。……而宗教之目的,則超越這一切。”[17](P3)自啟蒙運動以來,世俗教育走上了與宗教截然相反的道路,拒絕權(quán)威,反思“真理”,不斷對現(xiàn)有知識進行否定與更新。于是人類開始在心理上經(jīng)歷兩種不同的陶冶:一種是對超自然力量的深信不疑,一種是對自然和社會知識的證偽。
在當代社會,宗教的教育特征越發(fā)明顯,宗教信仰成為一種自主、自覺的行為,擺脫了外在的精神強制和壓迫,體現(xiàn)為智識上的覺悟和心靈上的提升。同接受世俗教育是個人的憲法權(quán)利一樣,宗教信仰活動也受到了國族-國家憲法的確認和保護。法國1789年的《人和公民權(quán)利宣言》第10條:“意見的發(fā)表只要不擾亂法律所規(guī)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見、甚至信教的意見而遭受干涉”。美國憲法第10條修正案也表示保護宗教信仰自由。而在此之后,各國憲法幾乎毫無例外地對宗教信仰自由作出規(guī)定,即便是像伊拉克、敘利亞等國,也在規(guī)定伊斯蘭教為國教的同時,對宗教信仰自由予以肯定。如《阿拉伯敘利亞憲法》第3條第1款規(guī)定,“共和國總統(tǒng)的宗教信仰是伊斯蘭教”;同時第35條第2款還規(guī)定,“國家保護舉行宗教儀式的自由,惟其儀式不得擾亂公共秩序”。但是在部分伊斯蘭國家,其憲法關(guān)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規(guī)定,徒具形式上的意義。在這些國家仍然實行張踐所說的“國教統(tǒng)治”[19](P22),如在伊朗,伊斯蘭教法是主要法律根據(jù),作為最高權(quán)力機關(guān)的國家監(jiān)護委員會,有一半成員是神職人員,最高精神領(lǐng)袖同時是軍事首腦,雖然允許其他宗教存在,但是其信徒不能擔任政府要職,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和現(xiàn)代意義的政黨都不存在,自由主義思想家還會遭到壓制、打擊和流放。[20]當然,在當今世界多數(shù)民主國家,宗教信仰自由還是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在我國,憲法第36條同樣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guān)、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并且在實踐中,我國對宗教信仰自由的保護及其實現(xiàn)程度還是值得稱道的。至于那些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的阿拉伯國家,并不被認為是真正的民主國家,也不是國族-國家,其現(xiàn)代性受到質(zhì)疑。
與對待世俗教育的態(tài)度不同,許多國家會通過憲法禁止對宗教進行補貼,如美國。雖然美國絕大部分教會財產(chǎn)是免稅的,但是這種稅收豁免被認為并不違反禁止對宗教進行補貼的法律原則。歐洲的一些國家在這一點上表現(xiàn)得并非那么絕對,如德國憲法一方面禁止確立國教,另一方面又賦予教會一定的征稅權(quán)。德國的宗教團體雖然自己可以制定規(guī)章,但須經(jīng)過州權(quán)力機關(guān)批準,同時教會稅主要針對其成員征收。瑞士、瑞典等國也有教會稅。但在英格蘭,教會稅的效力為法院所否定,認為它違反了歐洲人權(quán)公約。[21]總的來說,即便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教會稅,但其前提仍然是世俗法的認可,不同于中世紀時期世俗法依附于教會法或者世俗法與教會法呈現(xiàn)二元并存的格局。
在筆者看來,憲法對宗教補貼加以禁止有兩方面意義。一方面,宗教信仰自由與受教育權(quán)有著明顯區(qū)別。雖然宗教信仰自由是一種普遍性的權(quán)利,但是宗教信仰本身不具有普遍性:對那些不信教的人來說,對教會進行補貼有違公平原則;對甲教會進行補貼,在乙教會看來也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禁止對宗教進行補貼,實際上是將宗教信仰自由劃入了第一代人權(quán),即要求排除國家干預(yù)的消極權(quán)利,使國家權(quán)力遠離宗教,國家不得通過對某種宗教的扶持而使其享有經(jīng)濟特權(quán),從而阻斷國家與宗教的結(jié)合。事實上,各國憲法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一個前提恰恰就是政教分離。
在政教不分的情形下,教會成了高度組織化的政治實體,并與政權(quán)合一或者分享國家權(quán)力,此種宗教為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往往會利用國家權(quán)力和自身的教會特權(quán)排除異己、懲罰異端,并將自己的信仰強加給全體社會成員,個人無力擺脫這種精神統(tǒng)治,而只能以教眾即教會組織成員的身份存在,宗教信仰、政治地位均與其身份相一致,無法獲得獨立的公民身份,參與政治的權(quán)利和自由也就無從談起。當前一些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國家即是如此。這是因為,超出教育本身而組織化了的宗教具有某種排他性。就基督教的興起及其地位的確立過程來看,并不像今天基督教教會所宣揚的那樣,是福音自由播散的結(jié)果,而是一個伴隨著野蠻、恐怖、強權(quán)和暴力的過程。特別是在查理大帝統(tǒng)治時期,基督教借助法蘭克王國的力量,在西歐迅猛傳播、長驅(qū)直入。查理大帝在其征服的每一塊土地上都強迫被征服的人民信仰基督教,繳納什一稅。基督教的傳播過程是一個腥風血雨的過程。[22]當基督教一統(tǒng)天下之后,便開始排斥其他信仰的存在,甚至禁止有違神權(quán)統(tǒng)治的理論學說,宗教裁判所成為赤裸裸的反科學的暴力工具。而在政教分離的國族-國家,宗教不再分享國家行使暴力的權(quán)力,因此難以憑借武力進行精神壟斷并排斥其他宗教,于是宗教多元化開始出現(xiàn),人們有了選擇信仰宗教與選擇不信仰宗教的權(quán)利,宗教信仰自由才成為可能。
我們還可以認為,憲法對宗教信仰自由的文本確認是對傳統(tǒng)宗教專制的一種矯枉,并反過來說明國族-國家取得了超越宗教的政治地位和組織力量,使傳統(tǒng)的教會統(tǒng)治或者政教合一格局在法律上和事實上均被打破。而人們也從教會的統(tǒng)治中擺脫,由上帝的信徒變?yōu)閼椃ㄉ系墓瘛9駥ψ诮痰男叛鰞H僅是一種思想或精神上的權(quán)利,而不再是一種義務(wù),從而使人格獨立、精神自由等憲法權(quán)利得以實現(xiàn)。
五、中國國族-國家的構(gòu)建路徑
在邁向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中國也開始了國族-國家的建構(gòu)。雖然中國有時被看成是歷史上最世俗化的一個國家,并且中國自古便存在著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及可選擇性,存在著較高程度的宗教信仰自由,但事實是,中國的國族-國家建構(gòu)過程同樣伴隨著世俗化的過程,政教分離同樣是一個突出的命題。
張踐[19](P23)將宗教與政權(quán)的關(guān)系歸為四種類型:(1)宗教與政治權(quán)力相結(jié)合,宗教領(lǐng)袖與政治領(lǐng)袖合二為一,成為所謂的“神權(quán)政治”;(2)宗教與政治意識形態(tài)相結(jié)合,即某種宗教被宣布為國教而成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從而表現(xiàn)為“國教統(tǒng)治”或“神權(quán)政治”;(3)“政教主從型”的政教關(guān)系;(4)當代世界的政教關(guān)系,即政教獨立型或政教分離型。在他看來,傳統(tǒng)中國是典型的政教主從型國家。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祖先崇拜和祭祀活動是一種特殊的政治符號,形成了中國特有的祭政合一體制。同時,儒教、佛教、道教等各種信仰體系分別以不同方式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但它們都必須依附于專制王權(quán)。
這一界定有一定的道理,從歷史經(jīng)驗來看,宗教之所以會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與政權(quán)緊密結(jié)合,并形成前述(1)(2)(3)種政教關(guān)系,仍然可以通過國族-國家概念找到其根源。在當代,政府人員數(shù)量較多,如中國達7 000萬人,與民眾之比高達1∶18,美國為1∶94[23],加上科技發(fā)達,交通、通訊便利,辦公設(shè)備先進,所以能夠進行嚴密的政治統(tǒng)治。而在傳統(tǒng)社會,世俗國家的行政資源極其有限,官員人數(shù)較少。如中國漢代,官民比例僅為1∶400~1∶500[24];在中世紀的西歐,許多王國由于貧窮無力設(shè)置常備軍,致使他們難以對社會進行有效的控制,這就給各種社會組織,尤其是宗教組織的擴張?zhí)峁┝藱C會。特別是在世俗政權(quán)衰落之際,宗教勢力更會趁機擴張。在中世紀的日耳曼世界,由于日耳曼人的政權(quán)過于分散而不具有強大的政治力量,使得基督教崛起并凌駕于世俗政權(quán)之上成為可能。在日耳曼民族建立政權(quán)的過程中,基督教甚至一度成為其政權(quán)的合法性來源。此后,通過教皇革命,教會享有了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在內(nèi)的廣泛權(quán)力。
傳統(tǒng)中國則表現(xiàn)出較為特殊的一面,世俗皇權(quán)相對強大,在強大的皇權(quán)面前,任何宗教都無法染指政權(quán)。正因為宗教勢力無法對皇權(quán)構(gòu)成威脅,所以中國一直對各種宗教都比較寬容,除非是以宗教為旗號從事危害統(tǒng)治基礎(chǔ)的行為。于是在中國歷史上,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都得到了傳播。[25]相反,當某種宗教構(gòu)成了對統(tǒng)治者的威脅時,便會受到清剿,太平道、彌勒教、白蓮教等宗教都有如此經(jīng)歷。
由于各教派均不享有政治權(quán)力,他們只能作為民間組織存在,相互間的和平共處便成了可能。即便如此,在傳統(tǒng)中國特有的政治文化體系中,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仍然是不存在的。因為在傳統(tǒng)中國這樣一個專制社會,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各種宗教關(guān)系的調(diào)整都無法獲得制度保障,最終都取決于皇帝的個人喜好。由于每個皇帝會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在其統(tǒng)治過程中會加入不同的宗教信仰傾向,并導(dǎo)致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出現(xiàn)宗教壓迫現(xiàn)象。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是,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權(quán)力帶有明顯的宗法色彩,因而被稱為血緣政治。正如呂思勉、費孝通和梁治平等人所說的,中國古代之國是從家開始的,所謂一國,實則一家。“禹傳子,家天下”,國既產(chǎn)生,家便等同于天下。《大學》里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家、國、天下實是一圈圈推出的同心圓。這種國家是在原有的血緣關(guān)系上,把氏族內(nèi)部的親屬關(guān)系轉(zhuǎn)化為國家的政治組織方式,從而達致家國合一。[26](P16)這樣的國家形成方式,筆者稱之為擴張方式,由此形成的國家是宗法式的,其治理靠的是宗法關(guān)系。
春秋戰(zhàn)國的社會轉(zhuǎn)型使原來以親緣(血緣)為紐帶的家國一體結(jié)構(gòu)被打破,代之以地域原則。秦漢以后,以地域原則為主的集權(quán)國家建立,分封制這種松散的結(jié)構(gòu)形式已不適應(yīng)新的集權(quán)統(tǒng)治的需要,而代之以組織上更為嚴密的郡縣制及元以降的行省制。對此梁治平[26](P17)指出,此時的文明已不是初始的文明,但進化了的新國家不能不承受此前舊國家遺留下來的一切。這種承受是迫不得已的。同樣,由于朝廷及地方的行政資源有限,僅能掌握兵馬、財政、戶婚、田土及重犯懲罰等重要事項。至于地方治安、微罪處罰、農(nóng)桑、工賈及輕微民事爭執(zhí)等事項,大多委任地方自治[27],從而使傳統(tǒng)中國的政治呈現(xiàn)出一種二元的結(jié)構(gòu),即在城市,縣、府以上實行的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科層制,而在鄉(xiāng)村則是靠宗法進行治理的宗法政治。可見,政教之間存在著交織,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族-國家仍不存在。
有學者認為,中國近代國族-國家的形成是從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革命運動開始的,因為只有從那時起,國家權(quán)力才真正滲入到農(nóng)村。[28]事實上,在更早的時期就有人開始通過實踐將行政權(quán)力引入農(nóng)村。在清末“新政”初期,1902年,作為山西巡撫的趙爾巽便進行了改革鄉(xiāng)村政權(quán)的嘗試,趙爾巽將重建后的村落命名為“鄉(xiāng)社”,并召請地方上德高望重的精英人士來擔任這些組織的領(lǐng)導(dǎo)人,即“社長”。這些鄉(xiāng)社相對較小,約由10個村組成,比較靈活。正如湯普森所指出的,世紀之交的鄉(xiāng)社是一個從事地方事務(wù),特別是廟會、演出京劇以及征收政府所規(guī)定的稅費的社區(qū)組織。因此,無論是作為國家機構(gòu)還是社區(qū)組織,它都是十分重要的。同時代的袁世凱的改革代表著一種與晚清變法傳統(tǒng)更明顯的決裂傾向。例如袁世凱最成功的舉措之一便是于1902年前后在直隸引進現(xiàn)代警察制度,并將其擴大到廣大農(nóng)村地區(qū)。當警察制度改革推行到直隸農(nóng)村地區(qū)之后,一種全新的行政單位“區(qū)”便建立起來,以適應(yīng)監(jiān)管和稅收的需要。重要的是,“區(qū)”并不同于傳統(tǒng)士紳階層聚集的中心,而是試圖削弱、超越地方權(quán)力機構(gòu)的典型機構(gòu),因而地方士紳認為此舉是國家要取代其權(quán)威。[29]可以說,從“新政”時起,國家權(quán)力試圖進入農(nóng)村的打算從沒有中止過。其間有閻錫山在山西推行的村政改革,梁漱溟等人發(fā)起的鄉(xiāng)村建設(shè)運動,南京國民政府推行的農(nóng)村合作運動,抗戰(zhàn)時期湖北省政府推行的新縣制,最重要的是中國共產(chǎn)黨在革命時期進行的基層政權(quán)建設(shè)。
經(jīng)歷了一個世紀的歷程,中國鄉(xiāng)村的國族-國家構(gòu)建的效果如何呢?對此我們并不持樂觀的態(tài)度。其實在國民政府時期國家權(quán)力主要局限于城市,中國共產(chǎn)黨在鄉(xiāng)村建立政權(quán),卻又止于鄉(xiāng)村。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間內(nèi),國家權(quán)力無所不在,可惜在農(nóng)村未能發(fā)揮切實的效用,直到當前,中國農(nóng)村還沒有建立嚴密的科層制體系(包括自治體系),其權(quán)力的行使仍舊帶有很強的個人意志傾向。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時間內(nèi),國家機構(gòu)徒具形式意義,在實際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1982年《憲法》確認了村民自治制度,這一年離“文革”的結(jié)束僅僅6年,很難想象在這6年時間內(nèi)會把農(nóng)村中的傳統(tǒng)勢力祛除干凈。在舊的文化體系和社會結(jié)構(gòu)被摧毀、新的文化體系和社會結(jié)構(gòu)尚未形成之時,除了國家權(quán)力之外再沒有哪一種社會力量能夠擔當起整合社會生活的重任。然而恰恰在這種情況下,公社解體,農(nóng)村組織軟弱、癱瘓以至失控,國家權(quán)力草率退出農(nóng)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農(nóng)村社會的失序。國家權(quán)力退出后的真空地帶由誰來填補、鄉(xiāng)村秩序又該怎樣維護呢?顯然,在村民自治制度尚未發(fā)育成熟之際,除了請出幾度被打倒的宗法關(guān)系,再沒有一種社會力量能夠擔負起整合農(nóng)村社會的任務(wù)。于是,宗族傳統(tǒng)、宗法關(guān)系竟然迅速地復(fù)萌,傳統(tǒng)的宗族組織普遍重建,宗族活動重趨活躍,宗聯(lián)活動再次啟動,大規(guī)模的尋根祭祖儀式層出不窮,甚至諸如宗廟和祠堂的建制、祖先神位的排列、祭祀人員的組成和序列、祭祀經(jīng)費的籌措等,在許多地方都已被制度化。[30]這時的宗教影響比起傳統(tǒng)社會有所弱化是必然的,但仍不可忽視。有學者發(fā)現(xiàn),在許多基層社會機構(gòu)中,公務(wù)機關(guān)雖然形式上是現(xiàn)代意義的,然其本質(zhì)還是宗族的,往往與宗族結(jié)構(gòu)相重疊。由此可見,當前的中國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國族-國家,在我國還存在著進行國族-國家構(gòu)建、實現(xiàn)國家政治現(xiàn)代化的任務(wù),而完成這一任務(wù)的路徑則是著力對農(nóng)村社會進行現(xiàn)代化改造,即通過村民自治制度的實踐,促進農(nóng)村基層政權(quán)的不斷完善、形成非個人(宗族)的行政權(quán)力觀念以及建立在憲法(法律)而非血緣基礎(chǔ)之上的政治認同。只有這樣,才能通過完善的官僚體系(包括自治組織)驅(qū)逐宗法勢力,以非個人的行政權(quán)力代替宗族組織,以法律關(guān)系代替血緣關(guān)系,使農(nóng)村社會的現(xiàn)代化程度不斷提高。
六、結(jié)語
隨著現(xiàn)代國族-國家的建立和世俗化的實現(xiàn),國家壟斷了暴力工具,宗教組織的任何超出口頭訓誡的懲戒權(quán)力均被收歸國有,即便是口頭訓誡,如果構(gòu)成侮辱、誹謗,仍然要受到國家法律的調(diào)整。甚至宗教存在的基礎(chǔ)以及宗教活動的開展,都必須有法律特別是憲法的規(guī)定或默許。政教分離的進一步實現(xiàn)(當然,當今世界還有政教合一的國家存在),使得宗教漸漸褪去政治色彩,并向其教育的本質(zhì)回歸;宗教組織也有望趨于消解,漸漸退出政治領(lǐng)域,進而變成純粹的私人的聯(lián)合體;宗教活動則變成純粹私人的事務(wù),進而以座談會、研討會的形式展開,如福音真理座談會等。個人參與宗教活動不再是為了尋求組織上的認同,而是為了找到精神上的歸宿。當然,宗教共同體及其成員的活動也可以在公共領(lǐng)域展開,可以參與公共事務(wù)的討論。并且由于宗教去政治化的實現(xiàn),宗教界人士政治權(quán)利的提出才有了現(xiàn)實意義,宗教界人士以公民身份參與政治才具有合理性。而所有這些內(nèi)容的實現(xiàn)都必然以一部憲法為基礎(chǔ)。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政教分離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治基礎(chǔ),憲法構(gòu)成了國族-國家與宗教信仰自由的共同規(guī)范前提,且只有在國族-國家,宗教信仰自由的實現(xiàn)才具有現(xiàn)實的可能性。在我國,宗教信仰自由獲得了相當程度的保護,但建構(gòu)國族-國家的任務(wù)還未完成,宗法關(guān)系的世俗化以及政治認同基礎(chǔ)的現(xiàn)代性轉(zhuǎn)換作為建構(gòu)我國國族-國家的政治基礎(chǔ),其實現(xiàn)尚需時日。
[1] [美]托馬斯·潘恩.潘恩選集[C].馬清槐,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1:250.
[2] 徐迅.民族主義[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3] 石培玲.民族意識與多民族國家的社會和諧[J].貴州民族研究,2008(1):7.
[4] 熊錫元.民族意識問題通信錄——關(guān)于民族意識與民族主義[J].黑龍江民族叢刊,1992(1):20.
[5] 王希恩.說民族認同[N].學習時報,2002-12-09(6).
[6] [德]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M].張博樹,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184.
[7] [德]哈貝馬斯.公共領(lǐng)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M].曹衛(wèi)東,王曉鈺,劉北城,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281.
[8] 李素華.政治認同的辨析[J].當代亞太,2005(12):15.
[9] 李景鵬.權(quán)力政治學[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35.
[10] [美]邁克爾·羅斯金.政治學[M].杜震,王浦劬,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25-26.
[11] [法]吉爾·德拉諾瓦.民族與民族主義[M].鄭文彬,洪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5.
[12] [英]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M].胡宗澤,趙力濤,王銘銘,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233.
[13] 蘇力.從契約理論到社會契約理論——一種國家學說的知識考古學[J].中國社會科學,1996(3):79.
[14] [德]馬克斯·韋伯.韋伯文集Ⅱ[C].閻克文,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15] 張志剛.宗教是什么?——關(guān)于“宗教概念”的方法論反思[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4):23.
[16] 釋凈空.認識佛教[M].北京:線裝書局,2010:7.
[17] [英]懷特海A N.宗教的形成符號的意義及其效果[M].周邦憲,譯.貴陽:貴州出版集團,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
[18] [日]島園進.宗教概念的再探討[J].宇寒,譯.國外哲學社會科學文摘,2001(7):47.
[19] 張踐.論世界幾種主要政教關(guān)系類型[J].中國宗教,2006(12):22.
[20] 楊鳳崗.從伊朗選舉和美國歷史看政教分離[N].中國民族報,2009-06-30(8).
[21] [美]維克多·瑟仁伊.比較稅法[M].丁一,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29-130.
[22] 齊延平.自由大憲章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19.
[23] 馬浩亮.官民比例高達1∶18專家呼吁嚴控“官員”膨脹[N].法制日報,2005-06-13(10).
[24] [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上)[M].吳象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290.
[25] 韓香.唐代外來宗教與中亞文明[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5):57.
[26] 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27] 戴炎輝.中國法制史[M].臺北:三民書局,1987:189.
[28] 李默海.從民族國家到公民國家——農(nóng)民革命與20世紀中國政治發(fā)展[J].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4(6):35.
[29] 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xiàn)代史研究[M].王憲明,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155-157.
[30] 肖唐鏢,史天健.當代中國農(nóng)村宗族與鄉(xiāng)村治理——跨學科的研究與對話[M].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2:3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