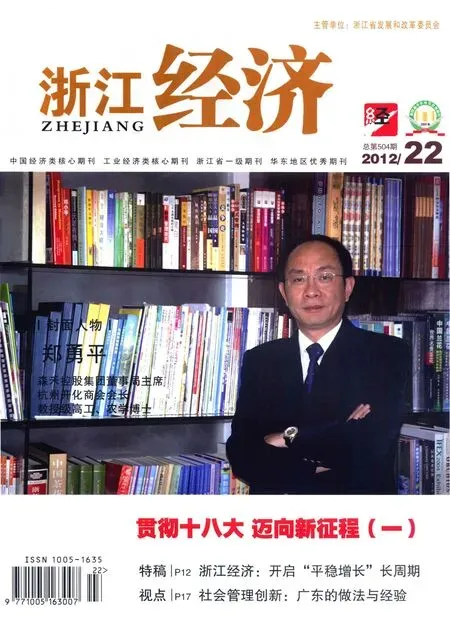從人口空間變動中把握城鎮化發展良機——以仙居縣為例
□文/徐躍平李立敏趙青青
加快仙居現有鄉鎮“傷筋動骨”的組團整合,著力城鄉統籌發展,就能產生“城鎮航母經濟”與人口變動的“人本”效應
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仙居縣2010年的戶籍人口為487588人,而常駐人口只有342676人,占總戶籍人口數29.72%的人口是凈流出。由此帶出了勞動力結構不甚合理所造成的人口空間變動與城鎮化發展不匹配的新問題。這也是一個司空見慣且易被忽視的社會發展大問題,已拖累了仙居“十五”、“十一五”兩個五年規劃。不難想象:“仙居欠發達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這句話剛提出不久,馬上就得反過來說了:“農民問題的實質是仙居城鎮化問題。”這不僅因為農民是一個弱勢群體,更因為戶籍中的40多萬“傳統農民”是我們要求培育成“農、工、商”(業)者的主體。這其中,人口空間變動與城鎮化發展就有著雙向互動的潛在結點。
統計數據中的表象與實質
2012年上半年,仙居縣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2775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4982元。這與同期臺州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030元和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9802元的數據差距甚大,也分別遠遠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6835元和8439元,反映出的不僅是兩種階層成員家庭收入差別的多少,而且更深刻地揭示出了現階段仙居城鎮化發展存在的實質問題。
常住人口發展緩慢。仙居常住人口由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的36.76萬人減少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的34.27萬人,年均增長-0.70%,這比全省同比1.53%慢了2.23個百分點,比全國同比0.57%慢了1.27個百分點。全縣外出半年以上人口占總戶籍人口50%以上的鄉鎮(街道)共有13個,其中以淡竹鄉最為嚴重,占71.39%,而占60%-70%的鄉鎮有4個(朱溪鎮、安嶺鄉、上張鄉、廣度鄉)。從臺州各縣市區人口流動情況來看,椒江、黃巖、路橋、玉環、溫嶺五個縣市區人口均為凈流入,仙居流出人口僅次于天臺187184人,流出人口居臺州市第二位,足見仙居的人口集聚能力十分薄弱。究其原因:仙居的貧困鄉、貧困村和貧困人口大都分布在廣闊而偏僻的山區,“喊話能聽見,走路需半天”的狀況處處可見。這些村落停留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狀況,滿足于“吃飽、穿暖”的原始需求,而要達到小康水平,邁向現代化,則難以踐行。如果不能改變眼前的生存環境和生活環境,那么相對貧困的狀態將伴隨終生。這就是人口空間變動的原始推力。
城鎮聚集輻射能力不強。仙居現有鄉鎮(街道)20個,從總人口規模(常住人口)上看,總人口在5萬人以上的有2個(南峰、福應),總人口在3萬-5萬人的有3個(安洲、橫溪、下各),總人口在2萬-3萬人的有1個(白塔),總人口在2萬人以下的有14個。這種人口規模偏小的行政區劃布局,缺乏城鎮集聚輻射功能,不利于產業的形成和市場的拓展。從目前看,讓農民不再是農民的唯一出路,是讓農民從速向二、三產業轉業,向城鎮遷移。但是由于仙居工業結構單一、規模偏小,其集聚能力十分有限。而城鎮化發展直到本世紀初才被提上議事日程,真正的啟動和三產的發展定位也是近三五年的事情。因此,城鎮化和產業對人口轉移、消化的功能還遠遠未得到有效發揮,致使農民在縣內轉移的通道既小又窄,彰顯滯阻。這就是仙居近17萬人(含子女)涌向縣外“淘金”的“現狀沖動力”。
資源與制度的約束。長期的城鄉分割體制、農村人口的不斷增長、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緩慢以及專業化、規模化、集約化生產不能形成,導致農村人口的流動被狹小分散的生產方式進一步“綁架”。可以說,仙居75%以上的人口在農村,人均耕地占有面積只有0.5畝,已靠攏聯合國確定的危險線,還有一部分村已接近人均0.2畝的失地線,如順其自然,連溫飽也難以保證。而事實上,仙居真正種田的人大概不會占到總人口的25%,但戶籍顯示為“農民”的人占公安機關登記口徑下的鄉村人口占90%左右。這種把“農民”看作與“市民”相對的社會類型制度已把農民死死地牽制在土地之上。按現行規定,農民進城后承包地、自留山地的處理,應由原所在地的村民委員會收回,但長久以來,農民一致將土地視為“保命田”“保險地”,千百年來的戀土情結根深蒂固,更由于進城后收入與社保的不確定性,要農民完全有償或無償交出土地,容易使其產生“恐慌”心理。資源與制度的雙重約束,嚴重地固化了農民的思維。這就是人口空間變動的潛意識內在變數。
管窺“人口變動矛盾面”中的生機
據預測:“十二五”時期是仙居人力資源最為豐富的時期。到2015年仙居勞動人口按國際標準將達到38萬多人,按國內標準達到33萬,分別占總人口的65%和75%,處于人口結構的“黃金時期”。在目前的人口空間變動走向中,在縣外經銷油漆的有1萬多人,三廢銀回收的有0.5萬多人,從事干洗行業的有1萬多人,專營服裝的有1萬多人,從事小商品、建材、化工、五金貿易的有1.5萬多人,提供飲食、美容、美發等服務行業的有2.5萬多人,其它勞務輸出的有3萬多人。表面看,這些常年在外的人口就是區域經濟的活力主體,是孕育出經濟快速增長的新動力源。但透過現象看實質,這其中也暴露了人口結構“黃金期”中大量勞動力外出與本地“市場經濟”發育不良、無法深化的“矛盾面”,彰顯出城鎮化發展滯后的通病。故此,如何把握“人口變動矛盾面”中的生機,值得認真思考。
事實上,目前仙居已基本形成了比較穩定的農村集市有序循環的“連體市場”互動格局。如白塔中心鎮以農歷2、5、8、10日,向東田市為 1、4、7日,向西皤灘為3、6、9 日為俗定的“市日”,形成了集鎮與農村連體的日日市場。通過露天集市,綠色農副產品與生活必需品等有序、等值地實現了交換,“第一市場經濟”悄然成熟。再如橫溪與埠頭,下各與大戰、雙廟等也不例外。可見,以糧、油、柴、果、肉、蛋等農副“第一產品”進城鎮占據市場為突破口,仙居“三農”與“鄉鎮集市”實現了直接連通對接。這種歷史現象在不經意中開辟了“城鄉一體化”進程中以經銷“三農”產品為主的“第一市場經濟”通道,它所反映的就是一種“連體市場”互動制衡的運行機制。
橫溪、白塔與下各這三個有著數千人口的農村集市有了一定經濟規模、綜合實力強大了便可改名為“城鎮航母經濟”(中心鎮經濟)。可以設想,要破解仙居“人口變動的矛盾面”,除了朱溪、上張、安嶺等邊遠(革命老區)鄉鎮加強自身集市貿易建設外,其它鄉鎮以其之間相同或互補稟賦要素為基礎,以共同發展目標為紐帶,進行一步到位的組團整合,就會產生人口變動的正效應。
仙居城鎮化發展的目標與要求
——基本目標。立足于仙居自然地理、歷史沿革、資源稟賦、經濟走向、風俗習慣等客觀條件,以縣城和橫溪、白塔、下各等中心集鎮為核心,通過整合周邊資源,形成人口、產業、要素向中心集鎮集聚,產業鏈和資本技術向山區延伸,讓全縣人口空間變動更趨合理,達到區域共同發展的目的。
——中心鎮組團模式。本文的中心鎮組團模式是指以城關、橫溪(省級中心鎮)、白塔(省級中心鎮)、下各(市級中心鎮)為核心的一種區劃組團整合模式。
——基本要求。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以雙向互通的中心鎮組團整合為主導模式的區域經濟格局,對當地政府工作提出了更多要求。一要解決勞動力與產業問題。中心鎮要善于在優勢中培育有特色的產業,在招商引資的同時,要大力鼓勵群眾放手干,形成“創新、創業”的新氛圍。同時要重視“人的城市化”,要從制度上、機制上保障失地農民的教育和培訓工作,提高其綜合素質。二要確定人口規模問題。把仙居沿永安溪流域劃成四個10萬-15萬人的特色中心鎮區塊,要求在規劃上調高中心鎮人口底線、在戶籍制度上充分考慮人口遷徙情況。三要把握政府與市場問題。要完善政府的監管體系,重審批、重監管,徹底打破公共設施建設上的各種壟斷,鼓勵各類經濟成分在公共設施建設上有序競爭。四要注重農業發展空間。要用新的視角去審視農業在中心鎮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要做到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人本)效益并舉,為人口空間變動提供“農業支撐”。五要理順綜合配套政策之間的關系。要理順中心鎮的發展規劃、人口空間變動、環境建設和重大基礎設施布局的關系;要理順中心鎮建設與中心村、資源村體系建設的關系;要理順農民轉業、轉移后的鎮保制度建立與農保、城保的銜接關系;要理順城鎮幫困與救助的財政轉移支付能力的關系;還要理順有利于執行全國與浙江省及本地計劃生育政策的關系。
初步結論
行政區劃的發展必須服從于、服務于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讓人口流動問題置于“中心鎮”培育成為“小城市”的發展要求之中,讓更多的農民不再局限于“固定傳統的安排”,使解決發展過程中的難題與實現既定的發展目標有機地統一在一起,以求在發展“小城市”(中心鎮)中重新認識與認真解決人口流動問題,在解決人口流動問題中求得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這就是人口空間變動與城鎮化互為促進的發展良機。
由此推論:加快仙居現有鄉鎮“傷筋動骨”的組團整合,著力城鄉統籌發展,就能產生“城鎮航母經濟”與人口變動的“人本”效應,就能在筑底企穩、制勝于人中有效地打開“兩個空間”:一是打開中心鎮培育小城市過程中增大城鎮建設投資的空間;二是打開非農產業和城鎮化發展為流動人口提供就業與增收的空間,從而促進仙居的產業結構與消費結構升級,讓整個縣域經濟社會進入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