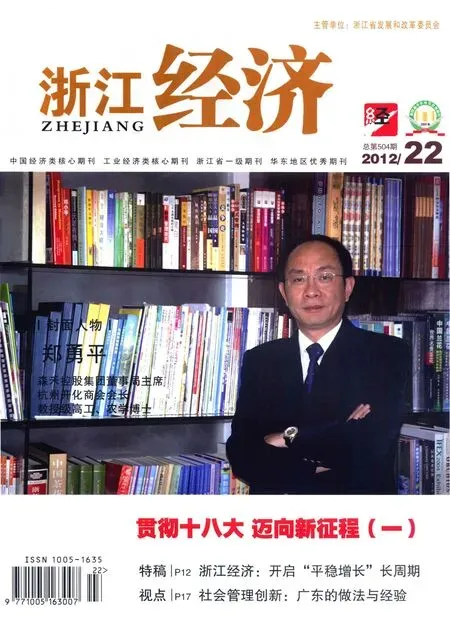浙粵滬行政管理改革模式比較
文/秦詩立
借鑒廣東簡政放權與社會重構的寶貴經驗和嘗試,來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內功的修煉,浙江才能尋得新的優勢和動力
相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與之相應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程相對較慢,同時國家尚未相關戰略決策和統一部署,無明晰改革方向和路徑選擇。但因經濟轉型升級面臨困境,及其導致經濟增速放慢,浙江、廣東等經濟較發達省市不約而同地開展了行政管理改革探索。
其中,浙江主要推進擴權強縣,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陸續5輪較大改革,縣級政府管理權限明顯擴大,縣域經濟發展全國領先。上海以浦東新區為試點,推進社會組織培育發展與功能健全,并通過政府授權或服務購買,使社會組織延伸或補充了部分政府職責,而在“強政府、大社會”構建上成功探索出新路。廣東以順德大部制改革為契機,陸續在全省25個縣市開展簡政放權,一方面推進行政管理的精簡化、扁平化,同時積極立法支持包括行業協會在內的社會組織發展,較好解決了減政后放權到何處,由誰來承擔等問題。
顯然,浙、粵、滬在推進行政管理改革的路徑選擇上并不相同。浙江強調的是行政權力下沉,以提高縣級政府在土地資金人事等要素資源調配、行政審批層級優化與簡便、社會管理與服務承擔等方面的權限,而對社會組織培育健全,以及政府部分權責向社會組織轉移建設,改革創新力度相對較小。上海強調的是通過社會組織的培育與完善,來承擔社區自治服務領域的部分職責,政府讓渡的權力也集中在基層社會管理領域,而在“強政府、大社會”建設上較好實現了某種平衡。廣東強調的是政府行政管理架構的重建和通過社會組織建設而帶動的社會重構間的對接,政府實現的不僅是部分權力,包括社區自治、經濟管理、慈善環保等領域的,轉移給社會組織,以推進“小政府、大社會”的形成;更包括通過大部制、扁平化等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及其社會組織直接登記、政府與社會組織溝通協商的契約化等,來推進社會治理機制與體系的重構。
總體而言,國家層面的政府管理改革與社會重組間的互動并不強,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及有實質意義的政府職能轉移并未有效開展。這也在相當程度上導致政府行政管理改革會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以及政府審批事項與權限難以有效減少,政府通過行政手段配置市場資源、干預經濟發展的現象未能有效減少。
對應,浙江的擴權強縣,以及擴權強區、擴權強市改革,也更多是政府體制內的管理權限梳理,未能從根本上觸及政府職能轉變及其向社會組織的轉移。相反,廣東簡政放權建立社會重構基礎上。2005年12月,廣東省人大率先通過支持行業協會建立發展的地方法規,在社會組織的登記管理、自治運營、權責明確、服務購買等方面給予法律保障,并允許先行探索、創新。2009年9月,廣東省委省政府批復《佛山市順德區黨政機構改革方案》,對順德區原41個黨政機構,按職能“合并同類項”,職能重疊、相近的黨政部門合署辦公,最終精簡為16個;并把權力鏈從“黨委——政府——秘書長——部門”簡化為“黨政——部門”,有效實現了行政部門精簡與行政管理扁平化的同步推進。與此同時,順德區及其街道、鎮成立發展咨詢委員會,主要由相關社會組織代表組織,在區域發展重大問題上實行契約化的協商;行業統計、打假維權等經濟管理,以及社區自治、慈善服務、環保服務等社會管理權責通過政府授權、購買服務等方式,讓社會組織來充分承擔,較好解決了政府職能轉變向何處轉,誰來接、能否接好等問題,以及深層次的政府職能轉變、轉移的動力源與督促問題。
廣東探索的簡政放權與社會重構改革,結合城鄉建設用地“三舊改造”、經濟人口粵西粵北“雙轉移”、前海橫琴南沙等三大新區創建、珠三角金融改革試點等配套支撐體系完善,較好保障了廣東政務、商務環境的改善和經濟增長、社會穩定。特別是面對國際金融危機蔓延,外向度最高的廣東,近年來經濟增速保持高于浙滬,其面臨的國際反傾銷反補貼訴訟相對較少,以完善社會組織為基礎的“幸福廣東”建設也較好促進了社會和諧。可以預期,隨著簡政放權的不斷推進和完善,及其對應的社會重構深入開展,廣東經濟社會發展的后勁將有效恢復,可持續發展能力將有效增強。
對浙江來說,同樣面臨國際金融危機,如何借鑒廣東簡政放權與社會重構的寶貴經驗和嘗試,來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內功的修煉,作為轉型升級發展的優良土壤和堅實保障,并有機結合“四大國家戰略”、“四大建設”、浙商回歸、工業強省等配套建設,可能是必須的戰略選擇和優先路徑。只有如此,浙江發展在轉危為機上,才能尋得新的優勢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