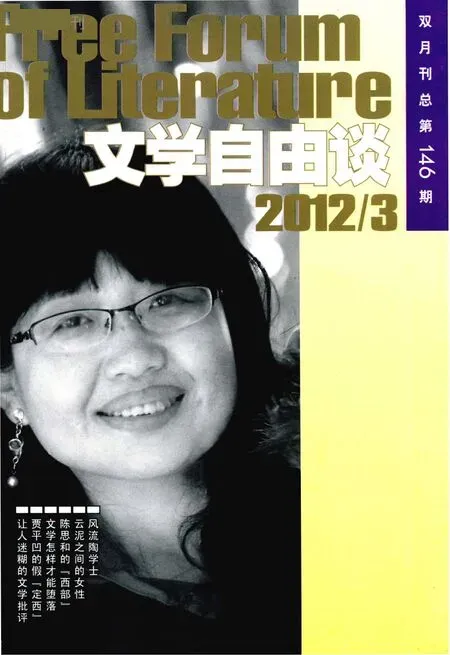苦難和重生的歷程
●文 蘇 葉
讀三卷本《柳萌自選集》,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作家此前的一生足跡,幾乎悉數烙印于此。
繾綣夢幻,翩翩風華,懷抱高潔,可還沒等展開柔嫩的枝葉,幾乎還是個大孩子,就被突襲的惡風摧折為賤民。叱奪,加罪,發配,流放,饑餒,苦力,審斗……二十余年的冤辱,戕割了柳萌最好年華,帶給他和家人深重的傷害與悲屈。
世事變遷,當柳萌在歷史的風霜中成了一株斑疤累累的沙漠斷柳時,命運又陡然翻轉,他重新回到當年驅趕他的紅墻下。帶著重病的妻子,窘迫的“家當”,在中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在百廢待舉的熱土,像無數被歷史斬殺過的文人一樣,在文山字海中重拾夢想,擔當起新時期文藝復興的責任。
他無暇也無心撣盡泥塵,和時間搶時間,向生命奪生命,除了自己的寫作,柳萌更像一位資深的裁縫,日日夜夜地飛針走線,裁剪綴掇,把全部精力擲撒于文學錦繡:編書,辦刊物,組稿件,審核,聯絡……凡此等等,都在為人縫嫁衣,做禮服,墊坎肩,修補孔雀裘。為中國文壇從毀滅中復蘇,壯大,傾心盡力地做事。
這樣一位曾經滄海,又縱覽群山之人的“戲劇”人生,在蒼茫時際秉筆記敘,這三卷《柳萌自選集》不可能不厚重。這些文字是悲愴沉郁,還是廟堂銀缸,紅燭照眼?
令人意外,都不是。
苦難和重生的歷程,在柳萌筆下波瀾不驚。那不疾不厲的敘說,映印著風云聚散的顏色,其不可阻遏的力量,似是負載了作家淵海般的深沉。書中一些章節的情景,他淡靜細切地敘來,令人如身歷其境,感受刻骨的哀痛,又對人間煙火無比留戀,個中滋味似苦還甘,難以細辨,常常令人掩卷,不忍卒讀。
1958年春那個寒冷的雨天,柳萌寫道:“中央各部委戴上右派帽子的罪人,冒雨從北京城四面八方向前門火車站聚攏,沾親帶故的男女老小,都來給發配異鄉,從此生死難料的親人送行。”這簡直是一個廣納全景的哀戚的電影場景。一個個壓抑痛楚的特寫則是:“凝滯的眼神,沉默的淚滴。新婚夫婦手拉著手久久相對而視,想親熱又不敢親熱,想勸慰又不便勸慰,兩人眼角都掛著淚珠,皺皺巴巴的神態,凄凄切切的情緒。此時此地,極其平常的叮嚀話說出來,每一句都如同悶雷,擊在烏云密布的心頭,摧落積蓄多時的淚雨,順著眾人的眼角流出,有的趕緊扭過頭去,有的止不住地抽泣。送行的人不忍看一眼走的人,卻又想再看一眼熟悉的身影……”
什么是古典詩詞中的“斷腸”?柳萌為我們做了最形象的詮釋。他用最單純的白描,如攝像鏡頭般將人間慘劇冷峻地一一囊括。深入骨髓地刻畫出“無數難言的話”,“無形的可怕的閘門”。用不著噴瀉激憤,只用這血淚相和的累累細節,就將人間殘忍的禍孽,為我們留下了永久的歷史刻痕!
這種平實文字的份量是柳萌獨有的。中國人說威武不屈,貧賤不移,富貴不淫。也許,只有一顆任其搓揉得百孔千瘡而慨然承受的心,才會獲得這份不溫不火的淡定吧?
寫磨難苦楚,寫生離死別,煽情易,平淡難。激憤易,柔軟難。只有為數極少的作家在此類題材的字里行間見溫柔見敦厚。這是品性使然。我們看到作者無論身處何境,是逆是順,是苦是樂,他的敏感總是貼近人的心。首先感受的是人本體的情感反應。事件在他筆下,幾乎沒有單獨的描述介紹,它總是和人的血肉絲絲牽連著,使我們觸摸到人心的悸顫,情感深處的曲波。
他寫母親獨自一人,站在桌前用菜刀切肥皂,一條長肥皂,從中間切開,分給她在遠方下鄉的兩個知青兒子。這個被遠歸的罪囚偶然撞見的孤凄畫面,完全不用渲染,銘刻下母親的酸辛和舐犢之情。
家人離散,一年只有十二天探親假,漫長歲月,發配荒原的賤民,區區數日之間,往返于擁擠不堪的京包線。那兩條冰冷的鐵軌,無異于兩行流不盡的眼淚。這平實的言詞,的確,只有寵辱不驚的人,才能以不加任何雕飾的最簡約的語言,表達出蝕骨傷魂。
流徙年復年,家書抵萬金。連這點兒權利都被剝奪,作家也不用激抗的筆墨,而是把自己如何在監視下,設法一而再地偷寄書信,甚至如同地下工作者寫密電碼似的機警,以及終獲家中回函的曲折細細寫來,其間不乏躲過狼眼的自得和慶喜,令讀者在悲澀中不禁會心莞爾。
還有“文革”中被歹人用火烤用冰凍嚴刑相逼;還有境況卑賤身心俱損,連累拔牙百般罹難……等等,不乏鬧劇中荒謬的詼諧,苦難中寧靜的微笑。這些沉沉往事,通過柳萌的徐徐敘談,百般滋味蘊含其中。其情至真,其真至柔,其柔至難至苦,同時至誠至善。隨便翻到哪一篇章,都可以看見作者的一顆心,一雙眼,一身風骨,附著在綿綿情義上。他不炫,不煽,不咒聲怨氣,不尖嘴利舌,更沒有油腔滑調。那些素筆陳述的點滴,如柳絮飛花,輕沾衣襟,拂之不能去。
儒家說,仁者愛人。學者方東美早就著文欽敬這種人格。他贊成老子說的:“含德之厚,此于赤子。”以前孔子欲居九夷,有人問:“陋,如之何?”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自然是不能用先賢的錦句來輕喻今人的苦痛的。但我們的確看到,一個從殺戮的獰態中脫身的人,以靜肅的尋常姿態回首平生,更多的是珍惜人間顛沛路上的溫情。
《柳萌自選集》三卷之書,有大量篇幅記敘重返文壇后的人和事。他寫在汪曾祺家替別人的書店請老先生寫店匾,自己也想要墨寶,又不好意思開口,就在書桌旁磨磨嘰嘰地翻弄字紙簍,想在扔掉的紙張中撿一兩幅寶貝。汪老問:“你這是干什啊?”得知是想要字畫,把他一撥弄,說:“要什么字,說!”
寥寥數語,作者的憨實本分,汪老的睿黠體察,文化人之間“過招”的性情趣味全畫了出來。故雨新知,平民百姓,文人雅客,閑花野草,凡此種種,在柳萌筆下總是飽蘸深情。
他自己說,人生在世幾十年,就是活個人品、人情、人緣、人味兒!
這是他的價值觀。他對美好,摯愛滿腔。對丑陋,極度痛恨。他抨擊社會歪風抨擊《文人的墮落》,直言《政績要算得失賬》,敏銳地譏諷《無障礙的障礙》,呼吁將真正的德政施惠于民,少來假大空。他的雜文,清晰地表明他與圓滑世故、勢利奸詐是絕緣的。
有評論家說,讀柳萌的散文,不如說是讀它坎坷艱辛的人生,讀他獨有的性靈。又有評論家說,柳萌看似豪邁,其實充滿柔情和哲理。他秀美的氣質深深隱藏在心中。這都是確切的。先前的苦難和后來的平順都沒讓他扭曲變形。
讀這部《柳萌自選集》,總使我想到俄國革命的十二月黨人。我還想到柳萌他們這一代新中國的知識分子,除了各自的秉性、天賦、知識各異而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深受俄羅斯優秀作品的影響。高貴的精神,浪漫的理想,開闊的抱負,坦蕩的人格,芳潔的涵養,純潔的多情……這筆精神財富自青少年時期就進入這代人的血液。令人痛惜的是,他們中最耿直最熱情最單純最有才華的優秀分子,幾乎無一幸免劫難!從劫難中撿回余生,如果仍保有赤子之心,會傾其精力追回夢想。柳萌是其中之一。這些人的堅韌豁達,和常人的從俗心態有本質的區別。
這是一種高貴的氣度和尊嚴。詩人雪萊說,道德的偉大之處在愛,在奉獻自我,在淘冶情操。當列夫·托爾斯泰穿起農人衣裳,自奉極簡,把土地分給農奴的時候,他成了真正的精神貴族。他毅然放下一切外在的、物質的、功名利祿的袍褂,只求道德的修正,只求心靈的善良與質樸。
這是作家人道主義的本色。也是文學對人性應有的終極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