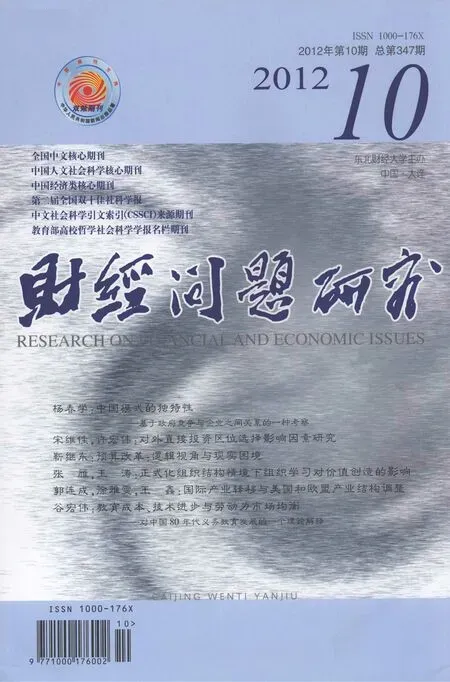社會(huì)認(rèn)同對(duì)全球品牌態(tài)度影響機(jī)制研究
郭曉凌
(對(duì)外經(jīng)濟(jì)貿(mào)易大學(xué) 國(guó)際商學(xué)院,北京 100029)
一、引 言
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重心正從粗放的總量增長(zhǎng)逐步轉(zhuǎn)移到以創(chuàng)新為核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對(duì)中國(guó)企業(yè)而言,全球品牌的建設(shè)勢(shì)在必行,唯如此才能真正提升企業(yè)實(shí)力和國(guó)家形象,并在全球產(chǎn)業(yè)分工中占據(jù)高端。在一個(gè)開放的市場(chǎng)環(huán)境下,是消費(fèi)者在本質(zhì)上決定著企業(yè)和品牌的競(jìng)爭(zhēng)力,因此建立全球品牌不僅需要關(guān)注海外收益等財(cái)務(wù)指標(biāo),更需要了解消費(fèi)者對(duì)全球品牌的認(rèn)知、態(tài)度和行為。但是,目前從消費(fèi)者心理角度探析全球品牌建設(shè),特別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考察消費(fèi)者認(rèn)同的影響,研究尚屬起步。以往關(guān)于社會(huì)認(rèn)同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社會(huì)心理學(xué)范疇內(nèi),討論社會(huì)認(rèn)同對(duì)于個(gè)體認(rèn)知、判斷、評(píng)價(jià)等方面的影響,較少涉及消費(fèi)者的產(chǎn)品和品牌態(tài)度。盡管如此,西方現(xiàn)有的文獻(xiàn)對(duì)此還是形成了較為一致的結(jié)論:消費(fèi)者的社會(huì)認(rèn)同會(huì)產(chǎn)生通達(dá)認(rèn)同的同化效應(yīng),即對(duì)于那些包含與自身社會(huì)認(rèn)同相一致信息的品牌形成更加正面的態(tài)度[1]-[4]。針對(duì)全球品牌,目前有些研究開始從全球化下消費(fèi)者心理角度探討消費(fèi)者對(duì)全球品牌的態(tài)度,比如消費(fèi)者感知的全球化程度[3]、消費(fèi)者全球—當(dāng)?shù)卣J(rèn)同[4]、消費(fèi)者價(jià)值[5]。其中,消費(fèi)者的全球—當(dāng)?shù)卣J(rèn)同就是全球化下形成的一種全新的消費(fèi)者社會(huì)心理認(rèn)同。
本文擬從社會(huì)認(rèn)同理論角度探析消費(fèi)者行為,特別是從全球認(rèn)同角度解釋全球品牌態(tài)度的內(nèi)在機(jī)理、具體作用和發(fā)生條件。發(fā)達(dá)國(guó)家消費(fèi)者的全球—當(dāng)?shù)卣J(rèn)同如何影響其對(duì)中國(guó)等新興國(guó)家全球品牌的評(píng)價(jià)?這一作用受到哪些條件的影響?研究這些問題有助于中國(guó)企業(yè)在國(guó)際營(yíng)銷中更好地制定市場(chǎng)細(xì)分和市場(chǎng)定位戰(zhàn)略,能夠真正建立起契合消費(fèi)者心理認(rèn)同的全球品牌。
二、社會(huì)認(rèn)同的多面性和通達(dá)性
在社會(huì)心理學(xué)“自我” (self)的大范疇之內(nèi),社會(huì)認(rèn)同 (social identity)超越個(gè)人自我,將個(gè)人納入更廣泛的各種社會(huì)范疇 (social category),如民族、種族、職業(yè)、性別、宗教等。Brewer提出,社會(huì)認(rèn)同反映了個(gè)人在自身與社會(huì)環(huán)境關(guān)系方面的自我認(rèn)知,通過自我歸類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自我的求同和求異需要[6]。例如,“我喜歡看書”屬個(gè)人認(rèn)同,“我是大學(xué)老師”則屬于社會(huì)認(rèn)同;“我喜歡旅行”是個(gè)人認(rèn)同,“我是國(guó)航俱樂部成員”則為社會(huì)認(rèn)同。根據(jù)社會(huì)認(rèn)同理論,為了滿足自我界定 (self-definition)的需要,個(gè)人傾向于對(duì)那些與自我一致的、能夠提高自我獨(dú)特性、有利于自我提升的社會(huì)群體或范疇產(chǎn)生認(rèn)同[7]。
顯然,社會(huì)范疇能夠表明一個(gè)社會(huì)的結(jié)構(gòu)特征,它先于個(gè)人而存在,同時(shí)也在不斷變化、流動(dòng)。比如,在因特網(wǎng)未普及之時(shí),必然沒有“網(wǎng)民”、“網(wǎng)絡(luò)工程師”、“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等范疇;今日,全球化若非如此深刻地影響全球經(jīng)濟(jì)、文化和社會(huì),世界各地的人們也不會(huì)出現(xiàn)“全球認(rèn)同”,不會(huì)自視為“全球公民”。隨著社會(huì)角色的增多和社會(huì)環(huán)境的變化,一個(gè)人可能在社會(huì)中具備多種身份,呈現(xiàn)多面性的社會(huì)認(rèn)同。比如,一名香港大學(xué)男教授的社會(huì)認(rèn)同可能包括:男性 (性別認(rèn)同)、大學(xué)教授 (職業(yè)認(rèn)同)、中國(guó)人 (國(guó)家認(rèn)同)、東方人 (東方文化認(rèn)同)、世界公民 (全球文化認(rèn)同)等,這些不同的身份和認(rèn)同反映了個(gè)體在不同情境下的自我歸類過程,可以和諧共處于同一個(gè)體中。同時(shí),從橫向角度,個(gè)體還可能同時(shí)具有看似沖突的兩種認(rèn)同。比如,美籍華人可能認(rèn)為自己既是中國(guó)人,也是美國(guó)人,體現(xiàn)出雙文化認(rèn)同 (bi-cultural identity)[8]。由于必須面對(duì)原有文化和新文化的相撞和沖突,雙文化或多文化認(rèn)同問題對(duì)于外來移民尤為突出。Berry認(rèn)為在移民的文化融入(acculturation)過程中會(huì)形成原有文化與新文化的認(rèn)同整合[9]。事實(shí)上,文化融入問題不僅涉及跨國(guó)界的移民,而且還包含在同一個(gè)國(guó)家內(nèi)部的流動(dòng)人員。比如,在我國(guó),當(dāng)土生土長(zhǎng)的農(nóng)民涌入城市成為農(nóng)民工,他們同樣面臨“農(nóng)村人”和“城里人”的文化認(rèn)同整合問題。同樣,在全球文化的影響下,人們可以同時(shí)具備全球認(rèn)同和當(dāng)?shù)卣J(rèn)同。
雖然個(gè)體可以同時(shí)存在多種社會(huì)認(rèn)同,但更值得關(guān)心的是,認(rèn)同如何切實(shí)發(fā)揮作用呢?Trafimow等認(rèn)為,只有當(dāng)認(rèn)同真正成為通達(dá)的認(rèn)同 (accessible identity)時(shí),才能對(duì)個(gè)體的信息處理和判斷施加影響[10-11]。因此,在社會(huì)認(rèn)同理論中,認(rèn)同的通達(dá)性 (accessibility)以及認(rèn)同如何經(jīng)過激發(fā) (activation)而變得通達(dá)至關(guān)重要。個(gè)體的社會(huì)認(rèn)同只有在通達(dá)的狀態(tài)下,才能進(jìn)行有關(guān)的信息處理,研究人員也才能真正了解研究對(duì)象的心理過程和機(jī)制[12-13]。在既定情形下,某種特定的社會(huì)認(rèn)同會(huì)比其他認(rèn)同更易激發(fā)為通達(dá)的認(rèn)同,從而在大腦中處于優(yōu)先處理的有利位置。所以,各種社會(huì)認(rèn)同并非固化的,而是基于不同的情境而處于不同的“顯性”(salient)狀態(tài),不同的社會(huì)認(rèn)同因此可以方便地進(jìn)行轉(zhuǎn)換。例如,雙文化認(rèn)同的個(gè)體可以進(jìn)行“文化框架轉(zhuǎn)化”(cultural frame switch)[8],即根據(jù)情境變化而采取不同的文化視角,類似于戴上不同顏色的眼鏡來看世界[14]。
社會(huì)認(rèn)同作為一種心理構(gòu)念,既可以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獲得常規(guī)性、習(xí)慣性的激發(fā),從而作為長(zhǎng)時(shí)構(gòu)念 (chronic construct)被測(cè)量[15],也可以通過臨時(shí)的情形啟動(dòng) (situational priming)來激發(fā)[16]。比如,香港人可能兼具“東方人”和“西方人”兩種認(rèn)同,若向其展示長(zhǎng)城等中國(guó)文化的象征元素,其東方認(rèn)同就會(huì)變得通達(dá);相反,若向其展示米老鼠等西方文化的象征元素,其西方認(rèn)同就變得通達(dá)[8]。除了明顯的象征性圖案外,啟動(dòng)也有很多隱性方式。例如,個(gè)人主義/集體主義啟動(dòng)就可以采用很多隱性方式,比如將自我描述為與朋友和家人相似或不同,設(shè)想自己進(jìn)行網(wǎng)球雙打或單打,或者僅僅是圈出復(fù)數(shù)或單數(shù)代詞[17]。2010年的一項(xiàng)研究還發(fā)現(xiàn),若詢問在美國(guó)的中國(guó)學(xué)生“做得怎么樣”,用英文提問比用中文提問得到的答案更為正面、更為肯定,證明語言本身也能夠成為個(gè)人/集體心態(tài)(individual/collectivemindsets)的有效啟動(dòng)工具[18]。
需要指出,雖然啟動(dòng)方式的采用日益普遍,但研究顯示,測(cè)量和啟動(dòng)兩種方式均可使構(gòu)念被激發(fā)而變得通達(dá),而且能對(duì)社會(huì)認(rèn)知和判斷產(chǎn)生相似的影響作用,因此都能夠有效預(yù)測(cè)個(gè)體的心理和行為[12]。因此,目前社會(huì)心理學(xué)和消費(fèi)者行為學(xué)領(lǐng)域的領(lǐng)先研究對(duì)于自變量一般會(huì)采用測(cè)量與啟動(dòng)相結(jié)合的方式,以便對(duì)研究結(jié)果進(jìn)行補(bǔ)充和佐證,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和內(nèi)部效度。
三、社會(huì)認(rèn)同的同化效應(yīng)和對(duì)比效應(yīng)
經(jīng)過激發(fā)而成為通達(dá)的社會(huì)認(rèn)同如何發(fā)揮作用?這涉及社會(huì)認(rèn)同的效應(yīng)問題。在不同的條件下,通達(dá)的社會(huì)認(rèn)同會(huì)產(chǎn)生同化效應(yīng)或?qū)Ρ刃?yīng)。一般而言,當(dāng)個(gè)體對(duì)目標(biāo)刺激 (target stimulus)做出判斷或評(píng)價(jià)時(shí),往往還會(huì)接受到相關(guān)的一些環(huán)境刺激 (contextual stimulus),若個(gè)體的反應(yīng)與環(huán)境刺激一致,就稱之為同化效應(yīng)(assimilation effect);若與環(huán)境刺激相反,則稱為對(duì)比效應(yīng) (contrast effect)。例如,消費(fèi)者可能因?yàn)橄矚g某廣告代言人的畫外音 (環(huán)境刺激)而青睞其所代言的品牌 (目標(biāo)刺激),即發(fā)生了同化效應(yīng);但是,如果消費(fèi)者認(rèn)為該畫外音意在操縱自己的認(rèn)知判斷,則會(huì)有意矯正 (correction)以避免受其影響,從而呈現(xiàn)對(duì)比效應(yīng)。
具體地,Wheeler等認(rèn)為,從信息加工的角度,人們認(rèn)為那些與自己認(rèn)同一致的信息更具相關(guān)性,更有利于自我提升,因此會(huì)給予更高評(píng)價(jià),從而呈現(xiàn)通達(dá)認(rèn)同的同化效應(yīng) (accessible identity assimilative effect)。例如,當(dāng)對(duì)華裔美國(guó)人施以美國(guó)文化啟動(dòng)時(shí) (如展示美國(guó)國(guó)旗、超人和國(guó)會(huì)大廈),就會(huì)更多地進(jìn)行內(nèi)部歸因(internal attribution);當(dāng)施以中國(guó)文化啟動(dòng)時(shí)(如展示中國(guó)國(guó)旗、孫悟空和長(zhǎng)城),就會(huì)進(jìn)行更多外部歸因 (external attribution)[8],而內(nèi)部和外部歸因正分別是典型的美國(guó)式和中國(guó)式歸因。但是,在一定條件下,同化效應(yīng)并未出現(xiàn),而是出現(xiàn)了與之相反的對(duì)比效應(yīng),表明同化效應(yīng)并非必然的、確定的,在個(gè)人、刺激物和情境的共同作用下同化效應(yīng)和對(duì)比效應(yīng)能夠互相轉(zhuǎn)化。例如,高認(rèn)知需求的個(gè)人容易呈現(xiàn)出對(duì)比效應(yīng),個(gè)人在認(rèn)知負(fù)擔(dān)較重時(shí)容易呈現(xiàn)出同化效應(yīng);啟動(dòng)行為本身如果被參與者視為一種明顯的操縱,人們就會(huì)進(jìn)行自我糾正并出現(xiàn)對(duì)比效應(yīng),因此個(gè)人是否意識(shí)到受啟動(dòng)的影響也決定了其表現(xiàn)為對(duì)比或同化效應(yīng)。此外,倘若啟動(dòng)的刺激物呈極端性、非代表性 (比如動(dòng)物的體積與真實(shí)動(dòng)物相比過大或過小),那么就會(huì)導(dǎo)致更多的信息加工從而引發(fā)對(duì)比效應(yīng)。事實(shí)上,社會(huì)心理學(xué)中的同化和對(duì)比效應(yīng)是一個(gè)涵蓋廣泛的課題,西方學(xué)術(shù)界對(duì)此亦有專門著述。
在文化心理學(xué)領(lǐng)域,雙文化認(rèn)同個(gè)體的認(rèn)同整合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BII)會(huì)引發(fā)不同效應(yīng):整合程度高意味著兩種文化 (如主流文化和本民族文化)共同構(gòu)成了一種結(jié)合的、交融的文化,易于引發(fā)同化效應(yīng);整合程度低則意味著認(rèn)為兩種文化彼此分割且相互對(duì)立,因此產(chǎn)生的心理不適引發(fā)對(duì)比效應(yīng)。例如,在整合程度低的情況下,當(dāng)華裔美國(guó)人被施以中國(guó)文化啟動(dòng)時(shí),反而會(huì)產(chǎn)生典型美國(guó)式的內(nèi)部歸因;相反,當(dāng)施以美國(guó)文化啟動(dòng)時(shí),則產(chǎn)生典型中國(guó)式的外部歸因。Cheng等進(jìn)一步指出,BII的調(diào)節(jié)作用還受到正面或負(fù)面文化線索的影響。如果對(duì)華裔美國(guó)人施以正面的亞洲文化刺激 (做有關(guān)亞洲文化的褒義詞填字游戲,如父母、紀(jì)律和勤勞),則體現(xiàn)上述結(jié)果;相反,如果施以負(fù)面的亞洲文化刺激 (做有關(guān)亞洲文化的貶義詞填字游戲,如迷信、保守和緊張),則認(rèn)同整合度高只會(huì)產(chǎn)生對(duì)比效應(yīng)[19]。
文化認(rèn)同不僅影響個(gè)體的認(rèn)知和判斷,而且影響其消費(fèi)行為。Aaker等發(fā)現(xiàn),美國(guó)消費(fèi)者對(duì)于品牌個(gè)性中包含美國(guó)文化特有的“粗獷”(ruggedness)元素的品牌,表現(xiàn)出更為正面的態(tài)度;類似地,日本消費(fèi)者對(duì)于包含日本文化特有的“和平”(peacefulness)元素的品牌,表現(xiàn)出更正面的態(tài)度;但是,對(duì)于美國(guó)、日本文化中共有的“興奮”(excitement)和“精致”(sophistication)品牌個(gè)性元素,兩國(guó)消費(fèi)者未呈現(xiàn)顯著差異[1]。這一研究成果證明了通達(dá)社會(huì)認(rèn)同在品牌評(píng)價(jià)中的同化效應(yīng)。另外,在消費(fèi)者種族認(rèn)同被激發(fā)從而變得通達(dá)的情況下,他們對(duì)與自己種族一致的代言人所代言的廣告產(chǎn)生更為正面的反應(yīng),從而也證明了種族認(rèn)同的同化效應(yīng)[2]。
在最近的研究中,研究人員開始關(guān)注全球化進(jìn)程對(duì)于消費(fèi)者心理認(rèn)同有何影響,以及該認(rèn)同對(duì)于消費(fèi)者在全球化市場(chǎng)中的產(chǎn)品評(píng)價(jià)和選擇發(fā)揮何種作用。具體地,Zhang和Khare發(fā)現(xiàn),伴隨全球化進(jìn)程,那些對(duì)全球化持正面態(tài)度、全球認(rèn)同程度高的消費(fèi)者會(huì)更喜歡全球品牌;反之,那些對(duì)全球化持反對(duì)態(tài)度、當(dāng)?shù)卣J(rèn)同程度高的消費(fèi)者則更加喜歡當(dāng)?shù)仄放疲?]。以下對(duì)此進(jìn)行詳細(xì)評(píng)述。
四、全球化背景下社會(huì)認(rèn)同對(duì)消費(fèi)者全球品牌態(tài)度的影響
全球化使得在任何一個(gè)國(guó)家或地方市場(chǎng)上,全球品牌和當(dāng)?shù)仄放贫即罅坎⒋娌⑾嗷ジ?jìng)爭(zhēng)。當(dāng)?shù)仄放茷楫?dāng)?shù)厥袌?chǎng)專門設(shè)計(jì)并只在消費(fèi)者所在國(guó)進(jìn)行營(yíng)銷和分銷;全球品牌則為全球市場(chǎng)設(shè)計(jì),在全球多個(gè)國(guó)家開展?fàn)I銷和分銷[3-4]。例如,在中國(guó)的智能手機(jī)市場(chǎng)上,全球品牌有蘋果和三星,當(dāng)?shù)仄放朴兄信d和小米。從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jì)學(xué)角度,全球品牌主要受到企業(yè)成本要求和經(jīng)濟(jì)利益的驅(qū)動(dòng),但近期研究表明,消費(fèi)者心理也能引發(fā)全球品牌偏好。Alden等提出了“全球消費(fèi)導(dǎo)向”(global consumption orientation,GCO),這一概念反映了受全球消費(fèi)文化的影響,人們?cè)谏罘绞健⒁轮⑹称贰蕵坊顒?dòng)等方面注重了解世界上多數(shù)地方消費(fèi)者的偏好并與其同步。而且,接觸國(guó)外媒體、到國(guó)外旅行、物質(zhì)主義能夠促進(jìn)消費(fèi)者的全球消費(fèi)導(dǎo)向,令其偏好全球而非地方品牌[20]。
更重要地,全球化影響全球消費(fèi)者的心理認(rèn)同。Arnett首次提出,全球化心理效應(yīng)的核心是人們的社會(huì)認(rèn)同發(fā)生了轉(zhuǎn)化,形成了全球—當(dāng)?shù)卣J(rèn)同 (global-local identity):人們?cè)诒A舢?dāng)?shù)卣J(rèn)同、認(rèn)同當(dāng)?shù)匚幕⒆鹬匚幕瘋鹘y(tǒng)的同時(shí),感覺到自己是一個(gè)“世界公民”,關(guān)心全球大事,熱心世界潮流[21]。以此為基礎(chǔ),Zhang 和 Khare[4]專門討論了消費(fèi)者全球—當(dāng)?shù)卣J(rèn)同 (consumer global-local identity),指出全球認(rèn)同消費(fèi)者認(rèn)為世界各地人們的共性大于差異性,對(duì)全球大事感興趣,并偏好世界上多數(shù)國(guó)家消費(fèi)者都使用的全球品牌;而當(dāng)?shù)卣J(rèn)同消費(fèi)者相信并尊重當(dāng)?shù)貍鹘y(tǒng)和風(fēng)俗,認(rèn)識(shí)到當(dāng)?shù)匚幕莫?dú)特性,偏好那些具有當(dāng)?shù)靥厣⒅饕嬖谟诒緡?guó)市場(chǎng)的當(dāng)?shù)仄放啤Ec其他認(rèn)同構(gòu)念類似,消費(fèi)者全球—當(dāng)?shù)卣J(rèn)同也可以通過測(cè)量和啟動(dòng)兩種方式進(jìn)行激發(fā)。在測(cè)量方面,全球認(rèn)同的測(cè)項(xiàng)為:我注意了解全球大事、我內(nèi)心屬于整個(gè)世界、我認(rèn)同我為一名全球公民、我認(rèn)為人們應(yīng)當(dāng)更加意識(shí)到自己與世界上其他人緊密相連等;當(dāng)?shù)卣J(rèn)同的測(cè)項(xiàng)為:我注意了解當(dāng)?shù)卮笫隆⑽覂?nèi)心屬于當(dāng)?shù)厣鐓^(qū)、我尊重當(dāng)?shù)貍鹘y(tǒng)、我認(rèn)同我為一名當(dāng)?shù)毓竦取T趩?dòng)方面,采用了25個(gè)語句重組作業(yè) (sentence unscrambling task),被測(cè)分別對(duì)含有“全球”、“全球化”或“當(dāng)?shù)亍薄ⅰ爱?dāng)?shù)鼗弊盅鄣?5個(gè)順序打亂的短句進(jìn)行排列,從而分別激發(fā)出“全球認(rèn)同”和“當(dāng)?shù)卣J(rèn)同”。
最重要的是,消費(fèi)者全球—當(dāng)?shù)卣J(rèn)同對(duì)于全球化市場(chǎng)上的品牌評(píng)價(jià)產(chǎn)生了什么影響?根據(jù)認(rèn)同一致性理論,通達(dá)的消費(fèi)者全球—當(dāng)?shù)卣J(rèn)同,在量表測(cè)量和認(rèn)同啟動(dòng)兩種方式下,都對(duì)于消費(fèi)者的全球品牌態(tài)度產(chǎn)生影響。具體地,具有全球認(rèn)同的消費(fèi)者對(duì)全球品牌的評(píng)價(jià)更高,而具有當(dāng)?shù)卣J(rèn)同的消費(fèi)者對(duì)于當(dāng)?shù)仄放频脑u(píng)價(jià)更高,即呈現(xiàn)出認(rèn)同的同化效應(yīng)。不僅如此,同化效應(yīng)在一定條件轉(zhuǎn)化為對(duì)比效應(yīng)。當(dāng)人們被明確告知要謹(jǐn)慎使用自我認(rèn)同描述作為產(chǎn)品評(píng)價(jià)依據(jù)時(shí),即認(rèn)同的可診斷性 (diagnosticity)被操控在較低水平時(shí),全球認(rèn)同消費(fèi)者反而更喜歡當(dāng)?shù)仄放疲憩F(xiàn)出認(rèn)同的對(duì)比效應(yīng)。即便未經(jīng)明確告知,但當(dāng)人們正在處于差異化的信息處理模式時(shí),也會(huì)出現(xiàn)對(duì)比效應(yīng)。由此,全球—當(dāng)?shù)卣J(rèn)同的對(duì)比效應(yīng)發(fā)生有兩個(gè)條件:認(rèn)同信息的可診斷性,以及信息處理模式。
五、全球—當(dāng)?shù)卣J(rèn)同對(duì)消費(fèi)者全球品牌態(tài)度影響的研究展望
全球化背景下消費(fèi)者的全球—當(dāng)?shù)卣J(rèn)同如何影響其全球品牌態(tài)度,該領(lǐng)域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也正因?yàn)槿绱硕鴺O具潛力。我們認(rèn)為,可以從以下兩個(gè)方面開展深入研究。
1.消費(fèi)者全球—當(dāng)?shù)卣J(rèn)同整合
消費(fèi)者的全球認(rèn)同和當(dāng)?shù)卣J(rèn)同并非同一概念的兩極,而是相互獨(dú)立的概念[5],那么能否建立類似雙文化認(rèn)同整合的全球—當(dāng)?shù)卣J(rèn)同整合(global-local identity integration)?事實(shí)上,消費(fèi)者雖然可能同時(shí)具有兩種認(rèn)同,但對(duì)二者的整合程度不同,整合程度高意味著二者交融和諧,整合程度低則表明二者互相沖突對(duì)立,從而導(dǎo)致發(fā)生同化效應(yīng)或?qū)Ρ刃?yīng)。可以推斷,在交融認(rèn)知下,全球認(rèn)同消費(fèi)者認(rèn)為全球文化和當(dāng)?shù)匚幕腔ハ喟莺痛龠M(jìn)的,因此呈現(xiàn)同化效應(yīng),偏好全球品牌;反之,在沖突認(rèn)知下,即使消費(fèi)者具有全球認(rèn)同,但由于意識(shí)到全球文化會(huì)限制甚至損害當(dāng)?shù)匚幕敲凑J(rèn)同的同化效應(yīng)將被對(duì)比效應(yīng)取代,這些全球認(rèn)同消費(fèi)者也會(huì)轉(zhuǎn)而偏好當(dāng)?shù)仄放啤L岢鋈颉?dāng)?shù)卣J(rèn)同整合概念的意義在于,全球—當(dāng)?shù)卣J(rèn)同的同化效應(yīng)不僅受制于之前所提出的兩個(gè)條件,而且受到消費(fèi)者對(duì)于二者關(guān)系認(rèn)知的影響。由此,一方面豐富了全球—當(dāng)?shù)卣J(rèn)同效應(yīng)的文獻(xiàn);另一方面,有助于全球營(yíng)銷人員更精確地識(shí)別出目標(biāo)子市場(chǎng)并施加營(yíng)銷影響。
具體而言,對(duì)于當(dāng)?shù)仄放频臓I(yíng)銷者,不僅要瞄準(zhǔn)當(dāng)?shù)卣J(rèn)同消費(fèi)者,而且要盡量激發(fā)對(duì)比效應(yīng),扭轉(zhuǎn)全球認(rèn)同消費(fèi)者對(duì)于全球品牌的追捧。例如,營(yíng)銷者可以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當(dāng)更仔細(xì)地考察產(chǎn)品本身,不要簡(jiǎn)單夸大全球認(rèn)同的決策權(quán)重;可以突出當(dāng)?shù)仄放婆c全球品牌的差異,如“原汁原味”、“文化繼承”等;可以告知消費(fèi)者全球文化對(duì)于當(dāng)?shù)匚幕幸欢ǖ呢?fù)面影響,甚至相互沖突等等。反之,對(duì)于全球品牌的營(yíng)銷者,不僅要瞄準(zhǔn)全球認(rèn)同消費(fèi)者,而且要盡量避免對(duì)比效應(yīng),比如,要強(qiáng)調(diào)認(rèn)同的重要性,并突出整合的思維模式,以及宣傳全球文化和當(dāng)?shù)匚幕幕ハ啻龠M(jìn)作用。
2.發(fā)達(dá)國(guó)家消費(fèi)者的全球—當(dāng)?shù)卣J(rèn)同對(duì)于發(fā)展中國(guó)家全球品牌的評(píng)價(jià)
Alden等在2006年就提出,在當(dāng)前的全球市場(chǎng)上,來自西方國(guó)家的品牌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可是隨著中國(guó)、印度、俄羅斯、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等國(guó)家對(duì)全球市場(chǎng)的參與日益深入,人們對(duì)全球品牌和當(dāng)?shù)仄放频倪x擇將發(fā)生怎樣的變化?因此建議在研究全球化的顧客態(tài)度時(shí)考慮這一動(dòng)態(tài)因素[21]。從市場(chǎng)上看,越來越多的發(fā)展中國(guó)家品牌走向全球市場(chǎng)。如2011年Interbrand發(fā)布的全球百?gòu)?qiáng)品牌中,就有來自墨西哥的酒類品牌科洛娜 (Corona)和來自中國(guó)臺(tái)灣的 HTC[22]。中國(guó)的海爾、聯(lián)想、華為等企業(yè)也在逐步成長(zhǎng)為全球品牌。
可以認(rèn)為,在中國(guó)等發(fā)展中國(guó)家品牌真正成長(zhǎng)為全球品牌的這一過程中,發(fā)達(dá)國(guó)家消費(fèi)者的心理認(rèn)同可能是關(guān)鍵因素。據(jù)社會(huì)認(rèn)同的同化效應(yīng),具有全球認(rèn)同的消費(fèi)者與具有當(dāng)?shù)卣J(rèn)同的消費(fèi)者相比,更加喜歡全球品牌。可以推斷,這一同化效應(yīng)也適用于來自于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全球品牌,即具有全球認(rèn)同對(duì)來自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全球品牌有更為正面的態(tài)度。原因在于,全球認(rèn)同意味著消費(fèi)者對(duì)于全球化持正面態(tài)度,認(rèn)為全球化帶來多種正面效應(yīng),來自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全球品牌為當(dāng)?shù)叵M(fèi)者提供了質(zhì)優(yōu)價(jià)廉的產(chǎn)品和更多的就業(yè)機(jī)會(huì);相反,具有當(dāng)?shù)卣J(rèn)同的消費(fèi)者可能對(duì)于全球化持負(fù)面態(tài)度,認(rèn)為全球化有很多負(fù)面效果,比如讓自己面臨失業(yè)危險(xiǎn),或者由于競(jìng)爭(zhēng)加劇而導(dǎo)致收入下降,因此對(duì)來自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全球品牌持負(fù)面看法。
在這一同化效應(yīng)中,仍需認(rèn)真考察之前所述三個(gè)調(diào)節(jié)變量的影響。其中,認(rèn)同信息的可診斷性和信息處理模式多受到情境的影響,能臨時(shí)啟動(dòng)和操控[4],而消費(fèi)者的全球—當(dāng)?shù)卣J(rèn)同整合與雙文化認(rèn)同整合類似,更屬于長(zhǎng)時(shí)構(gòu)念,消費(fèi)者對(duì)此存在著相對(duì)穩(wěn)定的長(zhǎng)期認(rèn)知,能夠進(jìn)行測(cè)量并獲得評(píng)分[19]。整合程度高意味著認(rèn)為全球認(rèn)同與當(dāng)?shù)卣J(rèn)同是相互包容、促進(jìn)的,消費(fèi)者在面臨來自中國(guó)的全球品牌和當(dāng)?shù)仄放茣r(shí),認(rèn)同的同化效應(yīng)發(fā)揮作用,偏好前者;整合程度低則表明全球認(rèn)同與當(dāng)?shù)卣J(rèn)同相互沖突,消費(fèi)者的全球認(rèn)同經(jīng)激發(fā)而變得通達(dá)后,很容易同時(shí)聯(lián)想到當(dāng)?shù)卣J(rèn)同,因而對(duì)于全球認(rèn)同可能出現(xiàn)“過度加工”和“過度矯正”[23],從而引發(fā)對(duì)比效應(yīng),即具有全球認(rèn)同的消費(fèi)者會(huì)轉(zhuǎn)而偏好當(dāng)?shù)仄放啤8鶕?jù)現(xiàn)有文獻(xiàn),建議對(duì)全球認(rèn)同進(jìn)行啟動(dòng),而對(duì)于全球—當(dāng)?shù)卣J(rèn)同整合進(jìn)行測(cè)量,
因此,在中國(guó)企業(yè)建設(shè)國(guó)際品牌的進(jìn)程中,要想被發(fā)達(dá)國(guó)家消費(fèi)者真正接受,首先,建議將全球認(rèn)同消費(fèi)者作為目標(biāo)顧客。至于全球認(rèn)同的激發(fā),一方面,通過測(cè)量,看哪些人更傾向于全球認(rèn)同,從年齡、教育背景、職業(yè)、國(guó)外經(jīng)歷等多角度繪制高全球認(rèn)同者的特點(diǎn),將其視為目標(biāo)子市場(chǎng);另一方面,通過啟動(dòng)方式臨時(shí)激發(fā)消費(fèi)者的全球認(rèn)同,比如,在廣告宣傳中突出“地球一家”、“寰宇無界”等概念。其次,對(duì)于已識(shí)別的或啟動(dòng)的全球認(rèn)同消費(fèi)者,還必須進(jìn)一步強(qiáng)調(diào)全球認(rèn)同和當(dāng)?shù)卣J(rèn)同的相容性,表明全球認(rèn)同并不排斥當(dāng)?shù)卣J(rèn)同,相反,即“地球人”和“當(dāng)?shù)厝恕笨梢韵嗷ゴ龠M(jìn),比如,“具有世界眼光的當(dāng)?shù)厝恕焙汀傲⒆惝?dāng)?shù)氐牡厍蛉恕薄?梢哉J(rèn)為,采用全球認(rèn)同概念,明晰其認(rèn)同效應(yīng),并提出全球—當(dāng)?shù)卣J(rèn)同整合這一調(diào)節(jié)變量,能夠?yàn)橹袊?guó)企業(yè)建立全球品牌提供切實(shí)有效的理論指導(dǎo),幫助其更好地制定市場(chǎng)細(xì)分、市場(chǎng)定位和溝通戰(zhàn)略。當(dāng)然,本文側(cè)重于中國(guó)等新興國(guó)家的全球品牌如何與發(fā)達(dá)國(guó)家市場(chǎng)上的當(dāng)?shù)仄放聘?jìng)爭(zhēng),未涉及與其他發(fā)達(dá)國(guó)家全球品牌,原因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消費(fèi)者在全球化進(jìn)程中可能更多體會(huì)到來自新興國(guó)家而非其他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競(jìng)爭(zhēng)。
[1]Aaker, J. L. Accessibility or Diagnosticity?Distangling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on Persuasion Processes and Attitudes[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0,26(3):340-257.
[2]Forehand, M.R., Deshpandé, R., Reed, A.Identity Salience and the Influence ofDifferent Activation of the Social Self-Schema on Advertising Response[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2,87(6):1086-1099.
[3]Steenkamp,J-B.E.M.,Batra,R.,Alden,D.L..How Perceived Brand Globalness Creates Brand Valu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3,34(1):53-65.
[4]Zhang,Y.,Khare,A.The Impact of Accessible Identities on the Evaluation of Global versus Local Products[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9,36(10):524-536.
[5]Steenkamp,J-B.E.M.,Jong,M.G.A Glob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nstellation ofConsumer Attitudes toward Global and Local Products[J].Journal of Marketing,2010,74(11):18-40.
[6]Brewer,B.The Social Self:On Being the Same and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1991,17(5):475-482.
[7]Tajfel,H.,Turner,J.C.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A].Worchel,S.,Austin,W.G.(Eds.)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2nded)[C].Chicago:Nelson-Hall,1985.6-24.
[8]Hong,Y.,Morris,M.W.,Chiu,C.Y.,Benet-Martinez,V. MulticulturalMinds:A 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Culture and Cognition[J].American Psychologist,2000,55(7):709-720.
[9]Berry, J. W.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7,46(1):5-34.
[10]Trafimov,D.,Triandis,H.C.,Goto,S.G.Some Tests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rivate Self and the Collective Self[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1,60(5):649-655.
[11]Trafimov,D.,Silverman,E.S.,F(xiàn)an,R.M.T.,Law,J.S.F.The Effects of Language and Priming on the Relative Accessibility of the Private and the Collective Self[J].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1997,28(1)107-123.
[12]Higgins,E.,Tory,J.A.B.Social Cognition and Social Perception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1987,38(5):369-425.
[13]Oyserman,D.,Lee,S.W.S.Priming“Culture”:Culture as Situated Cognition[A].Kitayama,S.,Cohen,D.(Eds.)Handbook of Cultural Psychology[C].New York:Guilford Press,2007.255-279.
[14]Aaker,J.L.,Benet-Martinez,V.,Garolera,J.Consumption Symbols as Carriers of Culture:A Study of Japanese and Spanish Brand Personality Construct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1,81(3):492-508.
[15]Higgins,E.T.Knowledge Activation:Accessibility,Applicability,and Salience[A].Higgins,E.T.,Kruglanski,A.W.(Eds.)Social Psychology: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C].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6.133-168.
[16]Srull, T. K., Wyer Jr., R. S. Category Accessibility and Social Perception: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Person Memory and Interpersonal Judgments [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0.38(6),841-56.
[17]Oyserman, D., Lee, S.W.S.Does Culture Influence what and how We Think? [J]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8,134(3):311-342.
[18]Lee,S.W.S.,Oyserman,D.,Bond,M.H.Am I doing Better than You?That Depends on whether You Ask Me in English or Chinese:Self-Enhancement Effects of Language as a Cultural Mindset Prime[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10,46(5):785-791.
[19]Cheng,C.Y.,Lee, F., Benet- Martinez,V.Assimilation and Contrast Effects in Cultural Frame Switching(CFS):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BII)and Valence of Cultural Cues[J].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2006,37(6):742-760.
[20]Alden,D.L.,Steenkamp,J.-B.E.M.,Batra,R. Consumer Attitudes toward Marketplace Globalization: Structur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2006,23(9):227-239.
[21]Arnett,J.J.The Psychology of Globalization [J].American Psychologist,2002,57(10):774-783.
[22]Interbrand.Best Global Brands[EB/OL].http://www.interbrand.com/en/best-global-brands/Best-Global-Brands-2011.aspx,accessed July 10,2012.
[23]楊曉莉,劉力,張笑笑.雙文化個(gè)體的文化框架轉(zhuǎn)換:影響因素與結(jié)果[J].心理科學(xué)進(jìn)展,2010,18(5):840-848.
- 財(cái)經(jīng)問題研究的其它文章
- 高管權(quán)力對(duì)高管薪酬的影響研究
- 教育成本、技術(shù)進(jìn)步與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均衡
——對(duì)中國(guó)80年代義務(wù)教育發(fā)展的一個(gè)理論解釋 - 中德遭受貿(mào)易壁壘差異性的原因分析
——基于出口價(jià)格與數(shù)量的對(duì)比 - 國(guó)際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與美國(guó)和歐盟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
- 自主創(chuàng)新企業(yè)縱向合作研發(fā)的利潤(rùn)分配
——考慮補(bǔ)貼激勵(lì)的演化博弈仿真研究 - 融資約束、現(xiàn)金持有與研發(fā)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