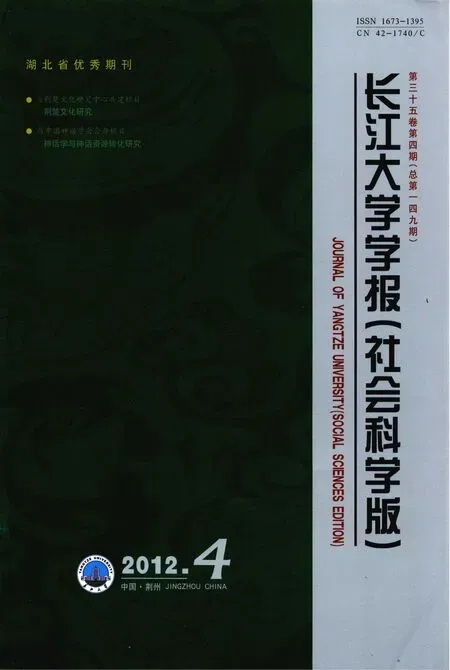論《蠅王》中的女性主義
吳甜甜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外國語學院,湖北武漢430074)
論《蠅王》中的女性主義
吳甜甜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外國語學院,湖北武漢430074)
由于作品中女性角色的缺失,《蠅王》被認為是男性文本的代表作,而戈爾丁則是男性話語的代言人。從立意主題和人物刻畫兩方面對其進行解讀發現,作者并非“菲勒斯中心文化觀”的支持者,相反,他對這種文化觀持懷疑態度;女性角色的缺失并不是對女性的否定和忽視,這種缺失凸顯了女性在場的重要性。
蠅王;威廉·戈爾丁;女性主義
《蠅王》從發表之日起就受到廣泛關注,人們從神話、宗教、歷史和心理等方面對其進行了全面的詮釋和剖析。隨著女性主義批評的興起,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文學的性別話題,抨擊小說的男性權威,認為男性權威是后現代主義語境中反女性主義的產物,戈爾丁這種不設計女性角色的做法,正是極端大男子主義的突出表現。
批評家萊利(Patric Reilly)指出:“《蠅王》有父親和兒子,卻沒有母親和女兒,這是一個令人矚目的省略。”萊利因此質疑戈爾丁作為作家的資格,“一個作家省略了如此不可缺少的成分,怎么還能冠以作家的頭銜?”[1](P57)于海青在其論文《“情所獨鐘”處——從〈蠅王〉的殺豬“幕間劇”說開去》中,將《蠅王》中女性角色的缺失理解為男性作家對女性角色的人性壓制,是“一場排擠或壓制女性的陰謀”。[2]陳楓艷在《論〈蠅王〉中女性的缺場》中指出,女性角色缺失,源自于戈爾丁的“菲勒斯中心文化觀”,即“把女人看作是客體、藝術品和偶像,而不是主體、雕塑家和作家”。[3]在這里,筆者試圖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出發,從立意主題和人物刻畫兩方面對小說進行闡釋。
一、立意主題方面
由于生理、社會和歷史原因,兩性在社會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蠅王》是一部探討人性善惡的小說。戈爾丁曾經說過:“《蠅王》的主題就是悲哀,徹底的悲哀,悲哀,悲哀,再悲哀。”他認為:“人作惡就像蜜蜂釀蜜一樣。”在他看來,惡與生俱來,人皆有之,是人性的一部分;要控制惡是不容易的,人總是在有意識地抑制本性中的惡,否則,后果將不堪設想。
根據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學說,人格由三部分組成: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id)按照快樂原則行事,一味追求滿足,永遠都是無意識的。自我(ego)按照現實原則行事,是仲裁者,監督本我的動靜。自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對本我進行控制和壓制,任何能成為意識的東西都在自我之中。超我(superego)按照至善原則行事,限制本我,指導自我。只有這三個部分和睦相處,保持平衡,人才會健康發展,否則,將給個人乃至社會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從這個觀點出發,本我就是真正的人性,而自我和超我都是文明發展下文化規約的結果。
為了揭示人性,戈爾丁創造了一個毫無規約的環境,試圖將一切暴露在最原始的狀態下——一群6~12歲的英國男童,一個近乎原始的孤島。在正常情況下,在兩性共處的環境下,男性往往被描述成英雄,為了在女性面前保持體面,他們即使孤立無援,也會努力彰顯陽剛氣質,英雄救美,顯示自己的勇猛,擺出一副護花使者的姿態;他們即使舉止粗獷豪放,也會努力在女性面前表現得溫文爾雅,極盡斯文紳士之能。《蠅王》所仿寫的歷險小說《珊瑚島》,將男性刻畫成可以拯救女性甚至世界的強者,這才是真正的“菲勒斯中心文化觀”的特征。而在《蠅王》這部小說里,女性角色缺失,男性失去了在異性面前展現自己的機會,讓讀者看到了他們的本來面目:爭權奪利、野蠻混亂、血腥殘暴,將好端端的美麗小島變成火海。在小說中,拉爾夫屢次強調公共衛生,多次號召孩子們開會,并規定大小便的地點,效果卻不甚理想。他們泥土涂面,衣著襤褸,嗜血殺生,野蠻狂舞,絲毫顧不得任何體面。在這樣一個沒有女性的環境下,文化規約的底線被徹底打破,男性擺脫了自我和超我的束縛,回到本我的無意識的狀態,這揭示了作家想要表達的人性本惡的主題。
小說在闡釋人性善惡的過程中,假設女性角色缺失,從表面上看,忽視女性角色,有大男子主義傾向,但實際上卻從反面證實了女性及其扮演的角色在文明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在人性的養成過程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忽略、排斥女性存在及其在社會中的積極影響,單調失衡的男性社會將難以延續文明;缺乏兩性的相互作用,人性中的惡只會不斷膨脹,最終導致世界的崩潰瓦解。而只描寫男性在斗爭中的邪惡殘暴,卻不描寫女性,也讓人想到女性的純潔和無辜,她們原本就不應卷入人性的退化墮落,她們應該遠離殺戮、戰場及一切黑暗和邪惡,她們代表著文明和希望。
二、人物刻畫方面
要想在現代社會立足,必須具備完整、豐富的性格特征。男性不僅要具備傳統的男性氣質,同時也應溫柔細心、心存關愛,富有同情心。
從對小說的主人公拉爾夫的描寫我們可以看出,父輩的戎馬生涯對一個小男孩的成長產生了重要影響:男性必須擔負拯救世界的重任;男性必須強健、剽悍、粗獷;男性必須富于競爭性、有野心和攻擊性。在拉爾夫的心中,父親就是他的榜樣,他的目標就是長大后成為一個像父親一樣的男人。他總是有意無意地向其他孩子提到父親:“我五歲就會游泳,我爸爸教的。他是個海軍軍官。”“我父親在海軍里。他說已經沒什么島嶼人們不知道的了。”“早晚會有船派到這兒,沒準還是我爸爸的船呢。”拉爾夫絕口不提他的母親或其他女性,他瞧不起總是將姨媽掛在嘴邊的“豬崽子”。他從不閱讀關于托普茜和莫普茜的書,僅僅是因為那是關于兩個小姑娘的故事。與此相反,《火車》、《輪船》以及關于“妖道術士”和“發掘埃及”之類的書卻對他有著莫大的吸引力。在男性中心主義文化觀的影響下,拉爾夫的成長明顯地打上了傳統男性的烙印。他們喜愛冒險和進攻,并由此發展為對暴力和戰爭的癡迷。這些氣質使男性在傳統社會享有統治權,但同時也使他們必須面對戰爭殺戮帶來的殘疾和早逝等問題。在小說中,男孩子們同樣成為權力擁有者的犧牲品。失去支持和小島管理權的拉爾夫最終遭到杰克的追殺,如一只受驚的“獵物”,東躲西藏,等待死亡的降臨。拉爾夫和他的伙伴們在珊瑚島上所經歷的一切,只不過是父輩掠奪、殺戮生活的縮影。不同的是,男性成人世界的這種斗爭要更猛烈、更殘忍。而導致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傳統男性社會制度和文化的缺陷,而解決這一問題則必須重視女性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三、結語
筆者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從立意主題和人物刻畫兩方面重新審視了威廉·戈爾丁的作品《蠅王》。以往文學評論界認為,戈爾丁是男權主義的推崇者,《蠅王》是二戰后男性主義的經典,[4]這其實是對戈爾丁和《蠅王》的誤讀。整部小說巧妙地運用反證法,女性角色的缺失,讓讀者意識到女性在場的重要性。如果忽略和排斥女性,不給予她們平等的社會地位,不考慮她們在社會中的積極影響,單調失衡的男權世界將是岌岌可危的。小說大膽假設女性角色缺失,并以悲劇結尾,從反面有力地證實了女性在場的重要性,集中表現了男權邪惡的藝術主題和缺乏女性影響下的男性人物性格缺陷導致的悲劇。在《蠅王》中,雖然沒有鮮明、飽滿、正面的女性形象,但這并不足以說明戈爾丁就是男性話語權的代言人,其作品并不是男性文本的代表作。
[1]Reilly,Patrick.Lord of the Flies:Fathers and Sons[M].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92.
[2]于海青.“情所獨鐘”處——從《蠅王》的殺豬“幕間劇”說開去[J].國外文學,1996(4).
[3]陳楓艷.論《蠅王》中女性的缺場[J].常州工學院學報(社科版),2005(3).
[4]王衛新.中國的《蠅王》研究:回顧與前瞻[J].外語研究,2003(1).
I106.4
A
1673-1395(2012)04-0029-02
2012-02-20
吳甜甜(1988—),女,湖北荊州人,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 葉利榮 E-mail:yeliro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