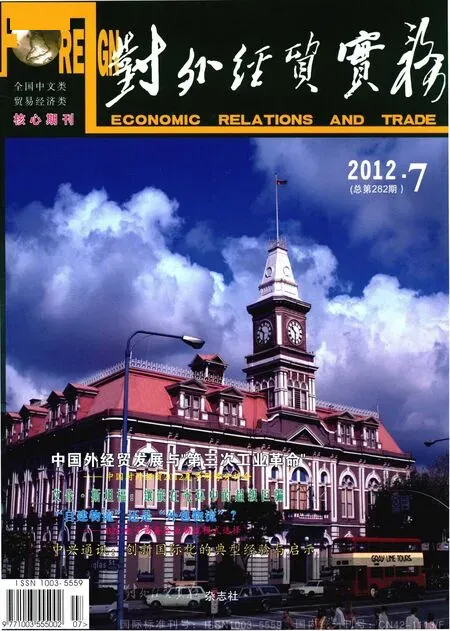《鹿特丹規則》下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承運人責任分析
■ 孫 爽 安徽國際商務職業學院
2008年12月11日經第63屆聯合國大會67次會議審議通過了《聯合國全程或者部分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公約》,即《鹿特丹規則》。在荷蘭鹿特丹舉行開放供簽署儀式的當天,該規則就獲得了16個國家的簽署。到2009年12月31日止,共有包括美國、法國在內的21個國家簽署了這一規則。根據該規則生效條件“該規則于第二十份批準書、接受書、核準書或加入書交存之日起一年期滿后的下一個月第一日生效”,為此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關注。總體來看,《鹿特丹規則》內容龐雜,共18章96條,實質性條款88條,有學者統計相當于9個《海牙規則》,3個《漢堡規則》,涉及多方面的突破與創新,是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律統一運動的重要產物和顯著成果。在其眾多的先進制度中加重承運人責任,平衡船貨各方的利益是其一大亮點。
1924年的《海牙規劃》出臺時,正是船方實力最為強盛的時期,所以在制度設計上,過于偏袒承運人的利益,船貨雙方利益明顯失衡;后來的1968年《維斯比規則》,再到1978年的《漢堡規則》,一直致力于平衡二者的利益,并為此目標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撼動“海牙體系”。進入到21世紀,船貨雙方在諸多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加之國際貨物運輸方式的發展和變化,《鹿特丹規則》作出了諸多加重承運人責任的規定,以期尋求船貨各方利益在新形勢下的平衡點。
一、擴展承運人責任期間
《海牙規則》規定,承運人的管貨義務為七個環節,《鹿特丹規則》則明確規定義務為九個環節,即承運人應當妥善而謹慎地接收、裝載、操作、積載、運輸、保管、照料、卸載并交付貨物。對承運人責任期間,擴展包括了接收貨物和交付貨物兩個環節,使這一責任期間形成一個閉合的“責任環”(《鹿特丹規則》第12條之規定)。這也是國際貿易實踐中通常的做法,也符合集裝箱運輸特點。
這一規定的初衷很好,承運人責任期間的擴大雖然有利于保障貿易商的貨物權益,但這就要求船公司具備全球物流經營的實力和能力,可是現實狀況是大多船公司對非海上運輸區段的風險難以控制。很多學者擔憂,若按照《鹿特丹規則》實施,在一定程度上將會刺激貨運代理業及中間商的發展,這樣的話勢必要增加而不是減少船貨雙方的中間環節以及貨物運輸的總成本。實際上擴展責任所增加的風險費用變相的將會轉嫁給托運人,實踐中的可行性有待商討。
二、延長承運人適航義務
《鹿特丹規則》繼續沿用前三個規則中傳統適航的內涵,保留了適航義務的標準是謹慎處理的規定。但《鹿特丹規則》將承運人適航的義務由原來的“開航前和開航時”改變為“整個海上航程”。《鹿特丹規則》第14條規定船舶全程必須適航,通過這樣的規定大大加重了海運承運人的責任。
在此之前的國際貿易運輸中,要追究承運人的適航責任往往要證明船舶的不適航原因在開航前或開航時即存在,這無形中增加了貨方舉證責任。如一艘貨船開航前經具有資格證書的驗船師檢驗被視為適航船舶,但該貨船未航行多遠即因船艙進水、貨物受損而停靠附近港口檢修。檢修時查明船艙進水的原因是一顆完好螺帽下的螺絲有裂隙。顯然,若根據《海牙—維斯比規則》一定要證明其在開航前即存在,致使船舶不適航;但在《鹿特丹規則》下,不需要有此過程,極大地解放了貨方的舉證責任,這一規定帶有一定的積極性。
但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其實這樣的規定也有其不合理的因素。試想這世界有哪艘船能保證它在各方面都完全適航,在整個航程中可以保證始終處于適航狀態,就連再次引起轟動的“泰坦尼克”也會在首航時出狀況。《鹿特丹規則》這樣的規定使承運人負有更大的風險和責任,從平衡雙方利益,也是公平起見,規則也規定對承運人實行完全過失責任原則,在這樣的原則下,要想承運人承擔責任,就變得不那么簡單,若實際實施起來圍繞這個問題產生的糾紛一定不會少。
三、提高承運人賠償責任限額
《鹿特丹規則》明確規定,承運人對于貨物滅失、損壞的賠償責任為每單位875SDR或毛重每公斤3SDR(以其高者為準)。賠償責任較之前的《維斯比規則》從每件貨物666.67SDR或每公斤2SDR(以其高者為準)、《漢堡規則》從每件貨物835SDR或每公斤2.5SDR(以其高者為準)提高較明顯。被學者總結為迄今為止,規定承運人賠償限額最高的規則,也是《鹿特丹規則》加重承運人責任的最好佐證之一。
中國學者參與了規則起草的全過程,有資料顯示,就這一款規定引起很大的爭論:一些非洲發展中國家認為,考慮經濟發展現狀,《鹿特丹規則》的責任限額理應大大高于《漢堡規則》;中國、韓國、北歐國家則認為,從商業的角度考慮,無需再提高。《鹿特丹規則》限額相對《海牙-維斯比規則》,每件提高了31%,每公斤提高了50%;相對《漢堡規則》,每件提高了5%,每公斤提高了20%。有些學者認為這種高限額責任制,在運輸實踐中落實程度將會打折扣,未必達到效果;同時如果實施這一規則勢必會帶來全球航運業的大洗牌,可能對于大型的航運企業影響并不大,因他們資金雄厚,但對于像中國等以中小型航運企業為主的國家,提高責任限額的規定對其沖擊很大,稍有不慎,就將企業推到了懸崖邊。
四、變化承運人免責事項
《鹿特丹規則》在承運人免責事項上基本延續了《海牙規則》的理念,但《鹿特丹規則》采用了“封閉式列舉”的方式,而非《海牙規則》的“開放式列舉”方式來加以規定,僅限于公約列明的15項。對這些內容加以整理,會發現比較突出的變化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增加了“海盜、恐怖活動”的規定。例如眾所周知的索馬里海盜,2009年12月,索馬里海盜當選為時代周刊2009年年度風云人物。2010年中國還派出了護航艦隊,是中國海軍15世紀以來首次遠征。2011年4月11日,聯合國安理會決定在索馬里境內和境外設立特別法庭,負責審判在索馬里附近海域實施海盜行為的嫌疑人。據統計,每年通過蘇伊士運河的船只約有1.8萬艘,其中大多數都要經過亞丁灣,而這條重要國際航道也為索馬里海盜提供了大量下手的目標,《鹿特丹規則》中這一規定非常具有現實意義,有這個時代的印跡。
第二,明確火災免責的范圍。僅限于在船舶上發生的火災,不包括陸地上發生的火災。《鹿特丹規則》取消“航海過失”和“火災過失”免責,這樣的規定使承運人對貨物的滅失、損壞可以免責的情形大大減少,甚至有些學者認為承運人幾乎就喪失了免責的機會。
第三,增加合理繞航的限定條件。在前面三個公約中規定,只要是救助或企圖救助人命或財產都構成合理繞航,承運人可以免除由此導致的損失賠償責任。但《鹿特丹規則》則強調,對于財產救助的免責必須是采取合理措施的結果,為其免責增加了限定條件。
第四,增加為環境損害的免責條款。《鹿特丹規則》中規定為避免環境損害而采取合理措施導致的出現貨損的,承運人可以免責。加強承運人的環境保護責任是時代的要求,這一變化符合當前國際航運發展的趨勢。
五、松動承運人憑單交貨義務
在整個《鹿特丹規則》中有一個幾經反復討論,又經多次增補、修訂而形成的條款,甚至成為《鹿特丹規則》備受爭議的最大關注點,就是該規則的第47條第2款。這一條款規定了關于可轉讓提單的無單放貨機制。現試就此項可能讓提單無單放貨機制的內容概括如下:
其實《鹿特丹規則》中的“無單放貨”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無單放貨,它在制度上做了諸多的假定和限制。根據該公約的規定,在一些特定情況下或者符合一定條件時,承運人無須承擔無單放貨的責任。對于不可轉讓的運輸單證,承運人在目的港交貨時并不一定必須要求提交不可轉讓的運輸單證,只需查明收貨人的身份即可向其交貨。
能夠實施這一規定的各種情況可以羅列如下:
1.單據的明確要求。能夠適用無單放貨合法機制的條件是必須在單證上有這樣的規定,即明確載明“無須提交可轉讓運輸單證或者可轉讓電子運輸記錄,便可交付貨物”字樣。這是實施這一制度的前提條件。
2.承運人盡到通知的義務。如果貨物到達目的地,單證持有人未能在期限內向承運人提貨或者承運人無法確定持有人,則承運人可以依次通知托運人、單證托運人,要求其就交付貨物發出通知。這是這一機制實施的又一個條件。
3.有指示義務解除。承運人依托運人或單證托運人的通知交付貨物的,解除承運人向單證持有人交付貨物的義務。
但是貨物畢竟是在無單的情況下交貨,依然存在很大的風險:按托運人或單證托運人的通知交付貨物后,規則規定成為可轉讓單證的“善意”持有人依然可以向承運人要求賠償,承運人應進行賠償,而上述發出交付貨物通知的人應當補償承運人遭受的損失。同時又規定發出交付貨物通知的人,如果沒有提供擔保的話,承運人可以拒絕執行其交付貨物的指示。《鹿特丹規則》“無單放貨”的規定,不再將單據作為交付貨物一項絕對化的強制性義務,這對改革國際貿易中貨物交付具有重要意義。
其實早在2002年6月,我國最高人民法院也有處理無單放貨的判決:審理菲達電器廠訴美國總統輪船公司無單放貨的案件,就判決船公司不承擔無單放貨的責任。雖然中國不承認判例的法律效力,但這樣的判決還是對后面的案件起到很大的影響,后續也出現了好多類似的判決,但絕大多數承運人被判定必須承擔無單放貨的責任。類似案件卻判決不同,顯示我國相關法律制度的混亂,這也是我國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鹿特丹規則》的這一項規定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值得深入研究。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目前共有1430多個港口,港口吞吐量和集裝箱吞吐量均位居世界第一位,在航貿中作用重大。但到目前我國并未加入前面的三個國際海運公約,我國通過制定《海商法》,將三個公約的相關內容加以確定形式,使我國的海運法規與國際接軌同步。對于是否加入《鹿特丹規則》,還是像以往一樣通過修改《海商法》的方式實現融合,成為各方學者不斷猜測討論的重要話題。無論是哪一種方式,在該規則中大量加重承運人責任的規定,都應引起相關部門的足夠重視。當然,在這樣的大環境下,1992年的《海商法》稍顯滯后,對其的修訂也是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