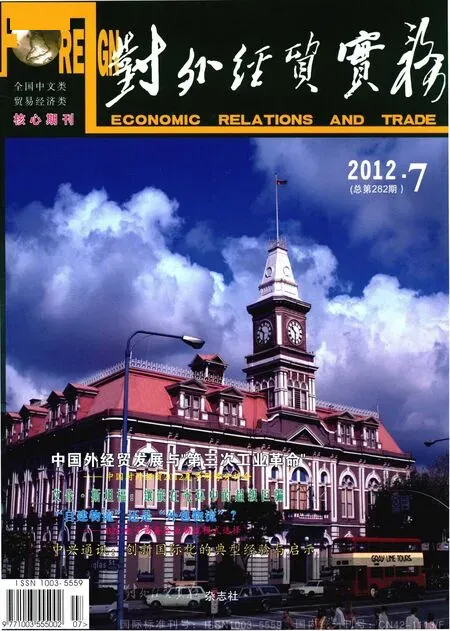中國與東盟貿易的環境規制問題與應對策略
■ 田 野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靳 緯 國家開發銀行
2010年1月中國和東盟如期完成自由貿易區(CAFTA)的建設,正式步入零關稅時代。貿易自由化和產品內分工程度的深化,將進一步擴大中國和東盟之間的貿易,而在低碳經濟背景下,由污染密集型產品貿易引發的資源消耗和污染轉移問題將會給雙邊貿易帶來更大環境壓力。那么,中國和東盟就雙邊貿易和環境問題存在著哪些方面的爭論和摩擦?在區內環境壓力日趨增大的情況下,中國又該如何與東盟各國協調雙邊貿易關系?這將是本文重點研究的問題。
一、CAFTA建立后貿易自由化帶來的環境問題
(一)CAFTA區內貿易帶來的污染轉移
根據《東盟統計年鑒》的數據,2001年自貿區始建之時,中國從東盟進口的產品主要為石油、木材、植物油等資源密集型產品,這類產品貿易額占到總進口額的67.3%。到2010年,中國從東盟進口1546億美元,進口的主體商品已經轉變為礦產品、化工產品、機電產品等污染密集型產品,占到進口額的46.3%。2010年,中國對東盟的出口額為1382億美元,東盟從中國進口的產品主要為紡織品、塑料制品、玩具以及污染密集型制造業的中間產品,其中中間產品進口額達到東盟總進口的14.5%。總體而言,CAFTA建立之后,污染密集型產品貿易成為中國與東盟貿易的最重要部分,而且雙方的貿易稟賦決定了此類產品今后將長期成為雙邊貿易的主體。中國和東盟的污染轉移情況可以用雙邊污染密集型產品的貿易差額來反映,2001年CAFTA建立之后,中國在HS編碼第5類、7類和16類污染密集型產品貿易中一直存在逆差,表明中國從東盟凈進口這些污染密集型產品,將自身的一部分環境污染通過這三類產品貿易轉嫁給了東盟。而在HS編碼第6類和15類污染密集型產品貿易中,中國一直存在著貿易順差,表明中國承接了東盟通過這兩類產品貿易帶來的環境成本。就污染密集型產品整體貿易差額而言,中國與東盟的貿易呈逐步增長的逆差趨勢,這表明自由貿易協定之后,通過雙邊貿易,中國從東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環境利益。
(二)CAFTA區內FDI產生的污染轉移
自貿區始建以來,中國和東盟雙邊直接投資(FDI)迅速發展,雙邊對于污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帶來的產出效應會導致自貿區內環境污染的轉移。根據UNCAD發布的《世界投資報告》,截止到2010年,中國對東盟年平均直接投資額在2億美元之上,投資主要集中在橡膠和塑膠制品、礦產品和電子電氣等污染密集型產業,這種投資的產業結構將一些中國國內的低端和污染型產業轉移到東盟國家,實質上是將此類產業的環境污染通過投資轉移到東盟。2010年東盟對華直接投資額為63.2億美元,東盟已成為中國第五大外資來源地。雖然近年來東盟國家尤其是新加坡對華直接投資開始有轉向服務業的趨勢,然而東盟對中國的投資主要還是集中于紡織服裝、電子電器組裝、家具、石化產品等存在污染密集型產品的產業,這種投資結構同樣會給中國帶來污染轉移。隨著2009年8月中國和東盟簽署《投資協議》,在現有投資結構下,雙邊投資的進一步便利化將會給雙方帶來更大環境污染轉移,而投資產生的污染轉移也必然會引發雙方更大的關注。
(三)CAFTA承接來自區外的污染轉移
中國和東盟不僅要面對區域內各國環境規制帶來的貿易問題,同時也受到了來自區域外貿易的環境壓力。這種環境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首先在國際產品內分工的大環境下,在亞太地區的國際貿易結構中,中間產品貿易規模已經超過了制成品的貿易規模。根據BEC分類法進行統計,中國出口到東盟的零部件貿易額從2001年的47.1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249.39億美元,占中國零部件總出口的近8.9%;零部件進口額從2001年的79.6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564.3億美元,占中國零部件總進口的15.6%,雙邊零部件貿易將近57%來自污染密集型產業。而且中國和東盟均處于國際產品內分工的產品制造鏈條中,雙邊通過簽訂自貿協定降低或取消了中間產品貿易的壁壘,而電子、化工產品等污染密集型的中間產品貿易規模的擴張將會給CAFTA區內帶來新的環境壓力。
其次,區域外的發達國家通過廢棄物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等手段向中國和東盟各國進行污染轉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為發達國家出口電子垃圾和轉移污染工業。根據SVTC的報告,每年全世界80%的電子垃圾被運到亞洲國家,其中90%流入中國。美國每年出口的電子垃圾有大約50~80%的目的地為亞洲國家,英國的電子垃圾中有大約40%出口到中國和印尼。中國和東盟國家一般采用焚燒、掩埋等低廉成本手段處理電子垃圾,會給本國造成極其嚴重的環境污染。另外在低碳經濟新背景下,發達國家可能把本國碳排放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和東盟國家,從而也將碳排放的部分責任轉嫁給中國和東盟國家。
二、中國和東盟各國內部環境規制對貿易的影響
(一)中國的環境規制對雙邊貿易的影響
環境保護問題在“十二五”規劃中得到進一步重視,目前中國國內關于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陸續出臺,由此帶來的環境規制的數量和程度相比以往有顯著提高(見表2)。
中國的環境規制致使來自東盟國家的部分產品進口受限,2009年3月中國商務部最終裁定對原產于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的進口丙烯酸酯繼續維持反傾銷措施。同年,對原產于印度尼西亞和泰國的進口核苷酸類食品添加劑進行反傾銷調查。截止到2012年2月,中國出于國內環境規制而對東盟國家實施的貿易限制措施累計達到10起。
(二)東盟的環境規制對雙邊貿易的影響
自2001年開始,東盟對中國的出口尤其是初級產品和原材料貿易增速加快,另外中國對東盟的投資主要集中在污染密集型產業或者資源密性型產業,因此引發了東盟各國擔心自身通過貿易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污染避難所。東盟各國相繼通過設立相關法律法規對本國進口和引資進行環境規制(見表2)。

表1 近年來中國新制定的國內主要環境規制一覽表

表2 近年來東盟各國新制定的國內環境規制一覽表
由于東盟綠色壁壘而引起的雙邊貿易糾紛,已經屢見不鮮。2007年,菲律賓針對原產地為中國的牛奶、糖果、午餐肉等12種商品實施禁售令,其理由為這類產品存在甲醛超標現象,但并未公布相關檢測報告,也未能得到生產企業的確認。2008年2月,印尼要求所有進口球莖植物必須出具原產國質檢部門的檢驗檢疫證書,并于2009年10月以不符合檢驗檢疫標準為由,強制退回41個貨柜原產地為中國的白蒜。截止到2012年2月,東盟各國出于內部環境規制或者資源節約而對中國實施的貿易限制措施累計達到17起。
三、CAFTA框架下中國應對環境規制的策略
第一,中國應促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中關于貿易和環境問題的運行機制,建立適當的規則來協調貿易與環境的沖突。目前雙方并沒有形成關于貿易與環境問題的協調機制,有關貿易與環境的規定僅限于《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中的“一般例外”條款:只要不在情形類似的有關締約方之間構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視的手段或構成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制,締約方就可以采取“為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對此條款的解釋和操作,雙方還存在一定的分歧,因此給不合理的環境規制留下了空間,僅通過少數成員國自行協調是不足以應對來自區域內外的環境壓力的,需要所有成員國精誠合作,并且要通過一定的制度化安排對環境問題合作加以必要的約束與激勵。另外,目前某些有中國和東盟共同參與的國際環境協定,其對貿易的限制條款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貿易自由化協定是相悖的,因此中國和東盟雙方需要進一步深化區域經濟合作的層次,建立對應的機制以協調國際環境協定與自貿協定的沖突。
第二,中國出口東盟市場的產品應加快提升綠色標準,以減少東盟國家實施綠色壁壘的影響。中國出口企業應在原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或產品生產區段內進行技術更新,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降低出口產品污染密集度,貫徹實施ISO9000、ISO14000標準,使自身產品符合東盟各國國內環境標準,從而形成可持續的出口競爭力,這樣才能在面對東盟的綠色壁壘時更加主動。東盟各國各自的環境標準總體仍參照國際環境標準,中國出口企業應加強與科研機構的合作,參照國際環境標準來要求出口產品,做到清潔生產,盡量爭取國際綠色認證。目前東盟對進口產品尤其是制成品的環境規制對象有從產品轉向包裝的趨勢,相關中國企業須注意出口時要建立綠色包裝體系,做到綠色出口以避免受到雙重綠色壁壘。東盟國家各國環境規制的產品、產業對象繁雜,污染密集型出口企業要建立預警機制,即時收集對東盟目標國國內環境規制的相關信息,提高面對綠色壁壘的反應能力。另外,東盟各國環境壁壘高低不一,中國出口企業可根據東盟各國環境規制的程度進行適當的區位調整,在自貿區內形成多元化市場,以降低環境規制的風險。
第三,中國對東盟的投資項目在產業和區位選擇決策時要充分考慮東盟國家的環境規制問題。從目前來看,東盟國家出于環保目的對本國設置的投資限制主要集中在礦產、橡膠、木材等資源密集型產業,各國政府對于初級產品的國外投資異常敏感,相關中國企業要盡量避開對此類產業尤其是開發項目的投資,可以將投資重點放在目前東盟國家設限較少的資源加工類項目。另外東盟對玩具、電器和紡織品產業設置的是以制定本國環境標準為主的綠色壁壘,而對以上產業投資方面的環境規制并不嚴厲,相關中國企業應抓住時機對東盟進行針對性投資,盡快了解和適應東道國的環境標準,以繞開綠色壁壘。
第四,中國從東盟國家進口的產品應加強環境認證和檢疫、檢驗工作。目前中國對進口產品的環境規制主要采用強制環境認證措施,在對境外供貨商的資格審核過程中,優先考慮三位一體的供貨商,即在中國境外有自己的打包廠或發貨工廠,在中國境內有自己的貿易公司。因此東盟產品尤其是化工產品和固體可再生廢品的進口商和供貨商要考慮到這一政策偏好,以降低資格審核失敗的風險。另外,中國在東盟國家指定的裝運前檢驗機構有限,若進口商進口的東盟產品來自沒有裝運前檢驗機構的地區,要盡量避免要求到貨口岸的檢驗機構派人到出口地區進行檢驗的這種方式,以免產生額外的人力和時間成本,可以在貨物運輸到到貨口岸后由口岸檢驗機構進行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