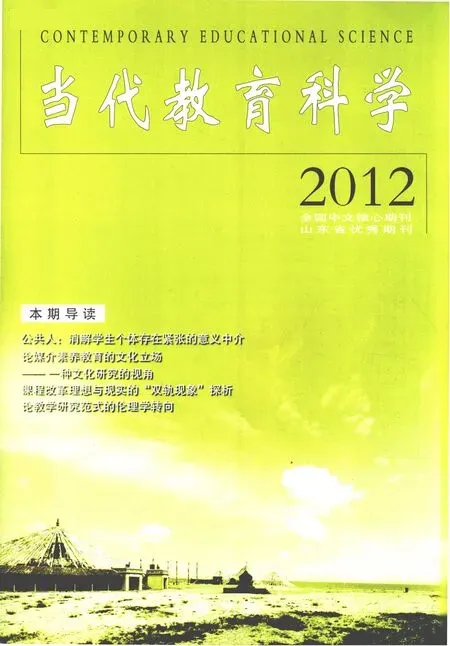教師知識解釋性的困境與出路探析
——基于學科教學知識(PCK)的視角
● 丁 菡 郜舒竹
教師知識解釋性的困境與出路探析
——基于學科教學知識(PCK)的視角
● 丁 菡 郜舒竹
在課堂上向學生傳授知識是教師的基本職責之一。然而當下教師的知識常常缺乏解釋性抑或教師面對知識存在解釋的無力感。這與一直以來的學科知識與教學知識的分離有關系。而具有融合性、建構性和轉化性的學科教學知識是解決教師知識解釋性的一條可行路徑。這需要走向融合的職前教師培養,邁向反思的教師自主發展以及建構合作的教師文化。
教師知識;知識解釋性;學科教學知識
“要給學生一碗水,教師須有一桶水”:這是多年以來社會對教師知識的要求。誠然,沒有一定程度的知識,學校中的教學活動必然將無法開展。那么,反之,是否教師知識量越大,教學活動越有效果呢?教育心理學家經過相關實驗后認為,“教師知識并不是越多越好,超過一定范圍和界線,教師知識就不再是影響學生學業成績的主要因素”。[1]于此,筆者不得不提出疑問:當教師知識量達到一定程度后,為何教學效果卻不甚明顯,甚至是失敗呢?究其原因,恐怕與教師知識的解釋性有關系。
一、教師知識的解釋性困境
(一)何為教師知識的解釋性
在課堂教學活動中,教師不僅要對所教授學科知識的概念、原則或原理有自己正確的理解,還需要掌握如何恰當向學生表征這些概念、原則或原理的方法,后者即屬于教師知識的解釋性。簡言之,教師知識的解釋性指教師如何向學生表征自己所講授的學科知識,使學生清楚明白教師所講授的知識。筆者認為,影響教師知識解釋性的因素有:(1)教師知識的多寡;(2)學生的認知水平;(3)特定的教學情境。教師知識的解釋性包括以下幾個層次:(1)教師對某一知識正確的理解;(2)教師確定學生的認知水平(包括認知能力和認知困難);(3)教師在特定的教學情境下將知識進行重組、調整為學生可接受的知識;(4)教師將知識表征呈現給學生,達到有效的教學。
(二)教師知識的解釋性困境
在學校教學活動中,教師常常陷入知識解釋性的困境。首先,教師知識缺乏解釋性。這樣的教師往往按照自己對知識的理解講授給學生,其結果是教師“口若懸河”,而學生卻“呆若木雞”。眾多新入職的教師會遭遇這一困境。教師未有效地思考學生的認知能力與認知困難,將學生的認知水平定格在與自身等同的水平上。按照伯恩斯坦的觀點,此類教師在教學中使用的語言屬于“限制編碼”[2],即他人無法明白的語言編碼。在教師看來,這些缺少解釋性的知識似乎已經到了學生的頭腦中;而對于學生來說,他們則對教師的語言“不知所云”。毋庸置疑的是,在這樣的課堂上,師生“對話”不可能出現,話語的不平等也會逐漸衍生。這樣的課堂與其說是教學,不如說僅僅是“教”。其次,教師知識解釋的無力感。這類教師在教學中會嘗試著用教育學或教育心理學知識去解釋所講授的知識,并試圖讓學生理解和掌握知識,然而,教師極易忽視特定的教學情境,無法對課堂中臨時出現的情景做出及時的反應。學生對于所學知識的理解也是處于似是而非的狀態,并未完全掌握知識。很多學科教師都會經歷這樣的解釋無力感。
(三)困境原因:分離式的教師專業化
19世紀以來,伴隨著教育學的產生,“人們開始同意這樣的一個原則,即(小學)教師不僅應當知道他們所要教授的科目的知識,也要知道他們進行教學的藝術”[3]。于是,從教師的職前教育到教師在職培訓,都普遍采納了“學科知識+教育科學知識的范式”[4]。“其中一個基本的假設就是,任何具有足夠學科知識的人只要懂得普通教育理論和原則,就能夠將這些理論和原則自覺運用到具體學科、知識點和情境的教學中,提高教學實效。”[5]而恰恰相反,這種專業化教師的培養造成了教師學科知識與教育學知識的分離。在這樣的培養方式中,“學科教育是按照學科知識的理論邏輯展開,教育學科是按照純教育的思維來組織的,學科知識不因教育知識而更加適宜于教學,教育知識也沒能夠在學科知識的教學中彰顯魅力”[6],兩種知識被徹底的分隔開,教師無力用教育學知識去輔助學科教學,教師知識也會相應的缺乏解釋性。這種分離式的教師專業化進程促使教師應該從知識基礎的角度去尋求解決困境的方法。
二、學科教學知識(PCK):教師知識解釋性的可能路徑
(一)學科教學知識的發展
在傳統的將教師學科知識與教育學知識分離之后,眾多教師研究者也洞察到分離的后果。他們也逐漸意識到,教師知識的重點已經不在于擁有多少知識,而在于怎樣將擁有的知識組織、表征給學生,讓學生理解這些知識,即從“教什么”到“怎樣教”。于此,1986 年美國學者舒爾曼(Shulman,L.S)提出了一種新的知識類型——學科教學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簡稱PCK)。他認為學科教學知識是包含在學科知識中的一種屬于教學的知識,是一種最適于“可教性”的學科知識,是“教師個人教學經驗、教師學科內容知識和教育學的特殊整合。”[7]PCK的內容包括“該學科領域內最常見的教育話題,表達思想的最好方式,最有用的類比、樣例、圖示、解釋和演示等易于學生理解的表征方法。也包括教師有關學生對某一主題感到容易或困難的原因,學生的偏見和誤解,消除誤解的策略,特定的話題、問題、論點以怎樣的方式組織表達調適使之適合于不同興趣、能力和背景的學生,幫助或引導學生以個人有意義的方式理解內容的知識。”[8]學科教學知識在舒爾曼看來并不是分散的知識領域,而是一個豐富的融合性的知識,主要包括兩大核心內容:基于教育目的的教學內容重構和向學生傳遞知識的途徑。學科教學知識的提出為教師知識以及教師教育研究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它“突破了以往將教師知識視為學科知識與教育知識單純疊加的觀點,使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能夠第一次真正地有機融合在其中,突出體現了教師知識的專業性和實踐性特征,有利于改變傳統師范教育只重視學科知識學習的局面,為接下來進行的教師專業化發展研究奠定了基礎”[9]。
受建構主義思潮的影響,科克倫(Cochran)等人又對舒爾曼提出的學科教學知識概念進行了增補。他們認為,學科教學知識的形成離不開教師自己的反思與建構,是教師在已有學科知識基礎上綜合學生的認知水平、教學環境重組而成的。這樣,柯克倫等人將舒爾曼的學科教學知識 (PCK)發展為學科教學認知(PCKg),包括學科內容知識、教學法知識、教學情境知識以及關于學生的知識。學科教學認知與學科教學知識相比,更進一步強調了教師對學生和教學情境的依賴性,更符合教學實際。最重要的是,學科教學認知更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主動構建出來的知識,而不僅僅是教師被動習得的知識。[10]
(二)學科教學知識的特征
1.融合性
學科教學知識不同于單獨的知識體系,它是由教師多種知識的內部融合而來的。這種融合也不單單是簡單的將學科知識與教育學知識的總和,而是通過大量的教學實習將它們進行重組形成的。古德蒙茲多蒂爾(Gudmundsdottir)強調“學科教學知識是包含學科和教學兩種知識的融合的結果,正像合金性質已與原先混合之物質的性質不同一樣。學科教學知識的產生,是教師將自己的學科知識以及有關學生、課堂文化和課程知識重組而形成”。[11]在這種重組過程中已經加入了教師本身的價值觀和他們對學科教學的看法。對于掌握大量知識的教師而言,學科教學知識有利于其將學科知識和教學知識融合形成自己對知識、學生和教學情境的獨特理解。而教師在理解的過程中能夠將學科知識過渡成為學生有能力理解的教學知識。只有這樣,教師的知識才具有解釋性,學生才會達到掌握知識的目的,教學才會達到預期的效果。
2.轉化性
學科教學知識的轉化性包括兩個方面:學科教學知識是由學科知識和教學知識通過一定方式轉化而來的,學科教學知識將學科知識轉化為學生能夠理解的知識。首先,馬克斯(Marks)從實際分析小學數學教師的學科教學知識中發現,學科教學知識不僅可以通過學科知識轉換形成,亦可由一般的教學知識遷移到特定主題與內容中的方式衍生出來。有學者分析學科教學知識可以通過三種方式轉化而來[12]:(1)由學科知識轉化而來。教師通過對學科主題的重組和排列,采用有效的方式呈現學科知識,并思考如何將學科知識解釋給學習者的一種知識。(2)由一般教學知識轉化而來。教師通過各種特殊的教學方式結合特定的教學情境,將教學知識轉化為學科教學知識。(3)由學科知識和一般教學知識一起轉化而來,或從原有的學科教學知識中建構而來。教師融合學科知識和教學知識,通過自身價值觀念建構而得到學科教學知識。其次,各種知識通過特殊的方式轉化為學科教學知識,而在這一過程中,學科教學知識已經轉化為學生能夠理解的知識。因為教師在將各種知識融合中對學生的認知水平、特定的教學情境等因素進行了整合,最后將一種符合學生認知水平也適合于教學情境的知識呈現在學生面前,使得知識具有強烈的解釋性。
3.建構性
托賓、蒂賓斯和吉拉德基于建構主義的觀點,從微觀的角度分析了學科教學知識的建構本質。他們認為學科知識、教學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識三者是相互交錯在一起的,不宜單獨分開。學科教學知識的建構性突出體現了教師在形成這種知識中的個體性和價值性。沒有建構的知識對于教師來說只是“死知識”,而課堂教學中教師和學生需要的都是建構后的 “活知識”。教師必須對學科知識進行自我的理解,對教學知識進行自我的探索,對學生和教學情境進行自我的分析,以建構出自己理解并能夠被學生所理解的學科教學知識。建構一方面使得各種知識變得適合于教師教和學生學,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差異性,這種差異即是教師價值觀念和教學方式的不同造成的。例如,同樣是一篇課文,不同的教師會有不同的教學方式,會表征出不同的知識呈現給學生。這也表現出學科教學知識并沒有一個最佳的解釋方式,而只要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與學生、知識以及教學情境相互作用形成,并且符合知識的表征的教學知識都是合理的解釋性知識。
學科知識與教學知識的分離造成了教師知識解釋性的困境,而缺少解釋性的知識只能是教師的“個體知識”,無法成為學生的知識。因此,亟需尋找一種方式使教師知識增強解釋性,而具有的融合性、轉化性以及建構性的特點的學科教學知識似乎是解決這樣問題的一條可能路徑。于是,教師有必要從各個環節建構自身的學科教學知識以增強知識的解釋性。
三、出路探析:學科教學知識(PCK)的建構
依據建構主義的觀點,學科教學知識是由教師自身通過各種途徑建構和完善起來的。
(一)走向融合的教師職前培養
當下以及傳統的教師教育培養幾乎采用“X+X”的分離模式,即學科知識與教學知識分開進行。在教師知識缺少解釋性的當下,這種模式有必要進行改變,建立起融合的教師培養模式。各培養單位在“課程設置上需要增加教學知識的課程比重,包括教學評價、教學策略與教學法、學生的學習特質、課程知識、有關學校情境與文化的教學社會學“[13],讓師范生嘗試著用教學知識去解釋學科知識,去尋找最佳的教學方式,使學生形成宏觀的學科教學知識。另一方面,培養單位還需開設學科課程與教學論知識。對于師范生而言,學科課程教學論是他們獲得學科教學知識的主要途徑。學生在這些課程中對特定教學情境進行體驗,并進行實踐和操作,形成自我微觀的學科教學知識。最后,培養單位還要加大和重視教育見習與實習。只有在教育實習中,學生才能夠將自己的理論的學科教學知識運用于實踐,并在實習中不斷地修正和完善學科教學知識。
(二)邁向反思的教師自主發展
在很長時間以來,“教師的專業發展主要以理想教師為模型,對教師進行培訓和補救,而將教師排除在外”[14]。誠然,我們不否認培訓對于教師的重要性,也不反對對教師進行培養,但是要使教師建構起屬于自身的學科教學知識,教師進行自我反思才是最重要的。因為學科教學知識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特定的教學情境,教師只有將自己經歷的教學情境進行課后反思,尋找課堂上的知識缺少解釋的原因,以備在以后出現類似教學情境時找到突破口。反思的過程也是教師建構的過程。在反思中,教師建構的學科教學知識是帶有自我價值觀的知識,同時,教師建構的也是關于特定的學生、教學情境的知識,是真正屬于教師自己的知識。
教師進行反思的途徑有很多,最為常見的當屬教師撰寫反思日志。教師對自己教學實踐中的各種特殊情況進行反思,對學生進行課后分析,對教學情境進行深一步的認識,對教材以及其它因素都進行反思,以研究者的眼光來審視課堂。例如,當教師面對知識缺乏解釋性時候,有必要在課后對各個環節進行反思: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受哪些因素影響?怎樣解決這些情況?經過反思日志的分析,教師尋找到問題所在,使得以后類似的情境中知識能夠順利的被學生所理解。
(三)建立合作的教師文化
教師要建構學科教學知識來增強知識的解釋性,更需要教師之間從疏離走向合作。首先,要向學科專家教師學習和借鑒經驗。正如舒爾曼所認為的,“學科教學知識是學科教師和專家教師最大的區別”[15]。很多專家教師經過多年教學經驗之后,在實踐中總結出大量的學科教學知識,如怎樣去組織教學,在某種情境下如何向學生表征知識……這些都是教師特別是新手教師需要去虛心請教和學習的。其次,教師之間要經常分享教學經驗以及進行教學研討。鼓勵教師在一起分享自己課堂教學中遇到的困難和解決方法,大家進行互動,深挖各自身上的“緘默知識”[16]。只有建立合作的教師文化才能使教師獲取更多的教學方法,掌握更多的教學經驗,形成和鞏固學科教學知識。
教師知識解釋性在課堂教學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其直接關系到教師的教、學生的學以及整個課堂效果。而知識的解釋性又涉及到課堂上眾多因素,因此沒有特定的標準方法去增強知識解釋性。盡管當下學科教學知識也備受質疑,但是其對于增強知識解釋性和提升教學質量的確有十分明顯的效果。
[1]鄭金洲.教育通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328.
[2][英]伯恩斯坦.社會階級、語言與社會化[C].厲以賢.《西方教育社會學文選》[A].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453.
[3]Monroe P.A.Cyclope dia of education(Vol.4.)[M].New York:Macmilla,1913,622.
[4]唐澤靜,陳旭遠.學科教學知識視域中的教師專業發展[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5).
[5]高芹.PCK:教師知識從“缺失的范式”到本體價值回歸[J].教育導刊,2011,(7).
[6]胡青,劉小強.分離還是融合:教師教育專業化中形式與實質的矛盾[J].江西社會科學,2005,(11).
[7]Shulman,L.S.Those Who Understand:Knowledge Growth in Teaching[J].Educational Researcher,1986,15(2):4-14.
[8]Shulman,L.S.Knowledge and teaching:Foundations of the New Reform[J].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1987,57(1):1-22.
[9]唐澤靜,陳旭遠.“學科教學知識”研究的發展及其對職前教師教育的啟示[J].外國教育研究 2010,(10).
[10]Cochran,K.F.Pedagogical Content Knowing:An Integrative Model for Teacher Preparation[J].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1993,(4):238.
[11]Gudmundsdottir.Values in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J].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May-June,1990,41(3):44-52.
[12][13]袁維新.學科教學知識:一個教師專業發展的新視角[J].外國教育研究,2005,(3).
[14]操太圣,盧乃桂.教師專業發展新范式及其在中國的萌生[J].教育發展研究,2002,(11):71-75.
[15]邵光華.教師專業知識發展研究[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38.
[16]石中英.緘默知識與教學改革[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3).
丁 菡/首都師范大學初等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英語課程與教學論 郜舒竹/首都師范大學初等教育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數學課程與教學論
(責任編輯:劉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