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會資本與大學生就業滿意度關系研究
鄭茂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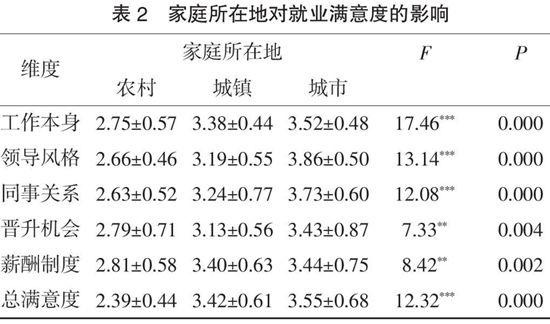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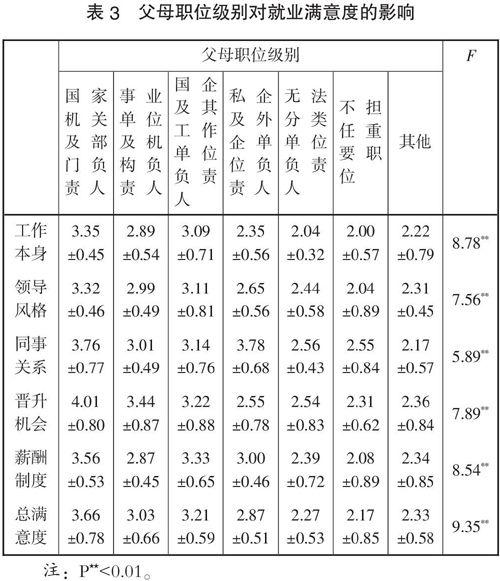
摘 要:中國社會是人情社會,關系、人情、面子、財富和權力等級等先賦性因素占據社會的重要地位。社會資本“強關系”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大學生就業機會上,而應該深入分析對大學生的就業質量的影響,尤其是對大學生就業滿意度的影響。本文擬以家庭為基點,綜合地位結構觀與網絡結構觀兩種理論視角,把就業滿意度作為大學生就業的重要指標,探討家庭社會資本對大學生就業滿意度的影響。同時,對家庭社會資本容易造成的關系就業、內部招聘問題進行探討。
關鍵詞:大學生;就業滿意度;家庭社會資本
基于大學生就業難的社會現實,就業問題已成為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學者們從經濟發展水平、勞動力市場、教育體制、就業制度和大學生個體特征、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陳成文等,2004;陳海平,2005;宛恬伊,2005;鄭美群等,2005;胡永遠等,2007)。家庭是大學生社會資本的主要來源,對于大學生而言,在走出校園之際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父母擁有的社會網絡和資源(鄭潔,2004;李黎明等,2008;)。因此,本文擬以家庭為基點,綜合地位結構觀與網絡結構觀兩種理論視角,把就業滿意度作為大學生就業的重要指標,探討家庭社會資本對大學生就業滿意度的影響。
一、文獻回顧和問題的提出
大學生就業屬于職業地位獲得的研究范疇。在職業地位獲得研究中,最有影響的是布勞-鄧肯地位獲得模型。他們具體分析了先賦地位(以父母的地位為操作尺度)和自致地位(指個體經后天努力獲得的角色地位,如教育、工作經歷等)對個人職業地位獲得的影響。布勞和鄧肯(1992)及其后來者對歐美國家的研究都表明,家庭背景中父母的職業地位(特別是父親)與教育水平對子女的職業獲得(首次工作或當前職業)具有顯著性正向影響。布勞-鄧肯地位獲得模型表明:父輩的職業地位越高,子輩獲得職業成就的可能性就越大,就業的質量、工作滿意度、收入也就相對越高;而父輩的高文化程度可以轉化為一種資本,一種對較高階層文化的掌握和了解,從而有利于從社會關系網中獲取子輩求職所需的信息或者幫助子輩獲得職業提升的機會。但布勞-鄧肯模型只說明一種事實或現象,并沒有說明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職業地位究竟通過什么樣的機制影響子女的職業地位。[1]
與布勞和鄧肯有所不同,格蘭諾維特(M.Granovetter)更注重從動態視角去看待勞動力市場的配置問題。在對人們求職及職業流動過程的研究中,格蘭諾維特將社會網絡與求職和職業流動聯系起來,并提出由于社會關系網絡嵌入人們求職和職業流動過程之中,因而關系通常會發揮信息橋的作用,解決了勞動力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幫助求職者更容易獲得新的工作。可以說,在勞動力市場上,是社會關系而非制度或普遍道德能夠產生信任。格蘭諾維特在其社會網絡理論中,既提出了嵌入性(embeddedness)假設,也提出了“弱關系”(weak tie)假設。其把社會網絡帶回到勞動力市場分析之中,彌補了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價格—效益分析模型過于抽象和單調的缺陷,讓人們認識到現代經濟活動同樣也嵌入社會關系之中,而不是孤立于人際關系之外。[2]
和格蘭諾維特一樣,邊燕杰也非常關注關系網絡在社會中的作用。不同的是,邊燕杰運用1988年天津市的調查數據,檢驗了與格蘭諾維特相反的“強關系”理論假設。無論在計劃經濟時代還是在向市場轉型的體制中,“強關系”的作用都非常明顯。“強關系”之所以在中國一直在起作用,與“權力維續”的社會體制可能有一定的關系。權力在社會資源分配中的重要地位為人情關系交易提供了存在空間。[3]
林南將關系網絡與社會資本聯系起來,認為社會關系網絡涵蓋了多種社會資源,人們可以通過網絡來獲得自己想要的社會資源,因而關系網絡也就成為重要的社會資本,成為影響社會結構和個人行動的重要力量。[4]
國內學者通過大量實證研究證明社會資本和社會網絡與大學生就業關系顯著。一是社會資本對大學生成功就業的作用得到大學生的高度認可(許曉青、趙耀,1994;陳成文、鄺小軍,2004);二是社會資本成為大學畢業生首選的求職渠道(陳成文、譚日輝,2003);三是社會資本對就業質量的影響(徐莉、郭硯君,2010);四是社會資本對就業滿意度的影響(姜繼紅、汪慶堯,2007);五是社會資本對前途選擇與就業意向的影響呈顯著的正相關(鄭潔,2004)。還有學者認為,地位獲得體現為制度安排機制(權力授予關系、市場交換關系)和非制度安排機制(社會關系網絡),并認為非制度因素在中國社會群體成員地位獲得中具有獨特功能(張宛麗,1996)。
然而,在眾多的研究中,筆者發現有幾個不足:一是局限于關系網絡研究職業獲得的多,而對家庭經濟地位對職業獲得的研究不夠。家庭經濟地位在影響職業獲得的同時,是否影響家庭關系網絡,研究不深入。二是家庭社會資本不管是定義、內涵或研究脈絡均不是很清晰。有的學者把家庭社會資本當成社會關系或社會網絡(尉建文,2009),有的學者把家庭社會資本當成家庭經濟地位(鄭潔,2004),很多學者把家庭社會資本的指標量化為父親職業、父親教育、家庭收人等具體變量(李黎明、張順國,2008)。其實家庭社會資本既屬地位結構研究的范圍,也屬于網絡結構分析的范疇,同時地位結構影響著網絡結構。三是將社會資本作為信息橋來研究大學生就業機會的多,而將其作為強關系研究其影響就業質量或就業滿意度的少。
因此,本研究一是綜合地位結構觀和網絡結構觀來研究家庭社會資本,把家庭作為地位和網絡的交匯點,把家庭作為“先賦因素”、“強關系”、“人情網”的基點,分析其地位結構及其網絡結構與就業三者的關系;二是研究家庭社會資本在成功就業的核心層——就業滿意度中的作用;三是對家庭社會資本的負面影響進行分析。
二、研究設計
(一)變量的界定
家庭社會資本:Marjorbanks和Maboya(2001)認為家庭社會資本主要是指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對個體來說,家庭中的父母是重要的家庭社會資本主體。家庭社會資本主要來自父母對個體的期望以及關系強度。 [5]Goddard(2003)認為社會資本一定是嵌入在某種社會關系中。但是普通的社會關系不一定都是社會資本,只有那種具有相互信任的社會關系網絡才可能形成社會資本。[6]張娟(2008)認為家庭社會資本主要是圍繞家庭中父母的社會關系形成的可利用的資源。家庭社會資本就是以家庭為基點的父母的主要社會人際關系。[7]歸納以上的家庭社會資本討論,本研究認為,家庭社會資本是社會資本的一種重要形式,是以家庭為基點,以信任、規范、制度或責任等為基礎建立的社會經濟地位和人際關系網絡。家庭社會資本可以轉換為在家庭成員之間流動的物質資源和非物質資源,如:資金、信息、關注、照料和情感依靠等。
就業滿意度:Hoppock(1935)認為工作滿意度是從員工的心理和生理上兩方面測量的。員工對工作環境和工作本身都有主觀感受,如果主觀感受和實際工作情況有出入,滿意度就會相對較低;而如果對工作情景期望和實際情況相符,滿意度相對會較高。[8]張凡迪(2003)認為工作滿意度就是個人對工作預先有一個主體的認識,這種認識形成了一個參考框架,當真正的工作比較符合這個參考框架時滿意度就比較高,反之比較低。[9]蔡林亮(1993)認為一個人的工作滿意度不僅僅受員工的期望值影響,也受員工是否感到公平的影響。當一個人感覺自己的付出與收獲成正比,公平感就較強,滿意度就較高。[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