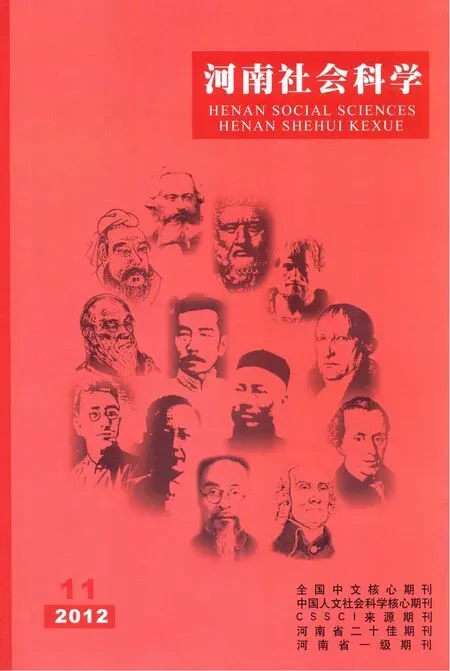論民事補償制度
高留志
(鄭州大學 法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補償制度在行政法的研究已較為深入,雖然我國民法中規定了多種補償制度,但長期以來學者對民事補償很少關注。在《侵權責任法》對緊急避險行為人補償、暫時喪失意識行為人補償和可能的建筑物使用人補償等三種補償制度予以規定后,民法中的補償制度已有相當規模。但對于補償制度的性質如何認定、如何適用補償制度,理論上存有爭議,司法實踐中也有不同的做法。本文擬從理論上對民事補償制度管窺,以向各位大家求教。
一、民事補償的含義
何謂補償?《現代漢語詞典》釋義,補償是抵消(損失、消耗)或補足(缺欠、差額)①,意思是指在某個方面有所缺失,而在另一個方面有所獲得。《牛津法律大辭典》以征收補償為例對補償的法學含義作出說明:“付給受損害影響的人的一筆錢,如因他們的土地被強制征收。”②我國法學理論對補償的探討也是最先起源于行政補償。關于行政補償的含義,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行政補償是行政機關對于其在沒有侵權行為和破壞契約的情況下,由于合法的行為對公民造成的損害所給予的補償③,或者是國家對行政機關及工作人員的合法行為造成的損失給予的補償④。學者的表述盡管略有差異,但均認為行政補償以合法行為為前提,是對合法行政行為給公民或者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失所進行的救濟。我國民法理論主要在探討侵權責任法的功能時使用補償的概念。民法學者在兩個意義上使用補償的概念:在抽象的意義上,補償指對損失任何性質的填補;在具體的意義上,補償與賠償相區別,前者專指對合法的行為造成損失的填補。
筆者對民事補償界定如下:所謂民事補償,是指由非基于違法行為而對受害人的損失予以填補的民事法律制度。具體有三層內涵:(1)民事補償以損失的存在為前提。在民法上,損害的類型包括妨礙、危險和損失等。對于妨礙和危險,可由當事人排除或者消除,沒有另行進行補償的必要。(2)民事補償非基于違法行為而發生。損失發生后,違法行為人對受害人損失的填補,適用民事賠償制度。當然,此處所說非基于違法行為而發生,并非指造成受害人損失的行為不是違法行為,而是補償人一定不是違法者。(3)民事補償與行使國家職權無關。在行政法中,行政補償是基于國家職權的行使而發生的補償;而當事人作為平等的社會成員之間發生的一方對另一方損失的填補,才是民事補償。
二、民事補償的理論根據
在違法行為致他人損害時,由行為人對受害人損害承擔賠償責任,是矯正正義的要求。但非違法者在并不具有可歸責性時,為何須對受害人進行補償,殊值思考。規定受益人的補償義務在客觀上有助于弘揚正氣,有利于發揚中華民族扶危濟困的良好道德風尚。他的分析是從國家和社會整體角度論述補償制度正當性的,但是,補償是受益人對見義勇為者的補償,對于受益人為何須對見義勇為者予以補償,他認為屬于特定條件下的損失分擔⑤。不過,損失分擔說仍有一定的不足之處。因為在有的情況下,受益人可能要填補受害人的全部損失,這就不是損失的分擔,而是損失的承擔了。而且損失分擔也是規則,其背后的價值考量仍需進一步探究。
從社會整體結構看,雖然補償制度具有重要性,但它也不過是整體系統的需要,并無必要考察道德背景。功利主義者認為,個人能達到他自己的最大利益,一個社會也能按同樣原則去行動。一個社會,當它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增加滿足的凈余額時,這個社會就是安排恰當的⑥。補償制度反映了社會系統各功能子系統的互補,當然對社會是有利的安排。但是,把社會類比于個人就不能從連續性上研究,所以從社會整體來看補償制度無涉道德。另外,功利主義以中立的個人為基礎,把人際關系看成個人內心的體驗,把補償看做個人自利的選擇。
而在社會中,個人都不是完全獨立的實體,其行為與其他人的連續性關系是普遍的。為了說明補償制度的合理性,基斯克(Jeske)提出了半補償理論。在基斯克看來,不能把人際關系化約為個人內心的體驗。但人際之間的心理連續也是有層級的,有心理連續性的人和完全是陌生人之間存在不同的道德邊界。如果某人提供了更大的利益給和他有心理連續性的人,他就半補償了他所施加的負擔⑦。半補償理論有助于解釋為什么能合理地被要求承受某種對于我的親朋好友的責任,而不必要求我承擔對陌生人的責任。雖然半補償概念為社會中的補償提供了合法理由,但在現代社會,匿名性、抽象性已經越來越突出,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以熟人為主體而是一個以陌生人為主體的社會,因而用它對于對陌生人進行的補償加以解釋,理由還不充分。
倫理學者曼特古(Montague)在其《補償的權利和義務》一文中論述了補償制度的道德根據。如何解決他人的權利與修復義務之間的困境?曼特古借用表面義務與實際義務的區分予以說明。后者是一種對等的、以平衡利益為目的的義務,而表面義務是一種具有約束力的道德義務,除非它在某種特定狀況下與另一表面責任相沖突、競爭進而被凌駕取代,這種義務就是必要履行的。所以,適法情形下的補償是表面義務使然。經過這一轉換,補償的根據就變成了對受害人的感激⑧。無疑,這種解釋較為圓滿地說明了對適法侵害行為的受害人進行補償的正當性。
三、民事補償的類型
對適法事實所致損害的補償如何實現?美國倫理學家阿穆德(RobertAmudur)提出了三層級的補償體系:(1)補償首先應由制造不公正的人來承擔;(2)補償其次應由那些因不公正而受益的人來承擔;(3)如不能辨明制造不公正的人或因不公正而獲益的人,補償應由共同體來承擔⑨。事實上,我國民法規定的行為人補償制度、受益人補償制度和共同體補償制度正是與此相應的三個類型。
一是行為人補償制度。所謂行為人補償制度,是指因某人的適法行為造成他人損失時,由行為人對受害人所受損失予以填補的制度。我國民法規定的行為人補償制度包括:緊急避險中避險人補償制度、暫時喪失意識行為人補償制度和相鄰關系中行為人補償制度。在行為人補償制度適用的場合,行為人的行為直接使其本人受益。行為人未違反民事義務,對于受害人損害的發生也沒有應受非難的道德過錯,這只是其不承擔侵權責任的原因。法律規定行為人在其合法行為致害的情況下對受害人的損失予以補償,在本質上是使受害人因行為人合法行為所作出的犧牲,以及行為人對受害人感激的道德義務法律化。適用行為人補償制度,也不會出現受害人的權利與行為人的權利在同一客體上發生沖突的困境。
二是受益人補償制度。所謂受益人補償制度,是指當行為人因第三人的行為或者自然事實而遭受損失,受益人因行為人的行為受益時,由受益人對行為人遭受的損失予以填補的制度。我國民法規定的受益人補償制度包括:見義勇為受益人補償制度、雙方均無過錯時受益人補償制度和幫工活動受益人補償制度。與行為人補償制度適用的場合不同,受益人補償制度一般適用于有三方當事人的法律關系(自然原因致害的情況除外)。在三方法律關系中,侵權人是加害的一方,行為人是對加害行為進行阻止、對受益人進行救助的一方,而受益人是因行為人的救助行為或者阻止行為其損害被避免的一方。此種情形下,行為人所受損害本應由侵權人承擔責任,但當侵權人不明或者侵權人無力承擔責任時,行為人就難以獲得有效的補救。法律規定受益人對行為人所受損失予以補償,本質上是使行為人因救助行為或者阻止行為作出的犧牲,以及受益人對行為人感激的道德義務法律化。還需注意的是,由于受益人補償制度通常適用于有第三人因素參與的場合,如果第三人或者其他救濟手段能夠填補行為人的損失,受益人即不需要對行為人予以補償。尤其是侵權人不明或者侵權人無力承擔責任而由受益人補償的情形,受益人不應是不利后果的終局承擔者。如果作為第三人的侵權人確定或者恢復了經濟能力,受益人當然應享有追償權。
三是共同體補償制度。所謂共同體補償制度,是指因公共利益或者整體利益的需要造成某人損失時,由集體對受害人所受損失予以填補的制度。我國民法規定了兩種情形下的共同補償制度:征收補償制度和征用補償制度。共同體補償制度是辯證處理個人與集體關系的結果。集體的存在,最終是為了維護個體的利益,真實的集體無疑是由個人組成的集體。真實的集體不但要求其成員為集體的發展作出貢獻乃至犧牲,同時也應充分實現和保障集體成員個人的正當利益,并讓集體成員產生歸屬感和認同感⑩。因而集體主義的道德內在地包含了補償的道德規范,法律規定共同體補償制度,本質上是使個人為集體利益所作的犧牲以及集體對個人感激的道德義務的法律化。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侵權責任法》第八十七條的規定。該條規定雖被認為也是一種補償制度,但我們很難在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與受害人之間建立感激關系。一方面,無論是建筑物的拋擲物還是墜落物造成他人損害,都是一種違法的侵權行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這與補償制度建立在合法致害基礎之上的理論前提不符;另一方面,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不是行為人,也不是受益人,還不能代表共同體,受害人并不是為他們做犧牲而遭受損害,他們也不需要對受害人有感激義務。所以,無論如何對該條的正當性進行辯護,都難以讓人完全信服。
四、民事補償的性質
非違法者對他人的損失予以補償,無疑是一種負擔。但對于此負擔的性質如何認識,存有爭議。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民事補償是一種民事責任。有學者明確提出民事補償責任的概念,認為民事補償責任是指民事主體基于特定的事由或者原因,依法應向受損害人承擔的以補償財產義務為內容、帶有彌補損害特性的特殊民事責任[11]。另一種觀點認為,民事補償是一種民事義務。王利明教授就受益人補償制度指出,受益人的補償,不是一種法律意義上的責任。因為法律意義上的責任都是違反義務的結果,而在受益人補償制度適用的場合,受益人僅僅只是受益而并沒有違反任何義務,所以不能使受益人承擔責任,而只能使其承擔補償義務[12]。
筆者認為,民事補償的性質如何,是一個純粹的法哲學范疇邏輯問題。根據我國法學理論,無論對法律義務與法律責任的關系有何認識分歧,都對無義務則無責任這一基本原理沒有爭議,即法律責任的設定必須以法律義務存在為前提,法律責任應當是違反法律義務的必然后果。無法律義務規定,則無法律責任的承擔。之所以這樣認識,在于國家要求一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理由就在于這個人對義務表示過同意[13]。在民事義務與民事責任的關系上,只要把民事責任看成是違反民事義務的法律后果,就只能認為民事義務是民事責任的存在前提。沒有民事義務的存在,必沒有民事責任的承擔。由于民事義務和民事責任對當事人而言都是不利的負擔,所以在具體情形下如果看不到民事義務的預先設定,就只能把法律規定由當事人承擔的不利后果看成是民事義務。
就民事補償而言,無論是行為人、受益人還是共同體予以補償,都是建立在適法事實的基礎上的。所以補償制度適用的場合,都不存在法定或者約定的民事義務的違反,否則,就要承擔違約或者侵權責任。既然行為人、受益人和共同體的補償都不是違反民事義務而引起的,那么這樣的負擔仍應處于自由的范疇從而屬于民事義務。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一百五十六條的規定看,“因緊急避險造成他人損失的,如果險情是由自然原因引起,行為人采取的措施又無不當,則行為人不承擔民事責任。受害人要求補償的,可以責令受益人適當補償”,其中明確受益人的補償不是民事責任,也只能認為法律規定的補償是設定了民事義務。
五、民事補償的范圍
民事補償的范圍如何,即如何認識補償數額與損失數額的關系,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實踐問題。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一是有限補償說。根據這種觀點,民事補償的范圍只能是損失的一部分[14]。在《侵權責任法》頒行后,有學者對侵權責任法中的補償和賠償進行區別時認為,“補償不是賠償,賠償一般是填平原則,即受損多少賠償多少,而補償僅是其中的一部分”[15]。二是全部補償說。根據這種觀點,民事補償的范圍等于損失[16]。三是合理補償說。根據這種觀點,民事補償的范圍不應大于損失,具體數額根據雙方的情況確定[17]。可見在民事補償范圍的問題上,學者有較大爭議。尤其是還有人認為民事補償的范圍可以與損失的數額相同,因適法事實而生的民事補償與因違法行為而致的民事賠償其區別何在?如果不能發現民事補償與民事賠償范圍上的區別,規定兩種不同的制度,其必要性令人生疑。
筆者認為,前文關于民事補償性質的探討對民事補償范圍的確定具有先決的意義。因為民事義務和民事責任在范圍上是有區別的:由于民事義務是義務人在履行期間是自由的,如果在民事義務的履行期間權利人的利益因民事義務未能盡早履行而有所減損,義務人就無須就此損失向權利人負責。而民事責任的承擔,從民事責任的產生之時就是責任人不可逃避的負擔,他本應在民事責任產生之時即應承擔。如果承擔民事責任的時間遲于民事責任的產生時間,則因時間的推移而對權利人造成的更多損失理應由責任人負擔。所以,在確定損害賠償的范圍時,間接損失計算的時間起點也應是民事責任產生之時。由于民事補償是一種民事義務而非民事責任,那么補償就不具有懲罰性,其范圍應限于直接損失。當然,由于民事補償制度適用的具體情形不同,將補償的標準限定為直接損失的范圍仍是一種原則。如若以直接損失為標準顯失公平,例如在受益人補償制度適用的場合,當受害人損失較大而受益人獲益較少時,還可采取其他的標準確定補償的范圍。
注釋:
①《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00頁。
②[英]沃克:《牛津法律大辭典》,李雙元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頁。
③王名揚:《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頁。
④羅豪才主編:《行政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頁。
⑤[12]王利明:《侵權行為法研究》(上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312頁。
⑥[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頁。
⑦Diane Jeske,“Persons,Compensation,and Utilitarianism”,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93,102(4).
⑧ Philip Montague,“Rights and Duties of Compensation”,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84,13(1).
⑨Robert Amdur,“Compensatory Justice:The Question of Costs”,Political Theory,1979,7(2).
⑩聶文軍、張群穎:《論集體主義道德的補償規范與現實的利益補償制度》,《道德與文明》2006年第1期。
[11]黃龍:《民事補償責任研究》,《廈門大學法律評論》2004年第2期。
[13]張恒山:《法理要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頁。
[14]馬新文:《見義勇為行為受益人的民事補償原則探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
[15][16]王勝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解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39、428頁。
[17]李珍:《淺析民事補償責任的基本屬性》,《法制與經濟》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