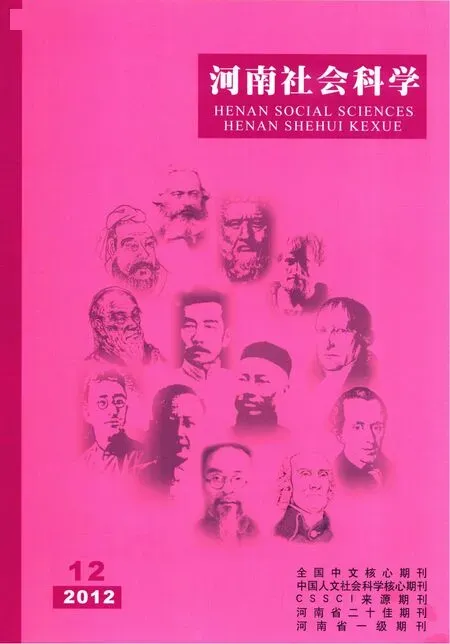制度與行動:城市貧困群體的生存邏輯——基于社會互構論視角
黨春艷
(華中師范大學 社會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一、引言
20世紀末,我國進入社會轉型加速期,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和經濟體制轉軌的不斷深化,國有企業改制、原有單位解體或重組帶來了大規模結構性失業,城市貧困問題日益嚴峻。對此,社會各界給予了高度關注,并從各個維度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和實踐,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受社會學個人與社會、行動與結構二元對立的理論預設的影響,在對城市貧困的研究中,也出現了與社會學二元對立相應的研究范式,在對致貧因素的探討和扶貧實踐的嘗試中均帶有個體主義范式和結構主義范式對立的傾向。鑒于此,本文另辟蹊徑,以城市貧困群體成員的社會適應性為根本出發點和立足點,在互構論的理論視角下,把個體與社會通過制度聯系起來,以制度與行動的“互動”、“互構”及協同演進來探討城市貧困群體在面臨國企制度變遷背景下遵循的適應行動與策略,以及國家救助制度建構下的行動選擇,旨在探討其內在生存邏輯,達到對城市貧困群體成員行動選擇的“具象”性認知,從而建構更合理的貧困救助制度。
二、制度變遷與行動回應
(一)制度變遷與貧困
林毅夫曾將制度變遷分為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前者指一群(個)人在響應制度不均衡引致的獲利機會時所進行的自發性變遷,后者指由政府法令引致的變遷[1]。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結構轉型過程中,主要的城市制度變遷表現為國家政策的調整帶來的制度變革,這種變革集中表現為體制改革中的企業制度變革。我國的國企制度改革是一種典型的強制性、漸進性的變革。強制性表現在這種改革是通過國家政策調整實現的,政府是制度變遷的主導者和推動者,漸進性表現在我國的企業制度改革中不是同時推進的,而是分階段進行的。伴隨著國家政策的不斷調整,市場逐步在資源分配中占據主導地位,以前靠計劃分配資源的格局被打破,社會群體與個人因占有資源的不同,其生活機遇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納在描述改革以前社會主義國家和企業組織的關系時將其比喻為五種不同類型的父子關系。即:(1)實物給予——被動接受的關系;(2)實物給予——主動表達愿望的關系;(3)貨幣津貼關系;(4)自立——有助的關系;(5)自立——無助的關系[2]。五種不同父子關系體現的是不同程度的父愛主義,第一種父愛主義最強,依次遞減,第五種父愛主義最弱。改革以前,我國的國有企業(單位)與國家之間也存在著父愛主義,但企業和國家之間的這種父愛關系,在我國由于個人依附于企業(單位),而企業(單位)又完全依附于國家進而表現為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父愛關系。因為在我國,企業(單位)并不具有經營自主權,其主要的生產經營活動及收入分配、人事安排等都受國家指令計劃的嚴格約束,可以說,企業(單位)是全面依附于國家的,所以,科爾納所說的這種企業與國家之間的父愛關系在我國實際上就表現為個人與國家之間的一種父愛主義關系。具體表現為:一方面,個人沒有選擇自己單位、職業的自主權,國家用統一分配的方式安排他們就業,所謂“我是黨的一塊磚,哪里需要往哪搬”,而且一旦就業,就固定在某一單位,沒有流動的自由和空間;另一方面,作為父愛的表達,國家給予個人全方位的照顧和關愛,不僅僅給予一份穩定的工作,使個人有固定的工資來源,還給予住房、養老、醫療、子女教育就業等幾乎是從搖籃到墳墓的一切基本生活保障等。
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中,國有企業改革日益深化,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不斷改變,在國有企業改革經歷了雙規制時期的“擴權放利”、“利改稅”階段和改制時期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減員增效等階段后,國有企業的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企業獲得了較多的經營自主權,但同時,企業從國家獲得的父愛主義的關照在不斷地消減甚至消失。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這種父愛關系因國家與企業關系的變化而逐漸發生了改變。一方面,個人有了選擇就業單位和就業崗位及在不同單位企業流動的自主權,另一方面,伴隨著個人自主權的增加,國家也減少了對個人的照顧和關愛,個人同時失去了幾乎涵蓋生、老、病、死的一切福利保障,作為制度變遷中的失業下崗人員也因此淪為城市貧困群體。
(二)生存危機下的行動選擇——積極的抑或消極的對抗
李漢林指出:“當一個社會中的制度本身在發生著變遷的時候,當一個社會中的制度試圖重新定義社會角色和社會地位,重新規定這些角色和地位的行為規范的時候,人們的行為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也就會不可避免地產生迷茫和無所適從。換句話說,失范的行為傾向也就會變得不可避免。”[3]隨著國企改革的不斷深化,相對于以前的單位制,個人有了較多的選擇就業單位和就業崗位的自由,但同時伴隨的是單位制下的社會福利保障的全面失去,面臨著結構性資源的約束,加上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單位體制的依賴慣性,及個人知識、技能等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差異,因此,對大多數個人而言,這種選擇的自由更多地體現為一種理論上的存在,他們更多面臨的是工作的無保障、生活的艱難與不確定、福利保障的損失,相當一部分失業下崗人員喪失的不僅是以前工人老大哥身份帶來的榮譽和地位,以及由此升華出的自尊,更多的是很多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沒有收入,或者收入遠低于維持基本生活的需要,他們面臨著不堪忍受的生存境遇。在這種生存危機下,他們很可能走向暴力對抗,進行積極的抑或消極的對抗。
從行為特征的角度看,積極的對抗指城市貧困群體通過堵馬路、靜坐和示威等方式給當地或上級政府施加壓力,以此希求自身的問題能夠得到解決。據公安部門統計,1998年到1999年兩年間,因企業拖欠職工工資、退休金、養老金等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占全國群體性事件總數的1/3左右[4]。年齡越大的人越容易采用這樣的行為策略。
消極的對抗是指作為城市貧困群體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以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和憤恨。吳清軍通過對東北老工業基地C市一個典型的單位型社區一拖拉機廠社區的研究發現:該社區自1997年7月工廠拖欠工資以來,部分職工家庭就開始陷入貧困。在拖欠13個月工資期間,社區內已經有兩人因生活困難自殺了。到目前為止,在過去的七八年時間里,有十幾個下崗失業職工自殺,以至社區里的職工對自殺事件的反應從一開始的“原來在上班的時候聽說一兩個年紀不大的人死了,大家覺得很驚訝”到現在的“大家好像習以為常了”,從該社區自殺的人數及職工的反應可以看出,陷入貧困的失業下崗人員自殺似乎已經成了一件極其平常的行為,這種漠然一方面揭示了自殺行為作為一種非常規行動的常規化,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對貧困者自殺行為的理解和接受。在我們調查的對象中,也有人表示:“實在受不了這種折磨了,窮的滋味真不好受,有時候真想一死百了了。”這些聲音或許就是他們對目前狀況最真實的感受和表達[5]。
三、制度建構與行動選擇
(一)制度建構
緣于對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的需求,針對城市貧困發生的特殊背景,國家通過一系列制度的建構補償城市貧困群體在社會轉型期因制度變遷帶來的利益損失,向他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城市貧困群體基本生活的保障是通過多層的制度建構起來的。第一層次是預防性制度的建構,主要包括最低工資制度和失業保險,這兩個制度的建構使在崗的職工能獲得基本工資,使暫時不能即時就業的人員依靠失業保險維持基本生活。我國城市的失業保險制度是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配合經濟制度改革而建立起來的。1993年4月,國務院頒發了較為完善的失業保險政策《國有企業職工待業保險規定》,覆蓋到所有國有企業職工;1999年,國務院頒發了《失業保險條例》,將覆蓋范圍擴大到城鎮所有企事業單位及其職工,該條例的頒布使我國失業保險步入了較為完善的階段。
第二個層次是再就業政策的建構。再就業政策主要是為增強貧困者應對社會風險擺脫貧困的能力而設置的。我國以各種形式頒布了一系列有關再就業的政策文件,積極推進再就業工程,幫助下崗失業人員盡快就業,以從根本上擺脫貧困的困擾。同時,國家根據再就業工程的政策規定,其他相關部門也陸續出臺相應政策配合再就業工程的推進,如再就業優惠政策,安置失業下崗職工的單位和失業下崗職工本人,可以享受一定優惠政策和資金扶持。
第三個層次是救助性制度的建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為保護城市貧困群體的最后一張安全網,它對處于貧困線以下的社會群體實行以家庭為單位的人均差額補助。據有關學者統計,到2001年年底,享受低保人數達到1170.7萬人,2002年年底為2064.7萬人,2003年年底為2246.8萬人,2004年年底為2200.8萬人,2005年年底為2232.8萬人[6]。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向城市貧困群體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使其基本生存能夠維持。
在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針對出現大量下崗失業人員而建立起來的預防性制度、再就業政策,為他們提供了免于陷入貧困的保護網。作為救助性制度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為貧困群體提供了一種基本的生活保障,這種生活保障展現的是一種生存倫理,生存倫理意味著應當通過一種合適的分配機制或幾種分配機制的共同作用來保證一切人都處于適當的生存地位。在任何社會,個體處于適當的生存地位是極其重要的,對于轉型期的城市貧困群體來說,一旦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對轉型過程中利益損失的承受能力將大為提高。
(二)滿足生存利益的行動選擇——從事非正規工作
改變自身所處的貧困境遇是城市貧困群體一種內在本能的訴求,他們也必將將這種本能的訴求付諸行動。作為最早對工人地位及行動進行研究的學者之一,馮國慶受吉登斯“所有的人都是具有認知能力的行動者。也就是說,所有的社會行動者對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為的條件和后果都擁有大量的知識”這一觀點的影響[7],將工人看成是具有社會認知能力的行動者。他認為,工人的社會行動不是單向度的,是可以與社會之間相互協調的,因為習慣了“主人翁”地位的工人盡管難以理解市場取向的改革對他們利益的沖擊,但由于強大的傳統力量,由“主人翁”地位升華出的自尊不但不會同步失去,反而得到了強化,在面對社會轉變帶來的壓力時,自身地位得到改善的工人,其行為特征是趨利避害,尋求擴展能夠自主控制的空間,而自身地位失落或下降的工人,受趨利行為能力的限制,其避害行為能力就更為突出,除極端情況下發生激烈沖突,他們更注重自我約束以保自尊,總體來看,他們追求的是有基本保障的工作和生活[8]。國家和政府通過構建一系列多層次的制度對企業變革過程中利益受損群體進行了相應的利益補償,預防性制度、救助性制度和再就業制度的建構在很大程度上減緩了他們的不滿情緒,使大部分失業下崗人員的基本生活得以保障。從事非正規工作是下崗失業人員在基本生活有保障的情況下所作出的一種較為理性的生存邏輯的行動選擇,但是這種理性并不是經濟理性,更多的仍是生存理性。
大部分城市貧困群體都通過各種不同形式的非正規就業來補償自己的日常生活,孫立平指出:“到2004年底,我國城鎮非正規就業人員已經達到8000萬人,占到城鎮就業人口的20%~41%。他們主要是個體經濟和小型私營企業中的就業者。而非正規就業人員的來源主要是兩部分人。一是失業者中的再就業者,二是城市中的新增勞動力。”[9]
對于城市貧困群體來說,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員回到社會的主導產業中去及回到原來那種穩定的就業體制中去都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朝陽產業也不會向他們提供多少就業機會,因此,大量的城市貧困群體只能從事非正規工作。一部分人在自己打零工,成為充斥于城市每個角落的城市流動無證小商販大軍中的一員,在中國城市管理制度的夾縫中謀求生存的空間。另一部分人成為型私營企業中的就業者,這些工作的報酬往往比較低,每月只有700—900元。目前城市貧困人員大都從事各種形式的非正規工作以補償日常生活的開支。
從對城市貧困群體在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變遷中的生存邏輯選擇到國家多層次救助制度建構下的生存邏輯選擇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這種行為的發生力來自其內部而非外部,雖然從制度變遷角度來考察,是一種強制性的制度變遷結果,但促其進行抉擇的仍然是一種生存壓迫性的動力。無論是在面臨國家制度調整、企業改制期間的自我利益保護選擇的沖突過程,還是在救助制度建構后的滿足生存利益而從事非正規工作的行動邏輯選擇過程,這種壓力一直是決定其選擇的關鍵性因素,這也就迫使個體從生存的問題進行思考,一切社會行為都將圍繞著生計的情境進行。對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城市貧困群體的生存邏輯選擇是一種內生的生存壓力作用的結果。
四、相關討論
從社會互構論的視角來看,幫助城市貧困群體擺脫貧困的反貧困歷程是貧困群體的參與行為與建構制度之間的互構過程。從理論上講,在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針對出現大量下崗失業人員而建立起來的預防性制度、救助性制度和再就業政策,為他們提供了免于陷入貧困的保護網。盡管城市貧困群體在國家建構的多層次保障制度之下維持了基本的生活,選擇了符合其生存理性的行為邏輯,但是,制度的文本規定和制度執行的實踐之間總是存在一定的脫節,還有一部分城市貧困群體游離在保障制度之外,基本生活難以維持。這個脫節是制度與下崗失業人員之間策略性互動關系和過程的表達,既有制度設計本身及執行的問題,也有貧困群體在面對這些制度時根據自身理性所進行的參與行為選擇,在這種制度與參與行為的互構中顯現了我國扶貧歷程中所存在的個人參與不足的問題,在以后的扶貧實踐中,如何更好地實現個人與社會的雙重參與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問題。
[1]R.科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科爾納.短缺經濟學[M].張曉光,等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6.
[3]李漢林.中國單位社會:議論、思考與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王大明.正確處理群體性事件確保穩定大局——在全國政協九屆四次全體大會上的發言[J].真理的追求,2001,(4):1—3.
[5]吳清軍.國企改制與傳統產業工人的轉型[D].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6]張磊.中國扶貧開發政策演變(1949—2005年)[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7.
[7]吉登斯.社會的構成[M].李康.李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8]馮同慶.中國工人的命運:改革以來工人的社會行動[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9]孫立平.活在兩個二元結構的夾縫中[J].經濟管理與就業研究,2006,(5):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