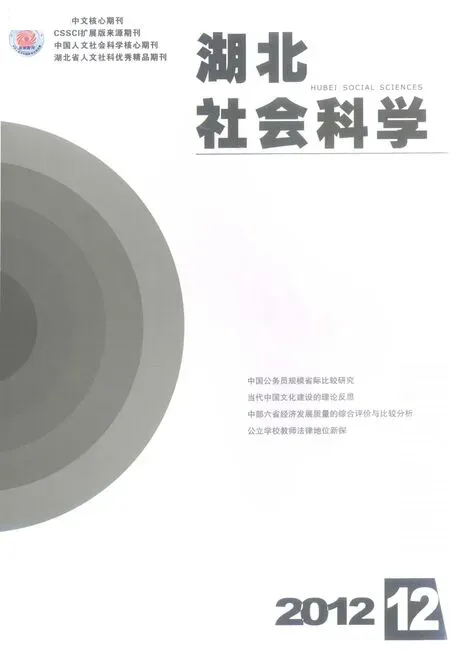科學實踐觀的本質意蘊
李月玲,王秀閣2
(1.山西大同大學, 山西 大同 037009;2.天津師范大學,天津 300387)
穿梭歷史的長河,展現在眼前的是一部部晦澀難懂的哲學書,而隱藏其后的卻是哲學家們在思維的最高層次,對自然、對社會、對人類自身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的持之以恒的探索。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前人的成就,運用科學的思維方法,吸收了黑格爾的“勞動”的觀點和費爾巴哈的“感性對象”的觀點,通過系統考察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實現了對“現實的人”的科學理解,形成了科學實踐觀,以此解開了自然之謎、人類社會之謎以及人自身生存發展之謎。科學實踐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區別于以往哲學的標志,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核心。以往哲學家不是沒有認識到實踐的作用,但他們只是抓住了實踐活動中的某一方面,肢解了貫穿于實踐活動中的完整的因素。科學實踐觀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它不僅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質的規定性,也表現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它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實踐是人與動物的異質點
遙遠而古老的希臘神話——“斯芬克斯之謎”,永恒地吸引并考驗了無數仁人志士的智慧。人對于人自身的反躬自問始終是哲學的真實主題和核心內容。人來源于動物界,這一客觀事實已經決定了人永遠不可能徹底擺脫獸性,[1](p106)在人的身上不僅集中了動物所具有的基本屬性,同時還具有其他一切動物所不具有的本質和特性。然而,人究竟是怎樣區別于動物的,同樣是哲學家們面臨的一個謎。于是,古今中外的一切哲人智士們對人的存在及其與動物的區別進行了深刻的探索和體悟。 諸如 “理念人”、“知識人”、“政治人”、“經濟人”等各種概念,反映了哲學家在不同的立場上對人的本質及其人與動物的區別作出的各種解說和闡釋。
考察哲學家們冥思苦想的歷程可以看出,他們幾乎接觸到了人的二重性中的各種矛盾,揭示了人是自然性與超自然性、生命性與超生命性、肉體與靈魂的雙重性、悖論性的存在,卻唯獨沒有找到形成這一矛盾的根源,也沒有找到把二者結合于人的基礎、中介和橋梁。他們對人的本質的認識始終局限在某一向度或停留在某一方面。譬如,“人的本質,人,在黑格爾看來=自我意識”。[2](p207)費爾巴哈僅僅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僅僅局限于感情范圍內承認“現實的、單個的、肉體的人”,[2](p530)他始終沒有找到人的二重性的根源,在他看來,承認人的二重性必然會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他強調人是有生命、有血肉的感性存在,但他又承認“人之所以為人和所以被稱為人,并不是按照他的肉體而是按照他的精神”。[3](p120)由于費爾巴哈把人局限在生物學意義上的具體人,在社會現實中卻是抽象的人,所以,在他那里,人仍然不過是“一半禽獸,一半天使”。
顯然,在馬克思以前的哲學家們一方面論證了人的自然性,另一方面論證了人的超自然性(精神性、能動性、社會性等)。他們只是以相互孤立的、片面的形式研究了人的兩個不同的方面。最終匯聚的矛盾的焦點是——從自然性說明不了超自然性,超自然性卻缺乏客觀的物質基礎。這種“二律背反”的矛盾體根源于本體論的思維方式,根源于把現實中的人看作是一種無條件的自在體。由此,以往哲學家在尋找和論證人與動物的區別時,同樣只看到了人與動物的直觀意義上的區別,卻沒有找到真正能把人和動物區分開來的支點和根基。從思維方式上看,他們認為只要在人身上找到了與動物不同的特征,就意味著抓住了人的本質。豈不知,這種方法沒有突破物種的限制,不論怎樣區分人與動物的不同,卻始終把人當做“一物”來看待,看不到人之為人的生成屬性。從具體論證上看,他們強調了人區別于動物并為人所特有的精神、意識、理性及其能動性等,但他們沒有追問人具有的精神、意識、理性及其能動性的根源,對自己所肯定的內容缺少理論前提的反思和論證。可見,他們從根本上忽略了一點,就是人之為人不但在于人與動物的區別性,也在于人與動物的聯系性。[4](p1)因為人不僅僅是精神的存在物,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物。
然而,“一個種的整體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2](p162)很明顯,人區別于動物的本質屬性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亦是說,“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是人與動物的最本源的異質點,因而也是人成為人的根據和奧秘所在。這種“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指的就是人的實踐。“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指的就是一種自覺活動,它是相對于無意識的自發活動而言,它意味著“人能區分自我和他我、人自覺到非我存在和自我存在的相異和對立,這就使人既能‘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進行生產,還能‘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5](p9)正是在這種活動的基礎上才表現出了人的精神、意識、理性、能動性等方面的特征。這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離不開人之為人的自然屬性。亦是說,馬克思在區別人與動物時并沒有排除人與動物的生命活動的共性,而是在共性的基礎上追加了人所特有的“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并且指出:“正是由于這一點(有意識的生命活動——筆者注),人才是類存在物。 ”[2](p162)
可見,實踐的內在邏輯蘊含著人是自然屬性和超自然的社會屬性兩個層面的統一。“實踐是解決以往哲學家揭露出來而駕馭不了的那些矛盾的現實基礎”。[6](p180)馬克思通過揭露和把握實踐的完整本性,克服了以往哲學聚焦的矛盾,最終得出:“實踐是人之為人的初始本源”。[4](p3)在此,實踐的本源性既不是指時間的前后,也不是指邏輯順序的先后,而是特指存在論意義上的基礎性。誠如馬克思所講的“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正是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2](p529)馬克思著眼于現存的感性世界,從“現實的人及其活動”出發,即從實踐出發“找回了具有雙重生命本性的現實的人”。[5](p3)也就是說,馬克思通過考察“對象性的活動”,最后得出了“人不僅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類存在物”[2](p211)的結論。這一結論與其說是揭示了人的存在的二重性,還不如說揭示了人不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也是進行著對象性活動的類存在物。人的社會性必須以自然性為基礎,人的自然性也只能存在于人的社會性中。決不能把人的這種二重性本質拆解開來理解。如果只承認人的社會性(或稱為超自然性),人也不再是人,而是神了。相反,如果只承認人的自然性,則只能看到人同其他自然物相同的性質,看不到人的生成性。
二、實踐是個人與社會的關聯點
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是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7](p79)而且,個人與社會二者之間的關系問題是有史以來就存在的問題,是歷代哲學家爭論的焦點,也是社會觀念產生分歧的聚焦點。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之前,對人的存在的理解基本有兩個向度:一個是自然主義的存在觀,它把人的生存簡單地還原為自在狀態,在很大的程度上蔑視了人的存在的神圣性。一個是超驗存在觀,它把人的存在抽象為一種純粹的精神實體。這兩個向度都不是從實踐出發去思考和把握人的存在問題。在本質上,都只是把人看作是一種現成的、既定的、靜態的存在物,看作是一種擺在眼前的、可以用理性予以靜觀的對象,看作是一種可以用概念、定義的方式被解釋的、被認識的客體。而根本沒有從屬人的、活動的以及人本身的社會生產條件及其歷史條件等客觀的方面去理解人的存在和生存。[5](p34)所以,囿于他們對人的存在及其生存的理解,他們也就沒有真正把握個人與社會二者之間的關系。
在古代哲學家那里,他們對個人和社會的關系的認識極為簡單,一般認為社會高于個人,個人的生存必須依賴于社會群體。到了近代及其以后,隨著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個人自主生產能力也逐漸提高,逐步擺脫社會群體對個人的束縛,這種個人和社會由不可分離到逐漸分離的現實使人們意識到了個人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這一時期,人們不但認識到個人可以自由活動,也認識到了個人活動的結果卻不是個人的意愿和預計的結果,使得個人和社會關系問題進一步凸顯,最終形成了個體原子主義和社會整體主義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個體原子主義從個人的自然本性出發,把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個人看做是孤立的個人,認為:“只有個體是真實存在的……,只有通過分析個體的行為,才能解釋社會現象”。[8](p327)社會整體主義認為:“只有社會才是真實的存在,社會對個人具有優先性,個人只是實現社會目的的手段,個人的需要、利益必須服從于社會整體”。[9](p40)這兩種觀點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個人和社會看做是兩種相互對立的、既成的實體,沒有把社會的問題作為個人的問題,也沒有把個人的問題作為社會的問題,而是把二者割裂開來,把個人置于與社會的差異、對立和沖突中,找不到個人和社會統一的現實基礎。
馬克思通過一步步地追問個人和社會的關系問題的邏輯起點,指出:“首先應當避免重新把‘社會’當做抽象的東西同個體對立起來。個體是社會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現,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現這種直接形式,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證。人的個體生活和類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盡管個體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是——類生活的較為特殊的或者較為普遍的方式,而類生活是較為特殊的或者較為普遍的個體生活。”[2](p188)那么到底什么是人?什么是社會?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2](p505)“社會不是由個人構成,而是表示這些個人彼此發生的那些聯系和關系的總和”。[10](p221)在這里,馬克思把人和社會最終都界定為“社會關系”。而 “社會關系的含義在這里是指許多個人的共同活動。”[2](p532)馬克思進一步解釋道:“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2](p724)在明白人和社會各自的本質的基礎上,我們還要追問: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如何呢?馬克思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蟄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2](p3)“社會本身,即處于社會關系中的人本身。 ”[11](p204)正如 “社會本身生產作為人的人……,社會也是由人生產的”。[2](p187)在這里,馬克思把人理解為社會,把社會理解為人,而且個人和社會是互相生產。由此可見,個人和社會始終是統一的,而且二者同構共生、彼此映照。但馬克思的這種界定并不是同義反復,他的這種界定是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上的,他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2](p505)如果脫離馬克思的實踐的觀點,就很難理解馬克思解釋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內在實質;如果脫離馬克思的實踐的觀點,那些把馬克思一方面用社會解釋人 (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另一方面用人解釋社會(社會本身,即處于社會關系中的人本身)的解釋方法理解為只不過是同義反復的情況也不足為奇。
總之,實踐既是把握人和社會各自的本質的基礎,也是理解人和社會之間的關系的橋梁和紐帶。只有在實踐中,個人和社會才具有真實的意義和內涵;也只有在實踐中,個人和社會之間才是統一的。因為決定個人和社會本質的“社會關系”只有在實踐活動中才能產生和形成,而不是存在于實踐之外的獨立的、先驗的東西。“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2](p196)同樣,實踐活動又只能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才能進行,而不是脫離一定的社會關系而憑空進行著的活動。“人既是實踐活動的發起者又是社會關系的承擔者。”[5](p12)實踐是“生產和再生產著這個過程的承擔者、他們的物質生存條件和他們的互相關系即他們的一定的經濟的社會形式的過程”。[12](p927)所以,實踐是個人和社會的關聯點。
三、實踐是主體與客體的分合點
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開宗明義地批判了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主要缺陷。他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唯心主義卻把能動的方面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言外之意,一切舊唯物主義不理解客體是主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活動的產物,唯心主義卻把主體的感性活動抽象為純粹的精神活動。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把對象、現實、感性看成是主體在感性活動中所創造的客體。馬克思從主體和客體的關系出發,對實踐作出了科學的規定。其中隱含著至少三個方面的含義:第一,實踐是主體創造客體的對象性活動;第二,主體是實踐的主宰者;第三,客體是主體的對象性活動(即實踐)的對象和產物。簡言之,主體和客體是一對關系范疇,它不僅產生于一定的實踐關系中,而且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實踐關系中。由此,沒有人的實踐活動,沒有在實踐活動中形成的對象性的關系,也無所謂主體與客體之分。其中“人始終是主體”,[2](p195-196)因為動物和外部世界之間只存在聯系,而不存在關系。“凡是有某種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么東西發生‘關系’,而且根本沒有‘關系’;對于動物來說,它對他物的關系不是作為關系存在的。”[2](p533)人在對象性的實踐活動中,通過把自己的本質力量不斷地對象化,自我生成為主體,從而把一切在自己對象性活動范圍內的人自身連同其他存在物都變成了客體。主體和客體的“相合線和相離線:彼此相交的圓圈。交錯點=人的和人類歷史的實踐”。[13](p239)在實踐的基礎上,主體創造客體,客體使主體對象化的本質力量不斷提高。猶如馬克思所言:“不僅在客體方面,而且在主體方面,都是生產所生產的,……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11](p16)所以,實踐是主體與客體的分合點。
四、實踐是現實性與超越性的關節點
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對舊唯物主義的特有的局限性進行了詳盡的歸納和總結。他指出:“這種唯物主義的第二個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為一種過程,理解為一種處在不斷的歷史發展中的物質。這是同當時的自然科學狀況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形而上學的即反辯證法的哲學思維方法相適應的。人們已經知道,自然界處在永恒的運動中。但是根據當時的想法,這種運動是永遠繞著一個圓圈旋轉,因而始終不會前進;它總是產生同一結果”。[14](p282)這種觀點從根本上抹煞了人及其世界所具有的超越性。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觀點,恰好突破了這一局限。
馬克思指出:“無論是在人那里還是在動物那里,類生活從肉體方面來說就在于人(和動物一樣)靠無機界生活,而人和動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賴以生活的無機界的范圍就越廣闊”。[2](p161)但是,人對“無機界”的依靠不同于動物對“無機界”的依靠。人不再是單純地依賴于自然的現成的恩賜,而是通過實踐活動來滿足自身對“無機界”的需要。“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正是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2](p529)也正是在這種實踐活動中,人把“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對象(材料)和工具”的整個自然界不斷地“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原來屬于人的現實環境的組成部分,通過人的改造,反而成了人的生命的組成部分(人的無機身體)。并且,在這種實踐活動中,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2](p162)把“他自身的類以及其他物的類——當做自己的對象,而且……把自身當做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2](p161)也就是說,實踐是建立在一定的對象的現實性基礎上并受一定的對象的現實性的限定。同時,人也是通過實踐不斷地改造現實的對象,不斷地打破對象的現實性的限定,從而在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具體的、不斷動態生成的過程中提升自身的認識水平、能力素質及精神境界。正是這樣,馬克思斷言:“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2](p500)質言之,人“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2](p528)“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前一代的工業和交往,并隨著需要的改變而改變他們的社會制度”。[2](p528)但人不是隨心所欲地超越各種界限,只能在既有的各種現實的基礎上活動。同時,人也永遠不會滿足于已變成現實的東西,永遠不會滿足于動物般的復制式的生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人不是在某一種規定性上再生產自己,而是生產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種已經變成的東西上,而是處在變易的絕對運動之中。 ”[11](p137)由此,實踐作為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總是在一定的現實的基礎上展開,并不斷地否定客觀事物的現存狀況,使現存物質世界不斷超越固有的限制。
綜上可見,科學實踐觀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突破了以往哲學孤立的、片面的、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上述四個“基本點”是科學實踐觀的基本意蘊。它內涵著個人與社會是同構共生、動態創生、緊密聯系的關系型范疇,表明個人和社會都不是固定的、不變的、先在的實體,二者都不具有先前預設的、固定不變的本性,其本質都是在社會關系中形成、變化和發展的。它內涵著實踐是人之為人的本源性活動,也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活動。但并不是人的所有的行為都是實踐,不能把實踐概念庸俗化、經驗化。實踐是主體改造客體的對象性的活動。對象性活動意味著人通過把自身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在改變和創造客體的過程中提升和改變自身。它具有現實性、目的性、動態性、超越性等特性。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德]費爾巴哈.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下卷)[M].榮震華,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4]高清海.轉變認識“人”的通常觀念和方法[J].人文雜志,1996,(5).
[5]鐘明華,等.馬克思主義人學視域中的現代人生問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高清海.哲學思維方式變革[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7][英]鮑桑葵.關于國家的哲學理論[M].汪淑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8][英]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M].李康,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9]陳晏清,李淑梅.個人和社會的關系問題是社會觀念的核心問題[J].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1).
[10]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列寧.列寧全集:第 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