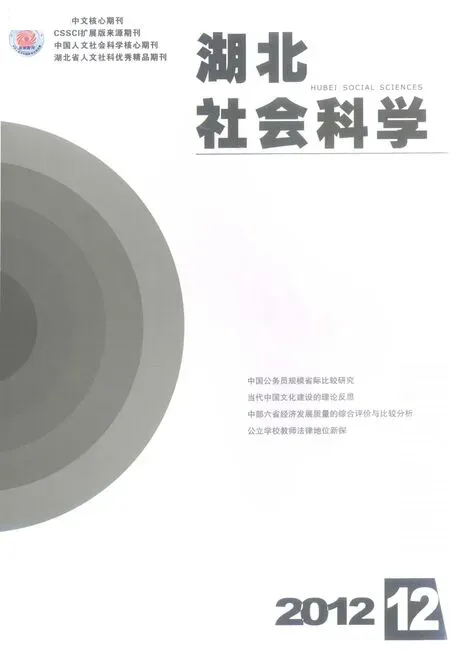政府公信力研究綜述與學術反思
楊 鈺
(南京審計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9)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權威的體現,是政府提高行政效率、節省行政成本,順利實現政策制定與政策執行的重要保障;同時,作為市場經濟規則和秩序的制定者與維護者,良好的政府公信力將有助于良性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保障市場經濟的高效運行;而最重要的在于,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體現,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將有助于強化政府合法性,鞏固政權的穩定性以保障國家與社會安定團結的大局。
然而,當前世界各國政府公信力卻幾乎呈現統一的下滑趨勢,因政府公信力流失帶來公共管理有效性的降低,從而帶來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及其他問題。在當前全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主題中,政府公信力已成為制約全球各國有效公共管理的瓶頸性問題。理論探討總是沿著時代與社會發展實踐的脈搏而發展,基于政府公信力的現實缺失,研究者們從不同的角度研究探討了政府公信力的有關問題。認真梳理有關政府公信力的研究成果,對于進一步拓展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寬度與深度將會有著十足的幫助。
一、政府公信力研究的國內外背景
美國民意調查顯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公信力一直處于下降趨勢,且下降幅度較大。美國全國選舉研究會(NES)針對政府信任危機進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證實美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確實呈現大幅下降趨勢。哈佛大學Nye Joseph教授針對政府信任危機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根據其調查顯示,1964年,美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為76%左右,而1995年,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到15%,盡管之后由于一系列的事件,政府公信力有所提升,但都遠不如30年前。[1]國外研究顯現,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具有普遍性特點,所有層級的政府公信力都下降。美國民意調查顯示,美國聯邦政府、州政府及各地方政府公信力及所有公共部門的公信力都在下降;不同類別的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均呈現出下降趨勢;所有發達國家政府的公信力都在下降。不僅美國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加拿大、英國、意大利、西班牙、荷蘭、挪威、瑞典等國政府公信力也在下降。政府公信力下降成為一種全球性現象。[1]
相對于西方國家對政府公信力的研究,我國學界與政府部門對于政府公信力的關注和研究要稍晚些。2001年,《廣州日報》刊登《電子政府:如何提高政府公信力》,國內關于政府公信力的研究開始展開。而至2003年非典事件后,國內學界及政府部門表現出對政府公信力的密切關注,而隨著近年來公共危機事件的增多與群體性事件的頻發,對政府公信力的研究更彰顯出現實針對性與時代性的意義。
二、政府公信力的內涵
公信力,在英文文獻中一般有這樣幾種提法,即credi-bility、accountability 和 public trust,大部分情況下,英文文獻視三者為同意,但在具體的中文語境中他們的深義是有區別的。Accountability多指對人或事負責,Credibility更多指向的是可信度、公信度,而public trust指向公信力,公信力所包含的概念深度與廣度更富于公信度的概念,但在當前中國的研究中很多人將這兩者視為同一意思。公信力的研究起源于西方大眾傳媒學的研究,研究者對這一概念的探究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即信源與媒介,是指在西方大眾傳媒中研究媒介公信力時的兩大重要領域:一是認為公信力受到信息來源本身特質的影響,如信息本身的準確性、可靠性;一是認為公信力受到信息傳播渠道的影響,如網絡媒介與傳統媒介在信息傳播可信度上的不同。西方媒介公信力在近百年的研究中經歷了不同的歷史研究階段,學者們從各自的研究中給出了不同視角的概念界定,但終未形成關于公信力的一致定義。
公信力在現代漢語中尚屬新興詞匯,《現代漢語詞典》未能對這一詞匯給出準確界定。公信力由“公”、“信”、“力”三個字組合而成,為對公信力有準確的認知與理解,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詞源的拆分分析。“公”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有多種解釋,與這個合成詞相關的主要有兩種意思,即國家或集體的,跟“私”相對,以及公共的,大家所承認的,在這個合成詞中,“公”跟這兩個意思都有相關性;“信”指向兩種主要旨義:說話算數,與之相關的組詞如誠實、信用、守信、言而有信;認為正確或確實而不加懷疑,與之相關的組詞有信服、信賴、信心、信任;“力”有三種相關的意思:一是指物體之間的相互作用,二是指能力,三是指事物的效能。由此,公信應指向公共的信任,公眾的信任,這一點基本上沒有爭論,但關于公信力,因為學者們對于“力”的理解的不一樣,而形成了今天國內學者對于公信力及政府公信力概念界定的不同代表性認識。公信力包含的內容涉及多方面。從當前的主要研究來看,公信力的類型主要分為政府公信力、企業公信力、社會組織公信力以及媒介公信力等。
政府公信力,從國內學者的概念界定來看,存在著三種代表性觀點。而這種代表性觀點的形成正源于對“力”這個字的界定與理解的差異。
一種是能力說,認為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獲得公眾信任的能力。高衛星認為,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在其公共行政活動中依據自身的道德狀況所表現出來的與社會公眾建立自愿的穩定的并能在緊急狀態下外化為物質力量的信任關系的能力。[2]舒小慶指出,政府公信力就是政府的影響力與號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觀結果,體現了政府工作的權威性、民主程度、服務程度和法治建設程度。[3]何顯明等認為,政府公信力體現政府的信用能力,它反映了公民在何種程度上對政府行為持信任態度。[4]
一種是效能說,即政府獲得公眾信任的程度,其指向性更強調公眾的認同與評價程度。龔培興認為,所謂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依據于自身的信用所獲得的社會公眾的信任度。[5]張旭霞認為,現代意義上的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信守對公眾的承諾,從而獲得公眾內心上對政府的運作方式、政府行政人員的行政行為以及與政府行為相關的整個社會制度的理解和信任。[6]吳威威認為,政府的公信力,正是政府行使公共權力效果的社會反饋,是政府責任行為的外射。[7]楊金木認為,政府公信力亦叫政府公信度,是指政府作為、能否全面履行公共責任的質量和獲得公眾認同的情況,它表明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和信心水平。[8]
一種是關系說,唐鐵漢認為,公信力是政府的影響力與號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觀結果,體現了政府工作的權威性、民主程度、服務程度和法治建設程度;同時,它也是人民群眾對政府的評價,反映了人民群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和信任度。用一個公式來表示,就是:政府公信力=政府行政能力?公眾滿意度。[9]政府公信力是社會組織和民眾對政府行為的主觀價值判斷,它是政府行為的形象和產生的社會信譽在社會組織和民眾中所形成的心理反映。政府公信力的基礎是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它是公眾對政府能夠代表他們利益的一種心理期待,也是公眾與政府之間的一種互動關系。[10]綜觀學者們對政府公信力的概念界定,盡管他們各自著眼的視角不同,但充分說明對政府公信力內涵的把握應注重以下幾方面:第一,政府的能力是政府公信力產生的基礎,政府在施政理念、執政行為中展示自身能力而形成政府形象與政府聲譽,構成政府信用,影響政府公信力;第二,信任本身既是一種理性選擇,更是一種情感活動,因而,政府公信力體現客觀的政府績效,但同時也依賴于公眾的感知與判斷;第三,政府公信力不是一種靜態的描述,它是一種動態的運行機制,在這種機制中,體現著政府與公眾的互動關系,政府的行為獲得公眾的信任,政府公信力產生,并繼續推進政府行為,產生新的循環。良性的政府與公眾互動關系將有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反之,將引起政府公信力的下降,產生循環證實。
三、政府公信力的特點及意義
政府是公共權力的實際行使者,“政府具有公共權力屬性最直接的結果是使政府在公共信任層面上,也就是我們說的公信力的層面上,所展現出的運行機理、結構要素與其他組織公信力或個人公信力有著明顯的區別和不同的含義和價值。”[11]具有區別于其他社會組織的不同特點。
第一,公共利益的特點。政府公信力來源于政府合法性,政府的公共權力來自于政府與公眾之間的委托——代理契約,政府的權力來源于公民權利的讓渡,政府通過提供公共服務來兌現契約、實現使命,而公共權力只是政府行為的手段,其終極追求在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因為公共利益的目的性決定了政府公信力區別于企業公信力的經濟利益性及其他主體的公信力。
第二,政府公信力涉及范圍廣。從政府公信力所涉及的范圍上看,縱向上,他涉及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以及政府機構與政府工作人員的公信力;橫向上,既涉及到國家政治管理如軍事、國防、外交等的公信力,也涉及到經濟、教育、文化等其他相關公共事務管理的公信力,其輻射范圍涉及到公眾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三,社會影響大。政府作為國家和社會中公共權威的承載者,地位特殊。作為社會公眾觀念與行為的指導者,作為公共管理的實施者,其行為與形象對于全社會來說有著重要的引導與示范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社會影響,決定了政府公信力在公共秩序和現代社會生活中起著基礎與導向性作用。
正因為政府公信力的特點,決定著政府公信力在當今行政改革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與作用。
首先,政府公信力影響著政府的政策執行效果及效率,是履行政府職能的重要保障。政策的執行以及政府職能的實現依賴于物力、財力及人力資源,但其順利推行更有賴于公眾對政府的信任。盡管政府行為具有強制性的特點,但“一個政府為了達到上述目的而必須使用的強制,應減至最小限制,而且應通過眾所周知的一般性規則對其加以限制的方法而盡可能減少這種強制的危害”。[12](p17)如果公眾對政府缺乏信任,即便政府可利用其強制性,但其效果和效率也是十分有限的。
其次,政府公信力影響市場秩序的建立及其運行。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與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依賴于政府營造的市場環境及規則秩序的制定。政府作為游戲規則的制定者,既要保障規則制定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又要確保規則的順利實行,并對違反規則者實施懲罰。因而,作為規則制定者與實施保障者的政府只有自身擁有政府公信力,才能展現其表率力,引導市場參與主體按規則行事,追求誠信的長期利益,引領市場經濟向健康、有序的良性方向運行與發展。
再次,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根源。在學理上,馬克斯·韋伯率先對“合法性”問題進行了探討,他認為,“一切經驗表明,沒有任何一種統治自愿地滿足于僅僅以物質的動機或者僅僅以情緒的動機,或者僅僅以價值合乎合理的動機,作為其繼續存在的機會。相反,任何統治都企圖喚起并維持對它的合法性的信仰”。[13](p239)在這里,韋伯強調了公眾的認同和精神上的肯定對于政府合法性確立的重要性,體現政府公信力對政府合法性地位的根源性影響。
最后,政府公信力是社會信用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信用系統的基礎與重要保障。現代社會信用體系由多個部分組成,政府作為公共權威的代表者,其行為所涉范圍廣,社會影響大,因而構成整個社會信用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政府作為國家管理的實體,其行為活動對全社會具有決定性、指導性與示范性,因而,政府公信力是社會信用的基礎與重要保障,對于整個社會信用系統的建立與社會生活的有序建構起著決定性作用。
四、政府公信力的內容及影響因素
政府公信力包含什么內容?影響政府公信力的因素有哪些?對這兩方面問題的分析有利于我們直觀、明晰地理解政府公信力,為探究提升我國政府公信力的相關舉措研究做好基礎性工作。
姜曉秋等基于公眾對政府的主觀判斷,他認為,政府公信力包含三方面的內容:一是公眾對政府人員的信任,二是公眾對政府機構的信任,三是公眾對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信任——即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質量和公共政策的信任。[14]唐鐵漢認為,政府公信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人民群眾對政府公信力的評價,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政府的誠信程度、政府的服務程度、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政府民主化程度。[15]陳潮升等認為,公眾對政府信用的評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政府的民主化程度、政府政策的穩定程度、政府公務員的行政道德水準、政府的服務程度。[16]白春陽等認為,政府公信力包含三方面的內容:一是政府機構的社會形象或道德評價的問題,二是公眾對政府機構和官員們行政能力的信任問題,三是對各種政策的信任問題。[17]何顯明等認為,政府公信力包含行為信用、政策信用及績效信用。[18]
呂維霞等基于公眾感知的定量分析,將政府公信力的影響因素方面概括為公眾滿意度、政府形象、政府承諾、公眾感知行政服務質量以及人口統計特征五個方面。[19]舒小慶認為,影響政府公信力的指標體系取決于以下因素:政府行為的法治化程度、政府政策的規范程度、政府民主化程度、政府官員的道德感與廉潔程度、政府工作的公開程度。[20]張旭霞指出,政府公信力的強弱,取決于政府所擁有的信用資源的豐富程度。這種信用資源既包括意識形態上的(如公眾對政府的政治合法性的信仰,公眾對政府制度及公共政策過程的公正性、合理性的認可程度等等)、物質上的 (如政府的財力),也包括政府及其行政人員在公眾心目中的具體形象(行政人員的率先垂范性、服務性、效率性)等等。[21]另外,還有一些學者從環境、信息的角度分析了其對政府公信力的影響。
從學者們對政府公信力內容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來看,對于政府公信力內容的探討基本上著眼于橫向與縱向的分析上,即縱向的分析主要從政府層級實現,即可將政府公信力內容分為政府機構公信力、政府人員公信力、政府行為公信力;橫向分析則可從政府活動所涉的多方面體現政府公信力,如民主化程度、法治化程度、規范化程度、信息公開化程度、政策穩定化程度、政府官員的道德水準與服務程度等。
對于政府公信力影響因素的分析,因為各自所致力的角度不同,綜合看基本上著眼于政府與公眾兩方面。筆者以為,政府公信力的影響因素,除學者們已著力的這兩個角度外,我們還可以從環境層面作一些深層次的分析,比如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背景及政府所處的歷史階段對于政府公信力的影響,將會拓寬我們對政府公信力影響因素的認識,以便更全面分析政府公信力的可能影響因素,以為提升政府公信力提供可能性路徑探討。
五、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路徑選擇
在當前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有助于政府合法性的加強。因而,我們應將提升政府公信力作為當前政府管理改革與創新的重要任務,研究與探討改善政府公信力的有效途徑。
舒小慶指出,應加強政府法治建設,以公正立公信;推行政務公開,以公開促公信;引導公共決策中的公眾參與,以民主贏公信;提高政府績效,以效率樹公信。高衛星認為,應切實實現政府職能轉型,建設服務型政府,樹立行政管理的服務理念;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建立有效的政府問責機制,建設責任政府;改善決策機制以保證決策的科學化;建立公共政策制訂和執行過程中的公眾參與機制,實現公共政策制訂和執行中的制度創新;政府要公開、透明、誠實守信,要切實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信用意識。
綜合學者關于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路徑選擇看,分析的角度基本上著眼于這樣幾個方面:
(一)從政府角度的分析:創新政府服務理念,完善制度建設,改善政府績效。
所謂理念,是人對某種現實所作的價值判斷與態度選擇,影響人的行動取向。因此,為提升政府公信力,我們應強化行政人員的責任信念,培養良好的行政品德,夯實政府責任的道德基礎。以人為本、堅持以人民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強化柔性執法理念,以改變執法方式。[22]同時,應樹立行政忠誠,以強化政府公信力建設的內在動力。[23]
實行政務公開、信息公開并號召公眾廣泛參與行政,以避免因雙方信息不對稱而產生逆向選擇。[24]吳威威認為,應建立政府官員的承擔與職權相應的政治責任制度,加強政府的政治責任,以強化政府的責任機制建設,以激勵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依法。
高績效政府強調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注重責任,將公平置于重要的位置,是對服務型政府、有限型政府、責任型政府、公平型政府等治理理念的綜合與深化。但高績效政府的創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政府百折不撓的努力。[25]白春陽等提出,保障政策制定與執行的科學性與穩定性,保持政策的公正性和透明性。
(二)從公眾角度的分析:培育公民社會,促進公民對政府公信力的監督。
當前,隨著民主程度的增加,社會公眾對政府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這也促進政府不斷改善政府行為,提升政府績效,加強政府公信力建設。在民主的政治社會,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動應當面向整個公民社會,充分考慮公眾的民主需求,并接受公眾對政府的監督,促進責任政府的建設。吳威威認為,一個有效的公民參與系統,必須包含公民的主體性、知情的公民、參與的途徑等幾方面。
積極培育與扶持各種社會組織的發展與完善。社會組織作為政府與公眾之間的另一社會力量,一方面代表了一定區域、行業或階層公眾的利益,另一方面對于組織中的成員具有一定的約束和管理功效,因而,對于理性表達公眾訴求的重要途徑,有利于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建立政府與公眾的良性互動關系,提升政府公信力。
(三)從環境角度的分析:發揮網絡與其他媒介在政府公信力改善中的作用。
網絡與其他媒體在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并對政治生活產生重要影響,以致于西方將媒體稱為三權之外的第四種權力。網絡化是當今的時代特征,政府管理信息在網絡中得以最快傳達,公眾的需求與相關信息得以在網絡平臺傳播,網絡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負面效應。祝小寧等探索了政府、媒體、公眾(GMP)三大信息主體在互信互容、信息選擇、信息對稱等方面的機理,強調尊重信息傳播規律,監控媒體傳播方式,確保信息通俗易懂,降低信息選擇成本。[26]
六、評論與學術反思
十年,我國政府公信力研究走出了開創性的一步,學者們從政治學、公共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信息傳播學、哲學等多學科背景與視角對政府公信力問題展開了研究,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當前,CNKI收錄題名關于“政府公信力”的文章256篇,主題關于“政府公信力”的文章2024篇,這反映了政府公信力研究在我國取得了初期研究成果,并呈現出我國政府公信力研究在最初期探索階段的研究特點。
第一,從研究所關注的熱點看,當前研究關注的熱點仍集中于政府公信力研究的淺層面分析。文獻資料反映,近年來政府公信力的研究熱點主要集中于探討政府公信力的基本概念界定與內涵分析,并形成了幾種代表性的觀點,這對于初期的研究來講是必要的,也是有幫助的。但是在概念的相互關系上,我們還缺乏清晰的厘清,反映在學術探討中,關于“政府公信力”、“政府公信度”、“政府信用”、“政府信任”等相關概念仍有使用的隨意性與替代性。而筆者認為,這幾個概念之間是有區別的。信用,更多是從經濟學角度的分析,政府信用表現的是政府恪守規則、履行對公眾承諾的狀況,它是對政府行為及當前狀態的描述;政府信任是基于政府信用的存在,而產生的公眾對于政府的信任,它是對政府行為及績效的結果反饋;政府信用是因,政府信任是果。政府公信度與政府公信力兩者在當前國內學界基本視其為同一概念,但筆者認為,兩個概念雖只一字之差,但其各自含義上仍存在著差別,政府公信度一般是指公眾對政府行為的信任程度,它是一種量的體現,其概念所轄維度是單一的;而政府公信力包含著政府公信度的本義,但在概念維度上是多維的,它既指公眾對政府行為的信任程度,也體現著政府能力的建設,并富含著以上概念所未包含的影響力、號召力等更多廣度與深度上的含義。
第二,研究思路囿于傳統的分析慣性,基本未走出“研究現狀及存在問題——問題成因分析——對策探討”的分析框架。而事實上,政府公信力并不是一個簡單一維性的問題,我們對其探討應著眼于立體式與多維度的分析。從寬度上看,當前的研究沒有進行不同政府層面的剖析,幾乎所有的研究都致力于最泛化意義上的政府公信力,但事實上,不同層面的政府公信力可能是存在差異的,“就我國地方政府公信力現狀而言,理論研究還遠遠不能滿足實踐的需求。”[27]因此,未來對中央政府層面、地方政府層面以及基層政府層面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將十分有意義。從深度上看,當前研究還處于表層的現狀與原因探析,未對政府公信力的產生、運作機理作深層次分析,這是我們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關注的重點。
第三,從研究方法上看,當前的研究零散性研究多,定性分析多,因而缺乏研究的系統性與實證分析。在政府公信力研究的早期階段,研究成果的零散性折射了研究者們的參與熱情與理論火花;而定性的研究反映了學者們在此域研究中的思辨性探討。但未來政府公信力應向系統性研究發展,從各個不同視角、定性與定量的不同角度反映政府公信力研究的系統性探討。著重于定量角度及個案研究的實證分析將會成為未來政府公信力研究中新的突破點。
第四,政府績效是政府公信力提升的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早期政府公信力研究中,許多研究成果致力于政府特質的角度分析政府公信力,認為政府績效是政府公信力的價值取向與邏輯前提,因而,探討政府績效對政府公信力的影響及相互關系的研究較多。但到目前,我們從政府公信力的相關研究與分析已達成共識,政府績效影響政府公信力,但并非政府績效改善必然帶來政府公信力的提升,而政府公信力的產生機制與運行機制以發現其規律是我們未來研究的重點。
第五,政府公信力的研究應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與社會土壤中加以分析。國外政府公信力的研究歷史較長并已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展開中外政府公信力的比較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意義的。但是,應引起注意的是:無論是從政府本身、公眾視角以及政府、公眾在特定環境中的運作機制分析,我們都必須關注到我國政府公信力所處的大環境,政治背景是不同的,國外的政黨政治對政府公信力影響十分巨大,特定的國體、政體都將影響政府公信力,而更為重要的是,一國歷史形成與文化背景、公眾所持觀念、習慣都將影響到政府公信力。因而,我們在對政府公信力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重將其置于特定的社會土壤與文化背景中加以分析,畢竟政府公信力包含著太多觀念判斷與價值選擇,我們無法對其進行純技術性的分析與探討。
[1]NYE Jr.ZELEKOW D,KIN G C.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81,1-21
[2]高衛星.試論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流失與重塑[J].中國行政管理,2005,(7).
[3]舒小慶.政府公信力:價值、指標體系及其實現途徑——兼論我國誠信政府建設[J].南昌大學學報,2008,(6).
[4]何顯明,汪水波.地方政府公信力與政府運作成本相關性的制度分析[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2(專刊).
[5]龔培興,陳洪生.政府公信力:理念、行為與效率的研究視角——以“非典型性肺炎”防治為例[J].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3,(3).
[6]張旭霞.構建政府與公眾信任關系的途徑[D].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博士論文,2004.
[7]吳威威.良好的公信力:責任政府的必然追求[J].蘭州學刊,2003,(6).
[8]楊金木.提高政府公信力之我見[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06,(8).
[9]唐鐵漢.提高政府公信力 建設信用政府[J].中國行政管理,2005,(3).
[10]吳光蕓.社會資本與提升政府公信力[J].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9,(3).
[11]郝玲玲.政府公信力若干問題研究[D].2010年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12]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13][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14]姜曉秋,陳德權.公共管理視角下政府信任及其理論探究[J].社會科學輯刊,2006,(4).
[15]唐鐵漢.提高政府公信力 建設信用政府[J].中國行政管理,2005,(3).
[16]陳潮升,雍繼敏,等.政府信用的評價標準、現狀及對策探析[J].四川行政學院學報,2006,(1).
[17]白春陽,馬俊升.政府公信力:現代公共生活秩序的核心問題[J].天津社會科學,2008,(1).
[18]何顯明,汪水波.地方政府公信力與政府運作成本相關性的制度分析[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2,專刊.
[19]呂維霞,王永貴.基于公眾感知的政府公信力影響因素分析[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0,(4).
[20]舒小慶.政府公信力:價值、指標體系及其實現途徑——兼論我國誠信政府建設[J].南昌大學學報,2008,(6).
[21]張旭霞.試論政府公信力的提升途徑[J].南京社會科學,2006,(7).
[22]鄧巧玲.行政執法中政府公信力弱化的原因及治理思路[J].甘肅理論學刊 ,2010,(6).
[23]李忠翠.行政忠誠:政府公信力建設新視角[J].湖南行政學院學報, 2011,(1).
[24]趙超,賀華.信息不對稱理論下政府公信力影響機理探析[J].西北工業大學學報,2010,(4).
[25]張旭霞.高績效政府的創建與公信力問題[J].中國行政管理,2008,(1).
[26]祝小寧,白秀銀.政府公信力的信息互動機制選擇機理探究[J].中國行政管理,2008,(8).
[27]武曉峰.近年來政府公信力研究綜述[J].中國行政管理,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