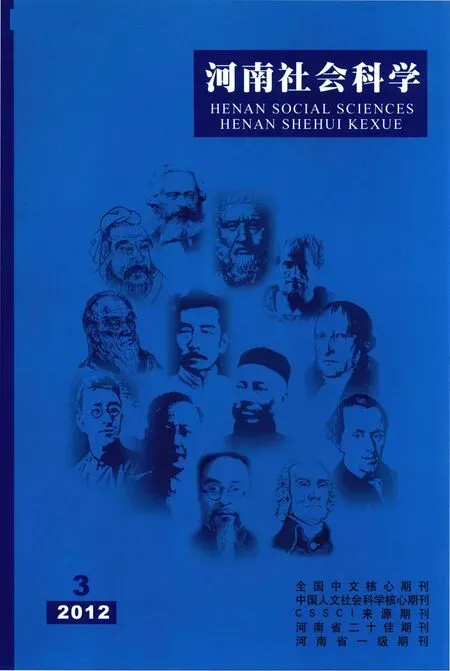翻譯“忠實”的現象學分析
屈 平
(河南工程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翻譯“忠實”的現象學分析
屈 平
(河南工程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按照海德格爾的觀點,是(存在)含義問題,即我們如(是)其所是地理解事物時事物是什么或怎么樣的意義問題,總是以我們有能力解釋事物在理解中能夠明確地如(是)其所是為前提的。既然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本體論旨在探討我們如何能夠如其所是地理解事物的普遍條件所具有的意義,而翻譯史上的翻譯忠實這一理解現象就是這樣一個有關“如其所是”的理解問題,因此,翻譯忠實應該能夠在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本體論框架內給出分析;并且這種分析是最本體的存在論分析。
翻譯;忠實;現象學;分析
一
在《存在與時間》的序言中,海德格爾清楚地告訴我們,本書的主要任務是揭示“是(存在)的含義”[1]。稍后,海德格爾又說,解決“是(存在)的含義”的起點已經找到,它就是人的存在——本體論剖析,或者說人存在的基本結構的解釋,在該解釋中我們能夠發現“能使其他本體論得以派生的根本本體論”。何以可能?因為人的存在——本體論剖析能夠提供“一個讓是(存在)的含義得以在解釋中敞開的視域”[1]。對海德格爾來說,“在是(存在)的問題上,人的存在論剖析始終是第一要務”[1],而且“是的含義”與人的存在有著明確的內在關系。在發現能使“是的含義”得以敞開的起點的同時,海德格爾還找到了通向這一問題的恰當方法,那就是他所指出的“解釋現象學”或“現象解釋學”。在海德格爾看來,存在本體論和解釋現象學并無根本上的不同,它們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本體論和現象學不是截然不同的哲學學科。這兩個術語表征著哲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對象的途徑。”[1]這似乎表明現象學方法論在對人進行存在——本體論剖析時應該具有一種內在的要求,因為現象學方法論不是別的而是在解釋之前就必須先行而在的“是—本體論”條件,該條件要求事物必須在其自身顯現自身,就像它一樣地顯現自身,即如其所是地顯現自身(變自在為自為而保持同一)。唯有通過現象學本體論,我們才能夠如其所是地把握事物,也就是說才能夠從事物自身來把握事物。筆者認為,既然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本體論旨在探討我們如何能夠如其所是地理解事物的普遍條件所具有的意義,而翻譯史上的翻譯忠實這一理解現象就是這樣一個有關“如其所是”的理解的問題,因此,翻譯忠實應該能夠在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本體論框架內給出解釋,而且,我們相信這種解釋,正如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本體論所承諾的那樣,是最本體的解釋。
二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翻譯史上,提出“翻譯忠實”這一概念的首先是那些既全身心體驗翻譯又試圖在理性上對翻譯經驗加以概述的譯者。盡管翻譯的現象像人類的歷史一樣久遠,但在我們所說的那些譯者出現之前翻譯的現象仍然處在遮蔽中。這里有一個問題,即當翻譯現象變得如此明顯和受到關注以至于它不能再逃避那些譯者的視域時,是什么原因讓那些譯者一開始就用忠實(誠實)的尺度或標準來描述(規定)翻譯之為翻譯的呢?翻譯之為,就我們所知,它和人們的“是之理解”(understanding of Being)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種具體的理解并無特別的不同。事實上,翻譯之為無異于人們在已經理解的世界中以澄明的方式去接近并擁有事物的“是”。這里的“是”就是事物在理解中的如其所是。
依據海德格爾的解釋現象學,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條件不是別的而是他的“是(存在)—在—世界”(being-in-the-world)。作為“是(存在)—在—世界”的特殊實體,不僅人會對處于他所關心的世界中一切事物有著強烈的依存關系,而且在這種依存的關系中,人所遇到的一個事實是他自己被他所關心的世界中事物定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所關心的世界——一個在關心中存在的“是”的本體論之光本質上就意味著人是借助于這個世界中的事物來界定和解釋自己的;在這樣做時,人總是依賴于歷史的各種流傳物和由社會建構的各種規范化的標準,它們總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和塑造著人。傳統和社會標準會剝奪人在提問和決定之為上的領導性。與“是—在—世界”即人的是—本體論同生共源的人的“是之理解”也是這樣[2],它通常以公共性——這一人被拋其中的事實來顯現自身。世界的公共性即人在其日常生活中命中注定要尋找的一種存在,因為正是它才是人立身于世而又“如同在家”之感覺的源泉。這種能夠在其中找到“如同在家”的公共性是如何可能的?要想從它的存在之源上做一探討,我們就必須回溯到人的本源性存在上,回溯到人的“是之理解”的可能性條件上,回溯到人的“沉淪”(fall)這一“人之為人的一個明確的存在論的特征上”[1]。
“是—在—世界”是一個統一的現象,它自始至終決定著人的存在。但“是—在—世界總是沉淪的”[1],“因此,人的存在可以被定義為總是沉淪和澄明、總是被拋和拋出為特征的‘是—在—世界’,并且為了這個‘是—在—世界’,人的最為本己的‘將是’是其最為最切己的擔心,這不僅體現在與‘世界’的共處也體現在與他人的同在上”[1]。作為“是—在—世界”的人首先來自他的被拋性。盡管被拋既不意味著終結也不意味著一勞永逸但它卻為被拋之人準備了一個有限的、起源性的理解框架,而理解與解釋正是在這個框架中才得以發生的。這個理解的框架不是別的而是與“是—在—世界”同生共源的世界的世界觀,其特征是一個意義的體系。因此,人被拋其中的那個世界的公共性就必然要依靠和通過這個意義體系來表現自身。如此一來,當與他人共在時個人的世界觀從存在—本體論角度看至少部分地為他人所分享。這個共享就是我們所謂的公共性。有了這個公共性,共在一個世界的人便有了可以彼此分享或者相互理解的機會。這個公共性并不是一個實體而是一種“是之理解”,它不存在于別處而只存在于理解中,它同樣適用于能譯和所譯之間的關系。不僅如此,它還是能譯與所譯之間唯一的橋梁,也就說,它是翻譯之為之所以可能的本源性的前提條件。
事實證明,翻譯忠實的現象就是公共性現象的一種如其所是的顯明,它在第一時間出現在譯者的“是之理解”中。靠著和通過“是之理解”(能譯)譯者才能夠著手于原文或詞語構成物(所譯),而這樣翻譯的方法正是現象學的方法,即讓所譯以自身來顯現自身。當且僅當這樣的公共性在能譯(譯者)和所譯之間出現時譯者才能夠翻譯,當且僅當所譯在譯者的以公共性為特征的“是之理解”中變成了它自身之所是時所譯才能夠成為能譯。公共性,即共享的世界性,或者說共享的意義世界,它與忠實同生共源,而忠實又是翻譯的存在—本體論的前提條件“是之理解”或者“是—在—世界”的內在要求。與公共性和忠實同為一體的翻譯之為其存在—本體論的基礎是作為一種“是之理解”的一切翻譯都必須不僅獲得已被理解和共享的世界的確認而且還要獲得對這個世界的事物之“是之理解”這一事實的確認,否則,翻譯之為和是之理解就未必必然;因為在海德格爾看來,“人之是是在其是中關懷其是并把其是當做其自己的能是而行事”[2],或者“人是這樣一種實體,在其實體之是中它把其是作為關心的問題并以自身最本己的能是把自己指向其是”,或者“人是一種實體,在這種作為實體之是中,它以理解的方式讓自身指向所是”[1]。也就是說,人自身的是其所是為了獲得本己的定義就必須和別的“是”合二為一:“歷史中的存在,辨明身份的要求,都必須要以與別的明確的建構之間的關系為奠基。”當“是之理解”或者“翻譯之為”發生時,理解中的事物之“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必然與人的“是其所是”相一致。簡單地說,正是“是之理解”決定著“事物之是”,因此在已經被“是”所揭示的世界中,所有事物只能以人的“是其所是”來決定其“如其所是”。在這種人其所是的“是”中,公共性和忠實都發揮著證實這種“是”的作用。
盡管在翻譯史上“忠實”概念的出現在中國要比在西方晚兩千多年,但催生這一概念的動因卻是相同的,即都是在翻譯作為一次運動進入其高潮的時候[3]。但無論翻譯發生在何時何地,譯者的能譯與事物的所譯必須以“是”的形式相互印證乃是一個不可辯駁的事實。以“是”的形式一致起來的能譯和所譯就是指譯者的能譯在縮短與事物的所譯之間的間隔。去間隔化的前提是間隔性。但屬于以“是”相連的間隔性是服從于他者(Others)的譯者的能譯,而這種能譯又總是和事物的所譯以“是”的形式相互對應的。這里的他者是另外一個用來指起主要建構世界作用的公共性的術語。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中,所譯之物毫無疑問都是譯者以其所是而是的順手之物(entities ready-to-hand within-the-world)。譯者處在這個由意義關聯起來的世界中斷然不能自已,因為這個世界在譯者被拋其中和拋射理解之前就已經被社會性、規范性、標準性、歷史性和傳統性所寫滿。這樣的世界,用海德格爾的觀點看,就是一個主要發揮他者或者公共性的世界。那么,他者在譯者的日常存在中會發揮何等的作用呢?他者,從其公共性這一特征來看,有權甚至就是負責把譯者的“是之理解”的權利接管過去。譯者以其“是之理解”的能譯向事物的所譯投射則要任由他者來決定。那些構成他者的個體成員在其特征上絕對不能說是清楚明了的。恰恰相反,他者中的每一個都可以代表他者。起決定作用的是由他者所控制的不清不楚和隱匿身份的主導性,而正是這樣的主導性早已經在譯者不經意的情況下接管了譯者的能譯。任何一位譯者都會不由自主地屬于他者,而他者又會因此更加強盛。這個在不知不覺中擁有并取代譯者的他者其目的在于掩蓋它就是實質性的譯者這一存在論上的事實。如此一來,正是他者而非譯者首先和大部分時間都與世界之事物(所譯)以“是”的形式兩兩相處。這里,譯者在他者中的“所屬”既不指這個也不指那個,也不指“所屬”本身,也不指譯者自己,更不指“所屬”加起來的總和。“所屬”是個中性,是個公共性,是個分享的世界性。
公共性或者說分享的世界性是指譯者的能譯與事物的所譯之間的一種通約性或者對應性。遵照這種通約性,譯者把自己的“是其所是”以“能是”的形式投射到事物之上并以此讓事物“如其所是”地顯現自身。公共性,因其在很大程度上表現著譯者所在世界的世界性,所以它就不僅會指導譯者的能譯而且還會把自身反映在能譯之上。這樣一來,翻譯作為還原譯者對原文的“是之理解”就不是無根無據或者隨意觸發的而是和公共性這一明確構成譯者的“是—在—世界”即本體論存在緊密相聯的。譯者在這種公共性中意味著其自身被拋射到一種關系系統中,該關系系統把譯者指向他所在世界中的存在之物(這些在世界中的事物早已以“是”的形式存在于起初的“是之理解”中了)。在這樣的關系系統中,譯者的能譯并不是隨心所欲地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聽從于公共性或者世界性說了什么。在此情況下,作為“是—在—世界”的譯者其被拋性才會激活或者促發與譯者的“是—在—世界”同源共在的“是之理解”的投射。略而言之,在譯者能夠進入認識論的階段之前,譯者早已經以與事物同在的“是”的形式理解了那些在世界中的事物了。
由于譯者與“是之理解”中事物之間的密切關系,譯者在各種知識或認知形式發生之前是不能讓自己從能理解的關系中分身出來的,以至于譯者好像就是干干凈凈立于所謂被觀察的客體面前。真實的情景應該是這樣的:當譯者在其世界之世界性(the worldhood of the world)的引領下去際遇或認識同樣被其世界之世界性照亮的某一事物時,譯者并非是從意識的內部——在這一意識中譯者早已被保持在知識中的、由認知所得的各種客體已經本源性地包圍起來——走出。實際情景恰恰相反,譯者本源性的“是之理解”,在本質上早已與由譯者“是之理解”所揭示的世界中的實體外在地處在一起。在譯者面對“是之理解”翻譯實體時,并不存在任何要去摒棄的意識內容,以便實現“面向事實本身”的翻譯的內在要求。相反,即使譯者外在地與所譯客體相處一起,從具體或實在上說,他仍然是內在于己的。也就是說,譯者作為一個能理解的“是—在—世界”者(a being-in-the-world),他總是內在的,否則個體的實在性便沒了著落。進一步說,對已知事物的感知不是感知者由內到外把握住所知之物再像獲得戰利品一樣將其帶回到意識中來。即使在感知、記憶和保存中,能知的譯者,無論是客觀或是主觀,都始終外在于客體,就如同他始終內在于己一樣。顯然,如果提到的外在性和內在性在個體的人身上要保持相通或合二為一的話,那么它們之間就必須有一種公共性或通約性。事實上,它們之間總是相同的,因為“是之理解本身就是人之存在的一個明確特征”,并且“唯有是之理解‘是’,實體作為實體才可以理解;唯有實體屬于‘是之理解’,‘是之理解’作為一種實體才得以可能”[1]。
總之,譯者翻譯對象—實體(包括詞語構成物)憑借的是自身與處在他敞開的世界中的實體之間的“是之理解”的關系來進行的,而且這種指導翻譯行為的關系“是之理解”是早在主體—客體分離之前就已經存在了。更進一步講,即使譯者進入到認識論的主客分離階段,作為本源性的“是之理解”——相互關系著(being-alongsideness)——從現象學上說是不能全然消除或凈出的。涉及語言,情況更是如此,因為根據海德格爾的語言觀,語言的特征正在于其順手性(the being of readiness-to-hand)。因此,作為“人生—在—世”的譯者在其與翻譯對象的是—在(being-alongsideness)中只能忠實于所譯的“是之理解”,如果“忠實”的含義是讓自顯者以其自身的方式顯現,或者說讓其“如其所是”,即忠實地、不偏不倚地顯現其原貌。這樣想來,“忠實”首先是指譯者的“如其所是”的理解,而且這樣的理解總是以譯者對所譯的能解為根據的。這種能解總是以譯者的在世的方式來進行的。在譯者,即在譯者的是之理解中,世界的理解方式在本體上影響到譯者自身的理解。結果是,譯者不可能跳出其對所譯的“是之理解”而只能忠實于其對所譯的“是之理解”。因為在理解之外無物被揭示(理解之外無他物)。也就是說,在理解之外一切皆昧,皆蔽。因此,難以想象的是譯者能背叛自己的是之理解,而且,甚至“背叛”已經奠基于本源性的“是之理解”。因此,從存在—本體論意義上來理解“忠實”,我們發現“忠實”其實是一種基本的動因,它潛在于人的存在并與人所已經敞開的世界中的實在的存在以“是之理解”的方式保持著一致。
三
“是之理解”是整體的,“忠實”這一概念只能在理解中提出,因此“忠實”本身已經是一種理解。我們可以“不忠實”于在我們的“是—在—世界”中敞開的事物,但這種態度或者心情已經是本源性理解和忠實解釋的派生。也就是說,當且僅當本源性的理解發生以后,我們才有可能知道(認識論意義上)這樣的理解是否忠實,只有在派生的理解中我們才能夠談論對某東西的理解是否忠實。簡單來說,“忠實”或是“不忠實”作為一種有意識的自省努力已經是奠基于本源性的“是之理解”之上的辨認。因此,這里就出現一種困難或不可能:在自己關心的世界中首先理解了順手之物(包括語言)的人(包括譯者)在反思之前將無法談論其理解是忠實的或者相反,所以像“忠實”或是“不忠實”一類的表達只能發生于原初的“是之理解”之后的反思中,而這種反思的認知已經是對所譯的本源性理解的一種派生方式,因此,給這樣的理解(斯坦納稱之為“翻譯之為”)貼上“忠實”或者“不忠實”的標簽,這樣做時其實已經遠離了事情本身(從現象學本體論來講),遠離了存在—本體論的基礎。很難想象人(譯者)一方面不忠實于自己的“是之理解”,另一方面“是之理解”又決定著他的“是—在—世界”中所遇之一切。如果我們的存在(人總是這樣或那樣地“向‘是’而在”,而且總是這樣或那樣地指示自己,我們稱作“存在”)是如此地忠實于我們以至于我們除存在本身之外并無別的本質,我們的存在是“是其所是”地忠實于我們,而且真的是我們不能不忠實于屬于我們自己的存在(是),該存在不僅是我們自己的決定性特征而且被我們的“是之理解”決定著,“是之理解本身是此在之是的決定性特征”[1],而且我們的本質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我們的能是(to be),那么,“是”與“能是”就是我們本身[1]。因此我們沒有作為本質的“是什么”,我們只有作為存在的“是這樣或那樣”。只要我們存在或者能是,我們的“是之理解”就必然忠實于我們,這樣我們才能是其所是。
所以,忠實是我們在“存在—本體論”意義上的“人生—在—世”的內在特征,它根本不能像屬性一樣從我們的理解中增加或去除。也就是說,忠實已經是本源性理解中的內在性。從形式上說,忠實指兩種存在之間的透明:人的理解之是和實在(事物)因此而是的是。顯然,這兩種是之間不僅是透明的而且是同一的。因此,忠實與是之理解之間是如此密切以至于它們不能分離。忠實是原初性理解的內在特征,因為我們的存在是不得不忠實于我們。如果人的本質是存在,也就是說,是由是之理解來明確決定的,那么,作為是之理解的內在特征的忠實從存在上講總是如其所是。因此,我們不能把忠實從是之理解中分離出來,然后回過頭來再拿忠實作為標準來判斷是之理解是否忠實,因為在理解之外我們無從知道什么忠實不忠實;也就說,只有內在于是之理解我們才能夠知道已被明了的某事某物。進一步說,只有在是之理解中我們才能對作為我們的是之理解的某事某物敞開。本源性理解的特征就是其內在性的忠實,舍此無他。只有我們的是之理解是忠實的,我們的存在才能如其所是向我們負責。
四
現在總結一下上述要點:作為“是—在—世界”的譯者本身是“是之理解”的存在者,而“是之理解”發生的方式主要是由譯者的世界的世界性(公共性或他者)決定的。“是之理解”比翻譯更為本源,前者是后者的奠基。在翻譯經驗發生之前,譯者的本體之“是”已經外在于所譯并與作為一種實在的譯者的、總是內在的具體經驗形成對照。“本體之是”和“經驗之是”之間公共性的建立明確地預設了是之理解以及作為其派生方式的翻譯。忠實不是別的而是“是之理解”的內在要求,后者一方面與“是—在—世界”同生共源,另一方面又代表譯者“是之理解”的公共性或他者的內在要求。因此,在當前語境下,當我們說及“是之理解”、“是—在—世界”、“世界的世界性”、“意義世界”、“公共性”和“他者”時,除了它們在揭示“是之理解”(能是)——這一翻譯可能的最終根據——的可能性條件上有側重外,它們之間有著很大的通約性。
在對“忠實”的相關剖析中,我們逐漸明白了忠實不能從“是之理解”中分離出來然后拿它作為標準來判斷“是之理解”是否忠實。我們對“忠實”和“是之理解”之間關系的樸素認識是“是之理解”在存在論上必然要求忠實而不是不忠實,因為作為“人生—在—世”的我們必然要以“是之理解”的理解方式去存在,舍此我們將無法如其所是。我們是此在之人,我們必然會把本體論的是投射到已經事先被我們的“是之理解”照亮的世界中的經驗之物(實在)上去。靠著和通過我們的本體之是我們得以以實體的是來認識實體:“是只在實體的理解中,而實體的是領屬著是之理解。”[1]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有理由認為是譯者根據其直接和切身的翻譯經驗而不是所謂翻譯理論家根據原語與譯語之間的詳細比較首先提出翻譯忠實的問題的。后者根據語言學知識或者意識哲學提出翻譯不忠實的概念,因為他們根據的知識會告訴他們說翻譯忠實僅僅是烏托邦和神話而已,所以忠實只是隨機的、偶然的,而翻譯不忠實對翻譯忠實來說是去神話和讓翻譯忠實通體暴露,所以,翻譯不忠實是經常的、必然的。
五
那些聲稱翻譯忠實是一種神話因此是一種虛幻的崇拜,且這種崇拜必須用解構手段予以粉碎的人,必然是在遠離于我們的本源性理解——我們作為“是—在—世界”因此必然被其占據——那里提問和設定的。何以如此?因為持這種觀點的人一開始便是既把忠實當做對象又把翻譯行為當做孤立的實在來審視和觀察的,而在這樣做時,他們忘記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忠實內在于本源性的理解和忠實本身的言論(the faithfulness about that which talks)。也就是說,是他們言論的忠實性才使他們的言論有所言。他們的言論本身以忠實性為其明確的特征,否則他們的言論將無法是其所是。言論是前理解(foreunderstanding)的一種派生方式而與解釋同生共源。言論的忠實性已經被其奠基性的前理解所決定,因為言談只能談論事先已經被其前理解所揭示的東西,正是前理解或是之理解支持和控制著所談的可能性。那些談論非忠實性的人并不真正知道他們的所談。在談論非忠實性之時他們已使其成為忠實。在談論中,他們有悖于自己的心愿,如果他們的心愿是不忠實的話。他們自我矛盾。因此,如果“忠實”或者其對立面“不忠實”一定要被確立為標準用來衡量翻譯行為是否忠實的話,那么,作為標準的忠實一定不是指是之理解的現象和其派生的翻譯行為(translating),而是指翻譯的別的東西——它是區別于是之理解和翻譯行為的,這種區別使其外在于是之理解并作為孤立之物與是之理解分開而立。但如果是之理解是全包的和決定的(holistic and determinative),一切實在都由其充分決定的話[1],這又如何可能?對這個問題的深入思考,使我們不得不去更加詳細地考察忠實的結構性問題。筆者將另文探討。
[1]Heidegger,Martin.“Being and Time:Introduction”in Martin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M].David Farrell Krell(ed.&trans.)London:Harper Collins Publisher,Inc.,1993.
[2]Heidegger,Martin.Existence And Being[M].Werner Brock Dr.Phil(int.) London:Vision Press Ltd.,1956.
[3]王東風.解構忠實——翻譯神話的終結[J].中國翻譯,2004,(6):3—9.
H059
A
1007-905X(2012)03-0074-04
2011-11-23
屈平(1968— ),男,河南漯河人,河南工程學院副教授,博士。
責任編輯 呂學文
(E-mail:dalishi_sohu@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