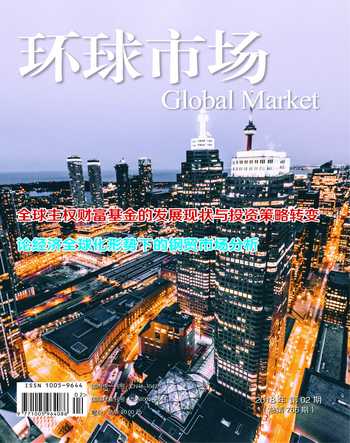企業(yè)文化在企業(yè)管理中的戰(zhàn)略定位分析
李博文
摘要:企業(yè)在多元化的社會經(jīng)濟(jì)市場環(huán)境下,要不斷的強化自身的競爭力以適應(yīng)社會的發(fā)展,企業(yè)文化建設(shè)已經(jīng)成為影響企業(yè)發(fā)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yè)文化代表了企業(yè)的對外形象和發(fā)展理念,促進(jìn)了企業(yè)員工和管理人員之間的和諧關(guān)系,因此,在企業(yè)的發(fā)展中需要創(chuàng)新企業(yè)文化建設(shè),是以促進(jìn)企業(yè)管理效率。
關(guān)鍵詞:企業(yè)文化;企業(yè)管理;戰(zhàn)略定位
一、企業(yè)文化建設(shè)的重要性
(一)企業(yè)文化代表企業(yè)形象
企業(yè)如果要實現(xiàn)良性健康的發(fā)展,首先要做好的就是企業(yè)管理工作,而企業(yè)管理人員在實施管理時,一定要突出企業(yè)的優(yōu)秀文化,才能體現(xiàn)出企業(yè)自身的價值,同時要加強企業(yè)和員工之間的交流,可以讓員工能更好的了解企業(yè)文化。企業(yè)文化如果想要向大眾傳達(dá)信息,都需要通過媒體手段來實現(xiàn),而且企業(yè)在實施企業(yè)文化建設(shè)在企業(yè)發(fā)展過程中,可以幫助企業(yè)更好的傳播文化的思想。不斷加大企業(yè)和社會各界之間的溝通,向其展示企業(yè)的文化,加強和外界的文化的溝通,企業(yè)還要保證企業(yè)內(nèi)部的管理人員和企業(yè)員工之間,可以相互達(dá)成公平平等的協(xié)議,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在于,企業(yè)文化所展現(xiàn)出來的是企業(yè)自身的形象,所以企業(yè)要重視對企業(yè)文化的建設(shè)。
(二)提升企業(yè)核心競爭力
企業(yè)文化同時彰顯了企業(yè)本身的價值和特色。一個企業(yè)在發(fā)展過程中,不僅僅需要展現(xiàn)自身的價值,同時企業(yè)在建設(shè)的過程中也需要擁有更加完整的企業(yè)文化,企業(yè)管理是企業(yè)文化中的重中之重,它反映出來的是企業(yè)自身的文化特色。如果一個企業(yè)想要發(fā)展,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自己的文化價值,創(chuàng)立自己的文化理念。企業(yè)文化建設(shè)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讓企業(yè)在市場競爭中擁有獨特的發(fā)展前景,從根本上提升企業(yè)的核心競爭力。
(三)推動企業(yè)的和諧發(fā)展
企業(yè)在正常運轉(zhuǎn)的過程中,作為企業(yè)的員工,大部分的時間處于工作狀態(tài),企業(yè)的優(yōu)劣和文化環(huán)境,對于員工產(chǎn)生著一定的影響。通常情況下,很多企業(yè)的員工在剛進(jìn)入企業(yè)時,就開始形成相應(yīng)的行為習(xí)慣和交往方式,企業(yè)的文化影響著企業(yè)發(fā)展的方方面面,就企業(yè)長遠(yuǎn)的發(fā)展角度來說,想要讓企業(yè)得到快速發(fā)展,首先就要建立和諧完善的發(fā)展戰(zhàn)略和方向,有利于企業(yè)更好的發(fā)展企業(yè)中的文化。
二、企業(yè)文化環(huán)境對企業(yè)管理的影響作用
(一)企業(yè)文化環(huán)境確立了企業(yè)管理的導(dǎo)向性
從企業(yè)文化的塑造上看,企業(yè)所具備的獨特的思潮對員工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企業(yè)形成了特有的文化體系,將通過管理者的塑造對企業(yè)的發(fā)展起到重要的導(dǎo)向作用。這一思想導(dǎo)向使企業(yè)文化環(huán)境的構(gòu)建變得更加緊密。它是企業(yè)發(fā)展的核心,能夠幫助企業(yè)在運營管理的過程中,進(jìn)一步聯(lián)系企業(yè)實際情況,制定完善的發(fā)展目標(biāo),確保企業(yè)管理和制度化建設(shè)中保持正確性和科學(xué)性。
另一方面,在企業(yè)文化的導(dǎo)向作用上,通過企業(yè)文化環(huán)境的渲染,能夠?qū)ζ髽I(yè)的領(lǐng)導(dǎo)層和企業(yè)員工進(jìn)行自主引導(dǎo)。首先,企業(yè)文化將會對企業(yè)的經(jīng)營哲學(xué)以及企業(yè)價值觀念形成健康的指導(dǎo)。企業(yè)的經(jīng)營方式和處事原則都是由企業(yè)的經(jīng)營哲學(xué)多決定的。這些思維方式和發(fā)展原則將對于企業(yè)領(lǐng)導(dǎo)層的具體領(lǐng)導(dǎo)做出決策性的指引,使員工能夠在經(jīng)營管理的過程中,對企業(yè)運營活動保持嚴(yán)密的監(jiān)管。使企業(yè)文化能夠在企業(yè)內(nèi)部形成統(tǒng)一的價值觀念,確保企業(yè)員工能夠采取更加科學(xué)有效的方法,使企業(yè)全員能夠統(tǒng)一發(fā)展方向。其次,企業(yè)文化有利于在企業(yè)內(nèi)部形成正確的發(fā)展目標(biāo)。幫助企業(yè)從科學(xué)的角度出發(fā),制定嚴(yán)格的戰(zhàn)略和計劃,保障企業(yè)決策的民主性和科學(xué)性。這樣一來,企業(yè)管理的方式將不再單調(diào),企業(yè)管理技術(shù)在更新的過程中,確保企業(yè)管理理念不斷創(chuàng)新。
(二)企業(yè)文化環(huán)境加深了企業(yè)管理的本質(zhì)性
眾所周知,企業(yè)是以經(jīng)濟(jì)效益為核心的運營管理模式,其發(fā)展本質(zhì)具有一定的穩(wěn)定性。企業(yè)文化環(huán)境建設(shè)能夠進(jìn)一步加深企業(yè)內(nèi)部的激勵和凝聚作用。在企業(yè)管理中,管理者通過各項規(guī)章制度,能夠以硬性跳躍來推進(jìn)企業(yè)員工的具體行為。利用企業(yè)文化的構(gòu)建,能夠結(jié)合企業(yè)管理的具體方向,通過個體化的發(fā)展措施,實現(xiàn)企業(yè)員工到企業(yè)潛能的發(fā)展,為企業(yè)未來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更加全面的價值。使企業(yè)管理工作變得更加人性化。企業(yè)內(nèi)部工作氛圍更加和諧。在突破管理方法的同時,進(jìn)一步延伸企業(yè)管理工作的實施成效。
在企業(yè)發(fā)展進(jìn)程中,個人利益與企業(yè)集體利益的融合和依存十分困難。這也給企業(yè)的管理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難度。企業(yè)文化所具有的調(diào)試作用及約束作用,能夠緩解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之間的矛盾,通過統(tǒng)一的價值觀念,對員工們的行為道德進(jìn)行全方位的約束。通過企業(yè)內(nèi)部統(tǒng)一的價值觀念及道德行為準(zhǔn)則,能夠為企業(yè)的管理提供強大的助力。加深企業(yè)和個人價值的相互融合。提高企業(yè)管理工作的發(fā)展成效,為企業(yè)管理的本質(zhì)性夯實發(fā)展基礎(chǔ)。
(三)企業(yè)文化環(huán)境有助于企業(yè)管理的開創(chuàng)性
在哲學(xué)領(lǐng)域中,有這樣一段論述:“真正的進(jìn)步是新事物取代舊事物的進(jìn)程”。量變積累質(zhì)變,這一道理對于企業(yè)的發(fā)展具有重要的影響。企業(yè)在管理進(jìn)程中,要不斷創(chuàng)新時代發(fā)展理念,推動企業(yè)具備更加強大的管理創(chuàng)新,繼續(xù)積蓄強大的思想動力。
當(dāng)前形勢下,企業(yè)文化環(huán)境的構(gòu)建在創(chuàng)新發(fā)展中具有實質(zhì)性的作用。很多企業(yè)為了適應(yīng)市場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不斷更新思想觀念,試圖通過現(xiàn)金的理論與經(jīng)驗促使企業(yè)實現(xiàn)創(chuàng)新式管理和發(fā)展。企業(yè)的經(jīng)營管理者要注重經(jīng)營理念的改變。企業(yè)只有在更加穩(wěn)固的文化基礎(chǔ)上,才能夠?qū)ζ髽I(yè)管理進(jìn)行創(chuàng)新,堅持企業(yè)文化的人性化發(fā)展理念,使員工并能夠立足于企業(yè)事實,進(jìn)行更加高效的企業(yè)管理。
三、結(jié)束語
現(xiàn)代企業(yè)面臨的市場環(huán)境非常復(fù)雜,企業(yè)之間已經(jīng)發(fā)展成為了全面競爭的關(guān)系,企業(yè)文化代表了企業(yè)的發(fā)展理念,是推動企業(yè)管理發(fā)展的重要因素。良好的企業(yè)文化是企業(yè)實施高效管理的基礎(chǔ),為企業(yè)人員樹立了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所以企業(yè)文化建設(shè)直接影響著企業(yè)管理的效率。
參考文獻(xiàn):
[1]欒強.我國企業(yè)文化建設(shè)亟待解決的問題及對策[J].山東社會科學(xué),2017(01):141-144.
[2]凌竹君.企業(yè)文化對企業(yè)核心競爭力的影響研究[D].天津財經(jīng)大學(xué),2016.
[3]張志學(xué),張建君,梁鈞平.企業(yè)制度和企業(yè)文化的功效:組織控制的觀點[J].經(jīng)濟(jì)科學(xué),2006(01):117-128.
[4]黎永泰.企業(yè)文化管理初探[J].管理世界,2001(04):163-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