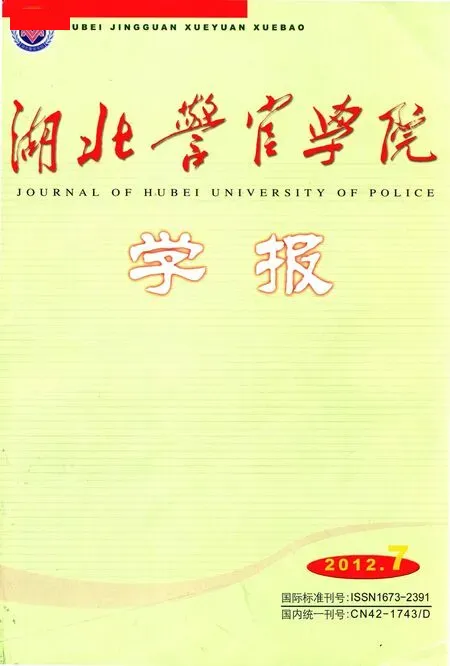重慶“地票”改革的價值及限度
陸 劍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法學院,湖北 武漢430073)
重慶“地票”改革的價值及限度
陸 劍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法學院,湖北 武漢430073)
“地票”交易是指建設用地掛鉤指標交易。“地票”交易通過城鄉建設用地實物資產的證券化,以指標交易為核心,能夠從體制內優化城鄉建設用地的結構失衡。但“地票”交易并沒有最大限度實現農民的土地權益,也未能恰當處理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的發展預期關系。雖然其啟動了對農地的價值發現運動,但對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作用仍是十分有限的。
“地票”改革;建設用地;復墾;耕地
作為全國城鄉統籌試驗區,重慶在不改變土地權屬和現行土地制度的前提下,在全市范圍內通過“地票”交易制度,力圖進行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制度創新。經過3年多的實踐,“地票”成交均價由每畝8.02萬元提高到16.7萬元。截至2011年8月中旬,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已組織“地票”交易23場,成交價款103.29億元。[1]
一、“地票”的概念與運作模式
按照《重慶市農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實物交易和指標交易均可在農村土地交易所進行。所謂“指標”就是“地票”,即建設用地掛鉤指標。在農村土地交易所進行交易的“地票”是指農村將宅基地等集體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經土地管理部門驗收后讓渡出的可用于建設的用地指標。就《暫行辦法》而言,“地票”并不是土地的票據化,也不是土地權益的票據化,更不是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票據化,而是指標的票據化。指標是一種資格,也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權利,“從法律上來講就是一種授權性政策規定,即如果擁有某種指標,則有資格有權利做某種行為”。[2]依照《暫行辦法》第27條,“地票”的首要功能為“納入新增建設用地計劃”,“增加等量城鎮建設用地”,即“地票”產生了增加城鎮建設用地的資格和權利。[3]
根據《暫行辦法》,“地票”的運行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步驟:第一,重慶市國土資源局依據總體規劃要求,編制城鄉建設用地掛鉤專項規劃,經市政府批準后實施;第二,經村民(代表)大會三分之二同意,對閑置的集體建設用地申請立項,經區縣土地局同意后方可組織復墾,經復墾而新增的耕地繼續由原承包農民經營;第三,集體建設用地復墾后,對于經土地局驗收合格所產生的建設用地指標,由市土地局發給土地使用權人相應面積的“地票”;第四,由市土地局制定統一的城鄉建設用地掛鉤指標交易基準價格,供交易雙方參考;第五,“地票”交易應當在農村土地交易所展開,交易總量原則上不超過當年國家下達的新增建設用地計劃的10%;第六,除繳納少量稅費外,“地票”交易的絕大部分收益歸農戶所有;第七,“地票”作為建設用地掛鉤指標,在使用時可納入新增建設用地計劃,增加相同數量的城鎮建設用地,并在“落地”時沖抵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和耕地開墾費,但仍須辦理征收程序,完成對農民的補償安置。在土地被征收為國有之后,有關主體通過出讓程序依法取得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
二、“地票”制度的背景與價值
早在2005年,國土資源部就頒布了《關于規范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試點工作的意見》,提出選擇湖北、安徽等省市進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項目試點。2008年6月,國土資源部正式下發《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管理辦法》,對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的具體操作辦法進行了規定。重慶“地票”交易制度與其他試點地區的掛鉤試驗有所不同:一是真正實現了在直轄市一級進行“異地置換”掛鉤試點,超越了掛鉤試點的市、縣行政區劃界限。二是真正實現了“地票”價格統一。“地票”交易是將不同地域的建設用地掛鉤指標進行打包交易,然后按照面積大小分配所取得的收益。“地票”價格僅與最終拍賣價格有關。三是把實物形態的土地交易轉化為票據形態的指標交易。“地票”將建設用地掛鉤指標票據化,將土地資產轉化為可流通的票據。四是先復墾后占地,減少了增減不掛鉤的風險。“地票”交易要求先將集體建設用地復墾,經驗收合格后再增加城鎮建設用地指標。
作為面積最大的直轄市,重慶市是一個大城市和大農村的結合體,具有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在發展過程中,其既存在城市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問題,又存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缺乏退出和利益實現機制,大量集體建設用地閑置的現象。最近十年,重慶市的城市化率提高了25%,但宅基地減少不到1%。目前,集體建設用地總量是城市的4.6倍。[4]隨著村莊、企業、學校和醫院的沒落,集體建設用地大量閑置;隨著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農民的宅基地也大量荒廢。由于城鎮建設用地采用“先占后補”的模式——“占地在先補地在后”,導致了“只占不補”、“占優補劣”和“多占少補”的現象,很難保證后續補充耕地的數量與質量,長此以往將造成耕地總量減少,進而危及糧食安全。重慶市未來對建設用地的需求將持續增加。截至2010年,其建設用地需求量為6.73萬公頃,其中需占用耕地3.18萬公頃;據預測,到2020年,建設用地需求量為18.43萬公頃,其中需占用耕地8.26萬公頃。[5]如何解決城鄉建設用地發展不均衡的問題,成為統籌重慶城鄉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
“地票”交易制度使農村閑置的集體建設用地通過復墾的形式變為耕地,從而讓渡出建設用地的指標,使其成為可以入場交易的“地票”。“地票”交易是城鄉建設用地資產實現的票據化,有利于在體制內優化城鄉建設用地的結構性矛盾。其不僅可以降低集體建設用地在非法領域內的流轉成本和制度風險,還能通過土地資產的貨幣化最大限度地節約耕地,實現農村和城市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地票”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城鄉建設用地的大范圍置換,有利于實現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價值,既滿足了城市發展的現實用地需求,又迎合了利用城市資金反哺農村、促進新農村建設的現實需要。“地票”制度以“先補后占”替代“先征后補”的“占”“補”平衡模式,既保證了新增耕地的數量與質量,又為閑置的集體建設用地建立了退出機制。在“地票”制度施行后,重慶市主城區的國有經營性建設用地將實行“持票準入”制度,即要取得國有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必須持相應面積的“地票”方可報名參與競買。這將使企業之間的競爭提前,從單純地爭奪國有土地使用權演變為爭奪建設用地指標,促使“地票”價格呈現上漲趨勢,從而獲得更多的資金以反哺農村。
三、“地票”制度的缺陷與走向
“地票”制度將集體建設土地和城鎮建設土地掛鉤,“地票”交易市場的建立使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成為可能。但“地票”制度的缺陷也很明顯:首先,“地票”制度并沒有最大限度實現農民的土地權益。誠然,“地票”制度使農戶在集體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后獲得了一定的現金收益,但集體建設用地復墾后產生的指標價值和集體建設用地本身的價值是截然不同的。“地票”因集體建設用地復墾而產生,其轉讓成交價減去土地復墾的成本才是給村集體和農民帶來的凈收益。從實體上考慮,這僅僅包括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和耕地開墾費。按照重慶市的收費標準,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按四等計收,每平方米40元;耕地開墾費為15元—20元/平方米(公益性用地耕地開墾費按15元/平方米收取,其余用地按20元/平方米收取,占用基本農田的收費標準上浮80%)。集體建設用地被復墾為耕地后,農民將離開村莊,搬進城鎮居住,獲得的補償金額一般在5萬到10萬元之間。雖然農民的居住條件得到了改善,他們也有權繼續耕種復墾耕地,但失去的是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和未來可能的土地增值。因此,基于現實利益考慮,城郊農戶并不愿意將集體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目前,“地票”的利益分配框架為:農民房屋補償和購房補貼份額最大;其余依次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補償、復墾成本、耕地保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專項資金以及彌補指標“落地”政府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的資金。可見,僅僅依靠轉讓“地票”所獲得的收益,是無法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的。“地票”“落地”時,依然要依靠公權力對集體土地進行征收,并作為國有建設用地進行轉讓。“地票”制度使城鄉建設用地指標的增減相掛鉤,但在“落地”時,地方政府是否能從土地出讓金中拿出部分資金反哺農村,仍是一個疑問。如何最大限度保障村集體和農民的土地權益,直接影響著“地票”制度的長遠發展。
其次,應妥善處理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發展預期的問題。重慶市部分發達地區通過“地票”交易獲得了充足的建設用地指標,可以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而欠發達地區通過“地票”交易獲得了存量建設用地換取的貨幣化收入,短期內燃起了復墾建設用地的熱情,卻喪失了未來發展所需的建設用地指標。從理論上看,這些欠發達地區仍可通過“地票”交易獲得未來的建設用地指標,但其中的成本無疑會大大增加。[6]因此,“地票”交易固然能夠促進發達地區的進一步發展,但未必能有效解決地區發展不均衡的難題。總之,通過“地票”交易,欠發達地區雖然在短期內獲益良多,但從長遠來看,卻未必是受益方。在實踐中,主城區周邊的集體土地價值較高,農民并不希望將集體土地轉變為“地票”,而更愿意等待土地征收,借助城市周邊農地轉非農地的豐厚溢價獲得較高的征地補償金。而遠郊區縣和偏遠地區的農民則愿意通過土地換取“地票”收益,因為偏遠地區的土地價格遠遠低于“地票”價格。不論農民自己耕種或出租復墾后的集體建設用地,都是一筆劃算的買賣。[7]由此可見,并不是所有的農民和村集體都是“地票”交易機制的長期受益者。
最后,“地票”制度是在現行法律框架內的重要改革。它啟動了對農地的價值發現運動,但對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作用依然比較有限。“地票”交易僅僅在一級市場內進行,政府并未開放二級交易市場。這可能會危及“地票”持有人的權益,即擁有“地票”并不意味著擁有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因為取得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仍需借助土地征收行為。《暫行辦法》只賦予了“地票”持有人對建設用地地塊的選擇權,即可以在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范圍內找尋尚未被征收且符合自身需求的建設用地。在選定地塊后,其再向政府提出征收建議。在政府按程序進行征收后,該地塊仍作為經營性建設用地進入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程序。在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過程中,“地票”持有人和其他競買者處于平等的競爭地位,并不享有在同等條件下對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優先購買權。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其壟斷了城市建設用地的二級市場,“地票”交易在客觀上可能會造成地方政府對土地的短期超額儲備。在現行制度框架內,地方政府的土地儲備行為需受中央政府關于建設用地指標的控制。通過“地票”交易,地方政府將擁有更多的建設用地指標,而該指標所表征的將是巨大的經濟利益。地方政府大規模儲備農地的態勢將進一步蔓延,可能會強化其壟斷土地發展權的非均衡利益分配模式,而中央政府通過土地進行宏觀調控的效果將受到一定的影響。中央的土地宏觀調控政策主要是基于數量的土地宏觀調控,即政府直接決定土地數量分配方案,在此基礎上由土地市場發揮具體的調節作用。[8]而“地票”制度的運作將使中央政府基于數量和可轉讓配額的土地宏觀調控措施部分“失靈”,對于地方政府過度依賴土地的發展模式而言,則存在進一步失控的可能。
綜上,“地票”的價值是可以量化的,實際上僅僅體現為“地票”“落地”時沖抵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和耕地開墾費。市場化運作和指標稀缺性所帶來的溢價將以一定的比例返還給農民。由此可見,“地票”制度對構建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市場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與“逐步建立統一的城鄉土地交易市場”,“提升農村特別是偏遠地區的土地價值,有效地促進農村增收和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的目標還存在一定的差距。筆者認為,重慶“地票”試驗要真正透過妥當的收益分配滿足各方利益主體的訴求,關鍵在于對農民和村集體意愿的尊重和利益的保護。
[1]李愛莉.重慶新土改三年,檢驗地票交易制[J].農經,2011(7):10.
[2]郭振杰,曹世海.地票的法律性質和制度演繹[J].政法論叢,2009(2):46.
[3]郭振杰.地票的創新價值和制度突破[J].重慶社會科學,2009(4):71.
[4]程世勇.地票交易:體制內土地和產業的優化組合模式[J].當代財經,2010(5):6.
[5]陳悅.重慶市統籌城鄉中的土地流轉制度改革[N].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10-10-07.
[6]程世勇.地票交易:模式演進和體制內要素組合的優化[J].學術月刊,2010(5):71.
[7]陳燕,姚佳威.重慶地票繼續試[J].財經,2011(2):23.
[8]靳相木.地根經濟[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67.
D922.32
A
1673―2391(2012)07―0112―03
2012—03—15
陸劍,男,江蘇鎮江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
本文獲第51批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資助,編號:2012M511308;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09&ZD043)。
【責任編校:王 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