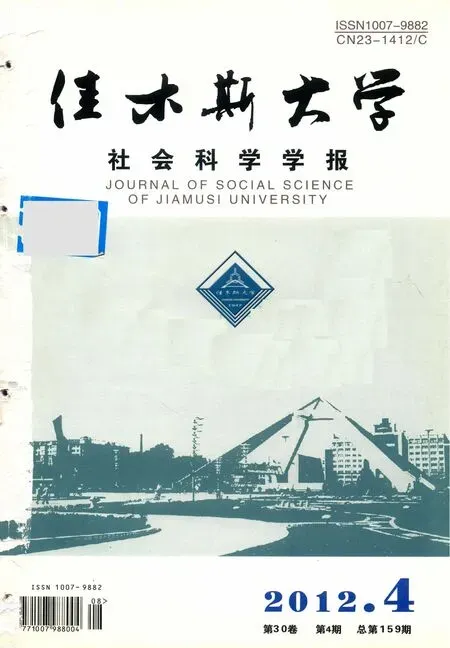我國古代社會鄉村社區治理的政治藝術①
李雪彥
(安順學院政法系,貴州安順561000)
我國古代社會鄉村社區治理的政治藝術①
李雪彥
(安順學院政法系,貴州安順561000)
維護既存政治秩序是每一代統治者的共同任務。但是,時代不同,他們在維護統治秩序過程中所采取的手段和策略也會有所差異。我國古代社會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鄉村地域極為遼闊,農民居住也相當分散,村莊之間亦呈相互隔絕之態勢。面對此種情形,統治者們將司法、宗族及鄉紳等方面的力量綜合起來加以運用,以實現對鄉村社會的有效控制。
古代社會;鄉村治理;政治藝術
政治藝術之一:司法控制
現代意義上,法律指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以規定當事人權利和義務為內容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社會規范。由于這些社會規范具有超強的嚴謹性、懲罰性及制約性,且通常有外在的暴力機構來輔助其實施,因此在調停社會矛盾和維持社會秩序方面,法律具有其他一般規范及教化所不具備的絕對優勢。正因為如此,法律被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及各政治權威奉為治國的經典術謀。在西方,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就將法律視為“最優良的統治者”,指出“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感情用事的人們較為優良。法律恰好是全無感情的,人類的本性使誰都難免有感情”[1](P163),“讓一個人來統治,這就在政治上陷入了獸性的因素”[1](P171)。在這一方面,我國也不甘落后,在先秦時期便涌現出了一些推崇法治的思想家。如春秋時期的管子就用“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管子·形勢解》)的簡單話語來概括了法的涵義,并進一步指出:“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實用也”、“不法法,則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法者則民之父母也”《管子·論法》),強調了法在國家治理方面的超強價值。
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古代社會的這種“法治”思考突破了理論爭鳴之局限,而進一步向實踐轉化。結果,在政治權威的催促下,我國形成了較為全面的古代法律體系,用以維持社會的有序運轉。那么,在鄉村社區的治理過程中,國家的這種法律體系有沒有價值呢?筆者在此提出這個問題的原因在于:長期以來,學術界有一種主流觀點,認為中國古代的官治行政以縣級政權為終端,即所謂“王權止于縣政”,縣以下之廣大鄉村社會,統治者采無為而治之策,聽民自為、自營。因此,對于鄉村的社會成員來說,國家的法律基本不起作用。
筆者以為,從歷史實踐去考察,受行政成本、國家權力之分配模式及傳統文化等因素影響,我國古代的政治權威確實將國家之外的社會組織當作農村管理的中堅力量。但是,這并不能否定國家法律在鄉村管理中所產生的價值。對于這一點,我們是可以從相關的記載中找到證據的。如山東費縣趙氏家譜《家規》就明文規定:“凡本族不肖子孫私自砍伐祖墳林木者,逐出本族,死后不得入祖墳,并送交官府法辦。”[2](P312)另,南海廖氏《家規》“禁淫穢”條分列三款:第一,服屬內乖戾失倫,送官按例治罪,當事人永遠革籍;第二,言語調戲婦女而生出事端,小則停三年,大則送官懲治;夜如人家,妄思無禮,或隱匿窺探,或恃酒胡鬧,本人停胙三年。[2](P131)光緒休寧《葆和堂冠婚喪祭及掃墓差遣各仆條例》也規定:“朝廷號令甚嚴,于斗牌、打架、賭博、盜竊四事,法在必究,更覺凜然。爾等小心安分,庶可以保身家。設有犯此四事者,鳴官究治理。”湖北麻城宣統年間的《鮑氏宗譜》則干脆指出:“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媳者,免祀,送官治罪。”[3](P601)
可見,我國古代社會統治階級通過國家法律對鄉村進行控制的行為,即所謂的“鳴官”、“送官治罪”是存在的。但需注意的是,這種控制有其自己獨特的行為方式。簡而言之,國家法律對鄉村的調控主要以人為對象,對觸犯國家法律的鄉民進行制裁,進而達到維護鄉村正常秩序的目的。然而,正如學者所言,“古代中國人為了尋求指導和認可,通常是求助于這種法律之外的團體和程序,而不是求助于正式的司法制度本身”[4](P3),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國家法律對鄉村的干涉、介入現象并不常見。若村民們發生一般性糾紛,通常他們也不直接尋求國家法律來解決,而是首先求教于宗族等傳統性社會力量。只有當族內的權威人物和機構不能處理,或其對處理結果不滿意的時候,才會選擇“鳴官”。所以,同其他政治藝術相比,我國古代社會統治階級對鄉村的司法控制只是一種“后位”選擇。
政治藝術之二:宗族管轄
何為宗族?目前的學界無一致性的回答。綜合各學人的觀點,大概可以做如下歸類:其一,對宗族進行靜態的描述。如學者劉宗棠就給宗族下了一個定義,認為“宗族組織是指世代聚居在一起的男性祖先的子孫,以血緣為紐帶,以地緣為基礎,以財產為保障所形成的一種社會組織形式”[5]。其二,用運動的觀點來詮釋宗族。如李錦順、章淑華曾撰文,提出了“宗族不是一個凝固不變的概念,社會的演變和發展賦予了宗族新的內涵”。筆者以為,同其他眾多的社會科學領域內的術語一樣,由于立場、視角的差異,人們對宗族具體內涵的表述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但綜合各類學術觀點,我們又發現幾乎所有對宗族有所研究的人都沒有背離宗族組織的基本特性:其一,宗族以父系血緣為紐帶;其二,宗族是一種社會共同體。因此,在本文中我們以最粗略的方式將宗族看做是以父系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社會人群的共同體。那么,接下來的問題便是,這種共同體在我國古代社會的鄉村治理過程中究竟有沒有發生過作用?對于該問題,筆者認為可從下述幾個方面來理解。
(一)教化及控制鄉民
政治教化是每一個階級社會都面臨的重要課題。但是,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統治階級推行教化的手段卻是有極大差異的。在我國古代社會,受地緣偏僻、通訊設施欠缺、經濟發展滯后、行政體制安排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統治階級將農村地區的教化、控制權賦予了同鄉民息息相關的民間組織——宗族。為了完成此目標,該組織通常先制定內容全面而復雜的行為規范系統,以為農人提供行事依據。盛行于我國古代鄉村社會的各種族規、族約、家典、祖訓即是證明。然后,再對這些家族法規進行宣講。如黟縣環山余氏宗族《余氏家規》就規定:“每歲正旦,拜謁祖考。團拜已畢,男左女右分班,站立以定,擊鼓九聲,令善言子弟上正言,朗誦訓誡”[6],另存在于家族內部的講正、講副即是負責宣講各種族規家法的機構。最后,為了保證家族法規的權威性,宗族組織還被國家賦予了強制性的懲處權力,專門懲辦那些違背了家族法規的個體。其方式有多種,常見的包括訓斥、罰站罰跪、罰款、責打、出族、處死等。概而言之,在家族組織這種有軟有硬的干涉下,我國古代鄉村社會中男女老少的言行被普遍地限制在各種規則以內,很少有越紀現象。
(二)調處民間糾紛
在中國古代社會,地方公共權力的分配與設置具有諸多的不合理性。筆者以為,最為突出的一點是地方行政權同司法權混同使用。地方公共權力的此種特性給地方行政官員帶來了繁重的工作任務,他們不僅要決訟斷辟、勸農賑貧,還要興養立教,可以說“凡貢士、讀法、養老、祀神,靡所不綜”。在這種情形下,地方官吏要親自去處理農村的各種糾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古代官僚體制下,政府通常將政權與族權相結合,利用宗族來調處鄉村的各種紛爭。這一點,有相關的史料可以明證。如江西按察使凌鑄就實行過“族約制”,由地方官授予宗族牌照,以達排難解紛之目的:
凡有世家大族,丁口繁多者……地方官給予牌照,專司化導約束,使之勸善規過,排難解紛。子弟不法,輕則治以家法,重則稟官究處。至口角爭忿、買賣田墳,或有未清事涉兩姓者,兩造族約會同公處,不得偏袒。
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宗族組織在調處各種民間糾紛時的重要角色。那么,具體一點,這些宗族組織是如何進行調處的呢?為了更好地回答這個問題,筆者從三個層面予以論述:
其一,處理糾紛之主體。對此,經過梳理,筆者發現古代宗族內普遍設有族長、房長、家長等專門機構來處理斗毆、戶婚、田土等一般性爭訟。這可從一些家規、宗譜中找到依據。如廬江府何氏家記中就規定到:“族有念事,非奸盜人命重事,不得冒官司,須投房長、主祠,分剖是里”。(《廬江郡何氏家記》山陰華舍趙氏亦準許族人將不教不悌、凌辱尊長、欺辱孤寡、不務正業、霸田占產者扭送宗祠,而后由族長、房長會同族中執事進行會訊,然后決定是否請出祖宗的“家法”來加以處置。(《山陰華舍趙氏宗譜》卷首《家規》)另蕭山管氏宗族也規定:族中“立通糾二人,以宗一族之是非,必選剛方正直、遇事能干者為之。凡族人有過,通糾舉嗚于家長”。(浙江蕭山《管氏宗譜》卷4)
其二,調處糾紛之范圍。在我國古代社會,宗族共同體對農人糾紛的處理范圍是相當廣泛的,概括起來主要有:第一,調處財產繼承買賣之矛盾。如蔣灣橋周氏宗族便規定“族內昆仲叔侄或因財產爭論,應聽族長及公正者調處,不得偏執己見”。(《蔣灣橋周氏續修宗譜》卷一《家規》)另,光緒年間,江蘇句榮縣民余人俊為其三個兒子分割遺產。余人俊的妻弟主張將全部遺產分為九份,兩嫡子各取三份,一庶子取二份,余人俊本人留一份作“養贍之資”。房長余人龍出面干涉,主張三字均分。最后經縣衙審理,同意房長余人龍的處理意見;第二,協調婚姻締結之糾紛。如涇川萬氏《家規》第十二條就指出,“嫁娶不拘貧富,惟擇閥閱相當。若貪財賄以淆良賤,有玷門戶多矣。吾族除以往不究,今后凡議婚納配,須鳴族商議,果系名門,方許締姻。如不鳴眾或門戶不相當者,合族共斥,譜削不書”。(《涇川萬氏宗譜》《家規》)另,道光十一年李氏家族《宗歸》亦規定“本房長、戶首即宜苦諫力阻,或該妻實系犯出,亦必經鳴房長、戶首,會同查議。公論無飾,方許從權,否則斷乎不可”。(《李氏宗譜》卷二《家規》);第三,調處輕微刑事糾紛。
其三,調處糾紛之程序。在我國古代社會,對于因觸犯族規家法而產生的案件,大多沒有固定的審理程序和模式。但是有幾點必須注意:其一,對于違反習慣法的案件,必須先向宗族組織投訴,而不能直接報官;其二,案件的處理絕大多數在祠堂內舉行,由族長、房長會同族中有名望者一起負責;其三,族長對案件作出判決以后,即發生效力,他人不能提出異議,也不存在二審程序。
總之,憑借上述家族內部的調處,在國家法律難以延伸至鄉村,鄉村社區各類關系及糾紛不可能全部依靠國家法制來協調的年代,中國農村社區的違規違紀甚至是違法行為得到了有效的處理,大大降低了因農人糾紛而導致鄉村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失控的風險。
(三)族內福利救濟
在我國古代社會,農民對土地具有極強的依賴性。可以說,他們所需要的生活、生產物資,基本都自于農業生產所得。然而由于生產技術、工具及設施的落后,農民即使辛苦生產、勤快勞作,其收入也相當有限。扣除應繳納的各種稅收外,農民已所剩已無幾。因此,農民必然成為傳統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客觀上需要社會的救濟與輔助。可惜的是,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歷代的統治者均將征稅、征兵以維護政治穩定作為自己最大的政治任務。對于采取措施發展經濟以促進社會福祉則保持著較為冷淡的情緒。
國家在救助鄉民問題上的行為缺失導致了在農村社區中,出現了許多需要救助而得不到救助的貧苦窮人。這部分人的存在,對于鄉村安全來說,無疑是危險地。這一點,宗族組織似乎也早已發現。因此,他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承擔起了經濟互助任務。在現實中,這種幫扶主要通過族內賑施來完成。對此,有相關的資料可以證明。如,(《樊重傳》)《東觀漢紀》就曾描述道東漢的劉般:“遷宗正,在朝廷竭忠盡節,勤身憂國,夙夜不怠,數納嘉謀,州郡便宜,清靜畏懼,受職修治,賑施宗族”。《后漢書·朱暉傳》也指出,“建初中南陽大饑,米石千余,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贏者,鄉族皆歸焉”。從這些零星的記載中我們可以明顯領略到宗族在族員救濟方面的重要作為。實質上,為了使這種救濟正規化,在實際生活中,許多宗族普遍設有公產——族田,以為賑施提供強有力的經濟支撐。具體說來,族田通常被分為三類,其中祀田的產出用作祭祀,義莊田的收入用于賑濟貧苦族人,書田則用于支付宗族學塾的經費。甚至,為了避免宗族公產的流失,他們還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體制。如義莊內就設有莊正、莊副職位,以負責收租、保管及出納的工作。
總之,鄉村社會的這種族內救濟活動分擔了窮困鄉民的經濟負擔,撫慰了他們的失衡心理,舒緩了民間矛盾,為鄉村秩序的穩定消除了隱患。
(四)傳承鄉村文化
鄉村管理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即使在經濟欠發達的小農社會,其所涉及的事務也是多維而復雜的。除了上述所講的政治與經濟層事務外,鄉村文化的傳承亦是我國古代鄉村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在這一問題上,宗族組織也承擔了絕大部分的功能。概括起來包括:
第一,組織祭祖及修編族譜。祭祀是宗族最為重要和嚴肅的事情。為了更好地開展祭祖活動,我國古代鄉村社區的許多宗族都建造了祠堂,并同時制定了一整套的祭祀規則,具體包括祭祀儀式、祭器祭品、出席人員、糾察設置、祭后議事、祭祠費用及對無故缺席的處罰等。另外,祭祀種類也較多,除祭祠外,常見的還有清明掃墓,忌日及節日祭祀等。族譜是宗族的歷史,是宗族活動的記錄,也是宗族文化得以傳承的媒介。因此,在宗族文化興盛的古代社會,修編族譜便成為了宗族組織除祭祖之外的另一項重要活動。
第二,制定鄉規族約。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家族組織主要依靠家族法來規范、調節鄉村的各種關系。因此,制定家族法規便成為了家族組織的一項主要文化活動。那么,這些族規祖訓是如何制定的呢?對此,沒有統一的規定。一般情況下,宗族法規由族內有聲望的“賢達”、“族望”組成臨時機構來主持制定,族長與副族長則會參與到其中。宗族法規草案制定后,通常還要在宗廟、祠堂中宣讀,通過即生效。為了增加族規的威懾力,有的宗族法規甚至還要以文本的形式進行公布。通常,這些生效的家族條例內容非常復雜,涉及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職業選擇、婚姻締結方面的規定,也有綱常倫紀遵守、族人糾紛協調層面的條款,甚至連參與宗族、娛樂活動都有詳細的規定。不僅如此,宗族組織還要相應地制定處罰措施,以保證其效力。
第三,登記族內人口。在我國古代社會,人口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象征著一個家族勢力的大小。因此,家族組織常將掌握族內人口數量作為一項重要任務。為此,許多宗族設立“紀年簿”一類的東西,登記所有的族人。對于那些新出生的人,也要在規定的時間內報告族長,以使之登錄在冊。此種登錄,使得宗族能夠將族人編制起來,以為自己的內部管理提供條件。
憑借著這些活動,我國古代鄉村社會形成并沿襲了一種以宗族為單位,以祖宗崇拜為核心的特殊文化。在這種文化系統中,人們形成了強烈的道德感、歸屬感,對祖宗、祖法普遍懷有敬畏心理,表現在行動上便是對宗族法規的絕對屈服,不敢越雷池半步。雖然今天人們對這種鄉村社會文化的價值依然褒貶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家國同構的鄉村文化為鄉村社區秩序的穩固提供了心理基礎。
政治藝術之三:鄉紳有限自治
鄉紳的含義,學界無嚴格規范的概念,在我國古代社會一般用來指稱那些有功名卻居于鄉村的人。從內容上看,鄉紳又可細分化縉紳和紳衿兩個等地。前者指退職的文武官員,以及封贈、捐買的實、虛銜之官。后者則包括有功名卻未致仕的舉、監、生、員等,他們常著青襟之服,以示同農人之區別。
作為科舉制度及學校制度所造就的一個特殊階層,鄉紳被國家賦予了一般平民所不具有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特權。憑借著這些特權,鄉紳比其他人更容易在鄉村事務中拋頭露面。而且,他們或者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或者企圖攫取一定的經濟利益,或者兼而有之,也往往樂于在地方社會事務中發揮作用。與此同時,我國封建社會直接接近農村的縣級行政單位,實行回避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知縣以上的行政官員基本不在原籍任職。因此,新上任的地方官對本地的情況很不熟悉,甚至不懂地方性語言。他們履行公務的時候,更多地依靠衙役、書吏和幕僚。而這些辦事人員除了收稅、稽捕等需要出勤以外,皆高居衙門,基本不同鄉人打交道。中國傳統社會的這種幕僚制度,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國家與鄉村社會、行政機構同平民百姓的大程度分離。而這對于一心想控制某種既定統治秩序的政治權威來講,無疑是危險的。為此,他們也急需一個能夠擔當“上情下達,下情上傳”的群體來連接已經分離的鄉村與國家,以加強其對鄉村社區的控制。在這種形勢下,鄉紳階層得到了蓬勃發展,并在鄉村秩序的維護中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一)溝通官民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在古代,我國以官僚體制為載體的國家權力未有效地延伸至廣大基層社會。可以說,在對鄉村社會的統治中,國家權力是空缺的。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面對地域遼闊的鄉村,居住分散的農民以及散漫平鋪的“蜂窩狀結構”的自然社會,統治者要更牢固地控制鄉村就必須培植一個既能代表國家又能代表鄉村的中介性群體來為其對鄉村的控制提供服務。鄉紳便是這樣一個群體。一方面,他們代表國家,替國家做事。在這一點上,最為突出的變現便是鄉紳協助地方官吏完成政務工作。而且,這種協助所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包括實征派、政策宣傳、治安、教化、鄉村經濟等諸多方面。甚至,他們還要充當官民矛盾的調節人。如清末時,華北泥井鎮屠戶拒絕交稅,由此屠戶與收稅人之間展開了持久的戰爭。當屠戶罷市,集上無肉之時,當地紳士便出面干涉,最后達成協議。與此同時,鄉紳還是鄉民的代表,代替鄉人同國家進行一定的博弈,以更切實有效地維護村民的共同利益。乾隆年間鄉紳郎秀才率民沖擊漠視鄉里災情的縣官即是一例。
(二)獻身地方公益
我國傳統社會的倫理教育以儒家思想為主要內容。因此,鄉紳作為一個接受過傳統教育并有著較高知識文化水平的群體,其必然性地會被儒家思想所影響。實質上,在他們的價值觀體系中,忠、孝、仁、義這些儒家思想的道德精華占據了重要的位置。再加上其相對優越的經濟條件,鄉紳必然性地在地方公益事業中發揮作用。關于這一點,有實在的例子可以明證。如明宣德年間,江西普遍出現饑荒,地方米價騰貴。官府曾考慮開倉平糶,然庫存有限,無法滿足四鄉的災黎。正當官府躊躇之際,地方鄉紳魯希恭、新淦及鄭宗魯各出粟二千石助賑濟,隨后又有眾多紳民獻捐,暫緩了饑民的乏食之困。當然,鄉紳們的公益舉動遠不止于此。實質上,除了上述民間賑災外,在基層社會的修橋鋪路、疏浚河道、修堤筑圍等活動中均可以看見他們的身影。
(三)振興地域文化
鄉紳是農村社區里有知識、有文化的群體。因此,在那個以文盲為主體的年代,他們必然性地在村級事務中的文化陣地上發揮作用。首先,他們在鄉村興辦學校書院,以興教化。對此,有相關的歷史記載:鄒守益,退職家居,鄒守益,退職家居,以講學善俗為事。“知教之不可不豫也,則立書院、建祠、廣鄉約,以浚其源;知弊之不可不革也,則舉清量、明戶役,以正其始。其他如賑貸周族、睦鄰施義、繕道橋、廣陂堰,不一而宇”[7];其次,鄉紳們還參與族譜、鄉規民約及地方志的編寫。如《柳亭山真應廟方氏會宗統譜.凡例》中就記載了編撰人員名單。根據此記載,參加編撰班子的共計70人,其中有功名的族人就占了23名,占三分之一。其他無功名者也都是讀書人。可見,編撰族譜及鄉規民約的權力實質上是掌握在知識精英,尤其是鄉紳手中。最后,鄉紳還通過講會來控制地方。對此,也有相關的史料可以證明。如“時陽明先生良知之學方倡,諸先生因佃以為萃和書院。月朔望,講學其中。切磋之余,民間有難申之隱,則就是告理。豪強亦為之斂手,亦治化之一助也”[8]。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鄉紳都能伸張正義、扶危濟困。實質上,也有不少的鄉紳憑借自身的優勢地位,橫行鄉里,魚肉百姓。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在國家財力有限、國家權力無法直接進入鄉村的年代,正是在鄉紳的介入與配合下,宗族組織才能形成較為全面的宗族法規以調控鄉民的行為及糾紛,國家的制度、政策、及意識形態也才能在閉塞、偏僻的鄉村得到宣傳、接受,原本處于隔絕狀態的國家與鄉村也才有了連接的機會與能力。正是在鄉紳的作用下,我國封建社會的農村保持了長久的穩定。
[1]亞里斯多德.政治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
[2]孫盛運.清代家譜匯編[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
[3]吳強華.家譜[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
[4][美]D.布迪,C.奠里斯.中華帝國的法律[M].朱勇,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5]劉宗棠.論清代宗族法規的文化內涵和社會功能[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6).
[6]環山余氏宗譜(木刻本)[O].民國六年,1917.
[7]羅洪先.明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致仕東廓鄒公墓志銘[M].念庵文集:卷十五.
[8]劉岵.寺院記.同治泰和縣志:卷9(書院志)[Z].
D69
A
1007-9882(2012)04-0013-04
2012-06-28
李雪彥(1981-),女,云南大理人,法學碩士,安順學院政法系副教授,從事政治學研究。
[責任編輯:陳如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