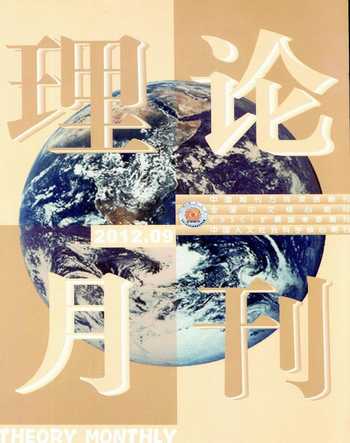試論波朗查斯的國家職能理論
陶歡英 江紅義
摘要: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波朗查斯站在結構主義的立場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進行了結構主義闡釋,對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職能作出了頗有見地的分析。他認為國家是階級關系的凝聚,因此國家具有維持與破壞兩種職能,其中國家的維持職能實質上是一種綜合調和職能。波朗查斯的國家職能理論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價值。
關鍵詞:波朗查斯;結構主義;國家職能
中圖分類號:D031(56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0544(2012)09-0039-03
一、結構主義政治學
波朗查斯的結構主義政治學主要圍繞著以下三個問題展開的。
(一)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
結構主義的本質和首要原則在于對整體性的強調,認為整體對于部分來說具有邏輯上的優先重要性,因為任何事物都是一個復雜的統一整體,其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個整體的關系網絡中,即把它與其它部分聯系起來才能被理解。所以,結構主義堅持只有通過存在于部分之間的關系才能適當地解釋整體和部分,并以此為基礎強調深層結構。具體到社會生活而言,結構主義明確指出,社會生活是由經濟、技術、政治、法律、倫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構成的一個有意義的復雜整體,其中某一因素除非與其它因素聯系起來考慮,否則便不能得到理解。
波朗查斯對于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關系的探討是其結構主義政治學的邏輯起點。波朗查斯指出,根據結構主義。生產方式所指的并非一般列為經濟方面的嚴格意義上的生產關系,而是指包括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理論等屬于這種方式的環節和實踐的特殊結合。這些環節之間的關系不是一種直線性的因果關系,而是一種這樣的關系,即在其中居統治地位的經濟環節對其他環節起著控制作用,使這些環節各得其所和各盡其職。至于如何理解經濟環節最后的統治作用,波朗查斯進一步論述道,“整個結構歸根到底決定于經濟這個事實,并不意味著經濟在這個結構中總是起著統治作用。由占統治地位的結構構成的統一體意味著每種生產方式都有一個占統治地位的方面或環節;但事實上經濟之所以起著決定性作用,是因為經濟讓每一個環節起統治作用,而由經濟掌握著起決定作用的環節的轉換,這種轉換是由于各個環節分散活動的結果”。
波朗查斯同時指出,生產方式構成一個抽象形式的事物,嚴格而言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實際存在的唯一事物是由歷史決定的社會形態。一種社會形態是在一定歷史時期所存在的一個復雜的社會整體。這個社會整體由若干“純粹”生產方式結合而成。其中有一種生產方式居于統治地位。
(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
波朗查斯以結構主義方法分析了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之間的關系后指出,他對于政治方面的研究著重于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居于統治地位的國家的政治上層建筑。其所依據的理論就是結構主義的共時性原則。結構主義認為共時性是同時要素間的關系,是整體性的必然延伸。
根據共時性原則,波朗查斯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是對不同但又統一的各個環節(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等方面)間關系的一般形式提出解釋。但是只有把政治方面的部門理論用來研究一個特定生產方式課題。才能得出更加豐富的結論。“因此,政治科學課題的概念的形成,從最貧乏的理論推斷提高到最豐富的理論推斷。首先要求嚴格限定把政治作為一種特定生產方式中的一個方面、部門和環節”。
波朗查斯認為,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中,指出了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經濟和政治方面聯結的特征是一種“混合關系”或“有機的”、“自然的”、“同時的”關系,其實際占有關系的特征是直接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統一。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里,則是經濟和政治這兩個環節特有的相對獨立自主性,這不僅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產過程以一種相對獨立自主的方式進行,而不需要“超經濟因素”的干預,而且表現為資本主義國家所發揮的作用具有自主性。
總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是經濟和政治環節的各自獨立性:這種獨立自主性是明確區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這些環節間的關系同其他生產方式保有的關系之間的基礎”。這種政治與經濟環節所具有的各自的自主性使得有可能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方面提出一個部門理論,例如提出有關資本主義國家的理論。
(三)政治實踐與國家政權
波朗查斯指出,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那里,政治與政治活動問題是與歷史問題聯系在一起的。于是,政治領域就不是一種特殊的結構和專門的實踐,而是包括屬于一種社會形態的結構和實踐的每一個方面的動態或歷時的面貌。這樣。對馬克思主義就會作出以下理解:其一是把政治活動與歷史相等同:其二是把屬于一種社會形態的各種結構和實踐的不同方面過分政治化;其三是否定政治本身的特殊性,不加區別地將政治列入其它各種因素之中,由此打破了一種社會形態中各種因素之間關系的平衡。基于上述原因。“使得政治和政治實踐結構的理論研究瑣碎化,從而導致意識形態上一成不變的唯意志論或經濟主義。并產生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改良主義和自發論,等等”。
二、關于國家職能的基本觀點
波朗查斯的國家理論是其結構主義政治學的基本內容。其中關于國家職能的基本觀點是理解結構主義國家理論的關鍵所在。波朗查斯的國家職能理論主要有以下觀點。
(一)國家是階級關系的凝聚
波朗查斯對于國家的理解集中于國家職能上,認為“國家的特殊職能就是要成為一種社會形態各個方面調和的因素。這正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概念的原意,即國家是一種社會形態的‘秩序或‘組織原則:但這并不是指現代意義的政治秩序,而是就它能夠起著一個復雜的統一體所有各個方面調和的意義而言,并且是作為調節這個體系綜合平衡的因素而言”。波朗查斯在《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階級》中,更是明確指出國家不是擁有內在的工具性質的實體,它本身就是一種關系,更準確地說,是一種集中起來的階級關系。在他生前最后一部著作《國家、權力與社會主義》中。他也同樣認為:“不應把國家看作是像資本那樣的一個固有的實體,倒不如說,它是各種權力之間的一種關系,或者更精確些說,它是階級和階級派別之間的關系的物質凝聚,以一種特別的形式表現在國家之中”。
波朗查斯指出,只有把國家看成是一種關系,才可以既避免把國家看作是一種工具,也避免把國家看作是一種絕對的主體。國家既非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是統治階級的工具,也非黑格爾所言的“是絕對自在自為的理性東西”。工具論與主體論的國家觀都把國家與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割裂開來。國家與階級的關系變成了一種外在的關系,“國家只是外在地與社會階級相關聯,因而自然地表現為一個沒有任何分歧的鐵板一塊的集團”。這兩種國家觀都無法理解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國家政策是怎樣確定的,都不能抓住國家內部矛盾這個決定性的問題。只有把國家看成是一種關系,是階級關系的凝聚,才能理解國家政策的制定,即“國家政策的制訂必須被看作是內在于國家結構中的階級矛盾的產物”,“也就是階級矛盾在國家中作用的結果”。可見,國家政策既不是統治階級簡單地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國家這個工具的結果,也不是國家本身絕對自主的權力產生出來的結果,而是內在于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結果。
(二)國家的兩種職能
只有在這一意義上理解國家,才能理解政治實踐所具有的兩種作用:一是維持一個社會形態在一定時期或階段的統一,因為“這種平衡從來不是由經濟因素帶來的。而是由國家來維持的。……政治實踐的目的就是把國家作為維持這種統一的調和因素”;二是國家以破壞統一的方式來產生一種新的統一。正因為如此,國家既是調和一個社會形態的統一的因素,也是這個形態各個方面矛盾集中在一起的結構。于是,我們才能以此說明政治與歷史之間的關系問題,即政治結構既是一個社會形態的特殊方面,又是其發生轉變的場所:它表明作為歷史動力的政治斗爭的目的在于國家,而集中各個環節之間矛盾的場所也正是國家。
政治實踐的兩種作用也就是國家的兩種職能。當國家的維持與調和職能成為一種專門職能時,“說明國家正處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這種形態中、由于各個環節的特殊獨立性以及由于國家所在地區的特殊地位而決定了這種特征。這種特有的獨立性是政治特征的基礎:它決定了國家作為具有獨立性的各個方面調和因素的特殊職能”。也正是因為國家具有維持與調和職能,使得國家成為各個環節矛盾集中起來的場所,尤其是“當我們考慮由歷史決定的社會形態的特征是由交迭在一起的幾種生產方式所規定的時候,這種職能就變得更加清楚一些”。國家的維持調和職能存在于各種生產方式交迭在一起的各種社會形態中,而在資本主義形態中這種職能顯得特別重要,“在這里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得當前的各種生產方式中都由資本主義結構占統治地位,特別是使得其各個環節都具有相對獨立性。這種獨立性帶來了由各種生產方式交迭導致的關系失調”。
因此,國家具有在政治階級沖突當中維持秩序的職能,同時也是作為統一的調和因素而維持全面秩序的職能。波朗查斯認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確實沒有從理論上精心制訂出國家的這種概念,但是我們在他們的著作中卻能找到無數痕跡”,如馬克思的國家是社會正式代表的觀點、恩格斯的國家是從社會中產生又居于社會之上并日益同社會相脫離的力量、布哈林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所闡述的社會形態是一種不平衡的體系、國家起著調節作用等。
(三)國家的綜合調和職能
國家維持秩序的職能具有多種具體形式,如經濟職能、政治職能、意識形態職能等。其中經濟職能與意識形態職能受到國家政治職能的多元決定影響,這是因為國家是政治上階級統治的場所。波朗查斯同時指出,嚴格而言,國家的經濟職能、政治職能、意識形態職能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由國家所處地位而決定的綜合的調和職能,這種職能有多種形式,并通過特殊的政治形式而受到多元的決定影響”。這樣,國家在一種社會形態中的綜合調和職能是能夠與經濟職能、政治職能、意識形態職能相區別的,而且國家的各種職能,即使不直接涉及到政治方面,也只能從國家的綜合調和職能來理解。國家綜合調和職能的首要目的是維持一個社會形態的統一,歸根到底是以政治的階級統治為基礎的,因而也可以說是政治職能。“正是在這里我們可以證實國家的經濟和意識形態職能受到其政治職能的多元決定作用,即按嚴格意義而論是指在政治階級斗爭中的政治職能”。這些職能的最高目的在于維持社會形態的統一,這些職能是和統治階級的政治利益相適應的。換言之,國家的各種職能通過國家的綜括作用而構成政治職能以適應統治階級的政治利益。
三、主要結論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對波朗查斯的國家職能理論作出如下總結。
波朗查斯的國家理論告訴我們,任何社會形態都不可能僅僅存在某種單一的生產方式,而往往是由若干“純粹”生產方式結合而成。其中有一種生產方式居于統治地位。就人類歷史而言,無論是雇傭奴隸制生產方式居于支配地位的社會形態,分封制生產方式居于支配地位的社會形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居于支配地位的社會形態、都是由多種生產方式結合而成的。不同人群在生產方式中由于所處地位的不同而分化為不同的階級,因此由歷史所決定的社會形態往往是多階級階層并存。其所引發的社會形態中的各個不同方面的矛盾在政治環節相聚合,從而形成一種“當前時機”或“形勢”。基于維系這種“當前時機”或“形勢”的需要,作為政治實踐環節的國家也就應運而生。因此。國家是階級關系的聚合體,是一定社會形態內部各種矛盾的交匯點。
由于國家是階級關系的凝聚。是一定社會形態各個環節之間矛盾匯聚的場所。也就是政治實踐的場所,因此國家必然具有維持或破壞社會形態統一的職能。盡管波朗查斯認為當國家的維持職能成為一種專門職能時,表明國家處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形態中,但也表明任何社會形態中,只要因政治實踐的需要而產生了國家,就必然具有維持社會形態統一的職能。波朗查斯指出。國家可以通過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具體職能的行使來維持社會形態的統一,這些職能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多元決定的關系,但是這種關系最終受到政治職能的影響。因此國家的政治職能實質上就是國家的各種具體職能通過國家的綜合作用而構成的,就是一種綜合調和職能。質言之,國家綜合調和職能就是指國家這一階級關系的“凝聚體”運用綜合手段調和國家結構中各環節的矛盾。當國家能夠有效調和國家結構中各環節的矛盾時,國家就能夠有效維持社會形態的統一,從而使社會達到和諧狀態。反之,當國家未能有效調和國家結構中各環節的矛盾時,國家最終必將以破壞統一的方式來產生一種新的統一。
國家的調和職能以服務于統治階級的政治利益為依歸。波朗查斯區分了統治階級的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認為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通過生產方式的運行得以實現,但是資本主義國家并不直接服務于分裂為各個利益派別的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而是通過綜合調和職能的行使維持社會形態的統一以服務于統治階級的總體的政治利益。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政治利益,要求國家必須具有相對于統治階級的自主性,從而實施相對靈活的政策,甚至可能限制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而換取被統治階級對現存國家的支持。因此。國家的綜合調和職能歸根到底是維持統治階級所需要的那種社會形態的統一,并非一種中立的職能。國家的這種職能表明國家不是一種完全被動的工具。也不是一種絕對的主體。國家具有相對自主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特定社會形態的走向。
總之,波朗查斯站在結構主義的立場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進行了結構主義闡釋,對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職能作出了頗有見地的分析,提出了許多獨具特色的觀點。當代中國正致力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國家正確行使其職能。盡管我國的社會性質與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本質區別,但改革開放以來逐步形成了公有制生產方式與非公有制生產方式并存的格局。據統計。1978-1985年,在我國社會總資產中,公有制資產和非公有制資產所占的比重分別為94.1%和5.9%。到2006年,公有制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的比重下降到44.3%(其中國有經濟為32.0%,集體經濟為12.3%),非公有制資產所占的比重則上升到55.4%(其中私營經濟為33.0%,個體經濟為3.3%,外資經濟為19.1%)。到2010年,公有制資產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為34.0%。如果將聯營經濟、有限責任公司的公有制資產按1/3折算約為8%,2010年公有制資產也只占42.0%(其中國有經濟為37.96%,集體經濟為4.04%)。多種生產方式并存必然導致在我國形成一種多階級階層并存的格局,國家也就成為一個多階級階層的聚合體,因此波朗查斯的國家職能理論對于當代中國而言也就具有一定的時代價值。
責任編輯劉宏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