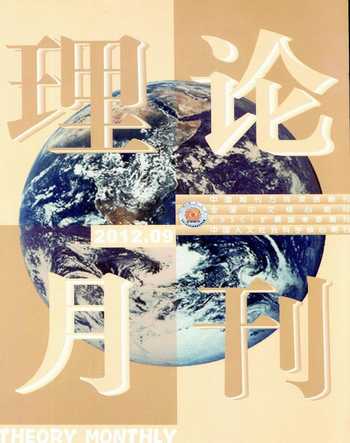從“親屬容隱”談窩藏、包庇罪主體的立法完善
張娟
摘要:容隱原則在不同社會制度的法律中都存在,我國新刑事訴訟法規定了被告人的近親屬有拒絕出庭作證的權利,體現了情與法的交融。從人性的角度來說,親屬之間互相窩藏、包庇的行為是出于親情的一種本能反應。要求親屬不窩藏、包庇犯罪的親人,期待可能性極低。實體法與程序法在理念上應當具有統一性,因此有必要相應修改刑法中關于親屬作為窩藏、包庇罪主體的規定。
關鍵詞:親屬;容隱;窩藏;包庇
中圖分類號:D92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0544(2012)09-0125-04
一、“親屬容隱”在我國的發展及西方立法例
“容”即容許、允許,“隱”即隱瞞、隱匿。“親屬容隱”又稱為“親親得相首匿”、“親親相隱”、“親親相為隱”,其基本含義可以理解為:法律在一定條件下允許一定范圍內的親屬之間相互隱匿犯罪行為不予告發或作證,而不予處罰或者減輕處罰。
(一)我國“親屬容隱”原則的發展
容隱原則萌芽于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發展于秦漢,至唐朝達到頂峰。《論語·子路》中記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攮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躬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也。”父慈而為子隱,子孝而為父隱,親屬容隱的正當性體現在其所包含的倫理價值當中。
儒家思想在漢朝被定為“獨尊”之后。親屬容隱的理念發展成為漢律中一項重要的法律原則——“親親得相首匿”——指在直系三代血親之間和夫妻之間,除犯謀反、大逆外,均可互相隱匿犯罪行為,而且減免刑罰。根據這一原則,卑幼隱匿有罪尊長,不負刑事責任;尊長隱匿卑幼,除死罪要上請廷尉決定是否減免外,其它也不追究刑事責任。
唐律在容隱制度方面形成了一個完備的規范系統。《唐律·名例律》總第46條規定:“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摘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所謂“同居”,疏曰:“謂同財而居,不限籍之同異,雖無服者,并是。”可見,在唐律中。除了允許親屬對本家犯罪者實行“親親相隱”的原則,對“同居”者的相隱行為也不追究隱瞞者的刑事責任。
經歷了清末修律的沖擊后,親屬容隱原則在民國時期的刑法仍然得以保留。南京國民政府1928年的《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親屬圖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而犯本章之罪者,免除其刑。”1935年的《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條規定:“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圖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而犯第一百六十四條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我國臺灣地區現行刑法典一《中華民國刑法》(2010年修訂)沿用了1935年的規定。
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期里,“大義滅親”被作為一種新型道德而鼓勵。親人間相互揭發、檢舉的“大義滅親”被視為革命行為加以推崇。1979年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在制定時,沿用了這種法治理念。本來,《刑法草案》在第22稿規定了:“直系血親、配偶或者在一個家庭過共同生活的親屬,犯第一款罪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所述“第一款罪”即:窩藏、包庇反革命分子以外的一般犯罪分子。但后來在討論中認為,“這款規定,還有點容忍封建社會提倡的‘親屬容隱、‘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那種倫理道德的味道,有提倡封建殘余之嫌。”因此第33稿把這款刪去。1997年刑法修訂時,延續了1979年刑法典的態度,仍將窩藏、包庇罪的主體規定為一般主體,即包括了親屬這一特定群體。2012年3月,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取消了近親屬當庭指控的義務,在第188條規定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享有拒絕出庭作證的權利,這個進步體現了立法者以人為本的理念。
(二)西方關于“親屬容隱”的立法例
“親屬容隱”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并不是中國古代特有的做法,在西方也是源遠流長。古希臘的法律思想中已經有了“容隱”的觀念。對于游敘佛倫起訴自己的父親殺人,蘇格拉底認為:“竟然膽敢告你父殺人,不怕自己做了慢神的事?”游敘佛倫自己也說:“現在我父親和家人都怨我”,“為子者訟殺人是慢神的事”。及至近現代,西方國家將“親屬容隱”的理念納入了刑事立法之中,在實體法上對于幫助、隱匿親屬犯罪的行為免除或減輕處罰,“親屬相為隱的規定幾乎可普遍見于世界各國刑法典;”在程序法中還規定了親屬的“拒絕作證權”。
《意大利刑法典》第307條“為參加預謀或武裝團伙的人提供協助罪”第3款規定,為幫助自己的近親屬而實施“提供藏身地、食宿、招待、交通工具或通訊器材的”,不予處罰。《德國刑法典》第21章規定了“包庇與窩贓”,第258條“阻撓刑罰”第6項規定:“為使親屬免于刑罰處罰而為上述行為的,不處罰。”《法國刑法典》第434-6條第2款規定,下列之人所實施的窩藏、包庇行為不受刑罰處罰:1.重罪之正犯或共犯的直系親屬、兄弟姐妹以及這些人的配偶;2.重罪之正犯或共犯的配偶或者眾所周知同其姘居生活的人”。《日本刑法典》第103條、第104條分別規定“藏匿犯人罪”和“隱滅證據罪”,第105條(有關親屬犯罪的特例)規定:“犯人或者脫逃人的親屬,為了犯人或者脫逃人的利益而犯前兩條之罪的,可以免除刑罰。”《俄羅斯刑法典》第316條是關于包庇犯罪的規定,該條末尾附注規定:“包庇配偶或近親屬所實施的犯罪而非事先許諾的,不負刑事責任。”其他的還有奧地利、西班牙、瑞士、挪威、芬蘭、荷蘭、巴西、阿根廷、韓國、新加坡、泰國、印度等國家的刑法典中都對親屬間的窩藏、包庇行為作出了免于處罰或從寬處罰的規定。
在程序法方面,很多國家和地區還在刑事訴訟法中也規定了親屬的“拒絕作證權”,如美國、英國、意大利、法國、德國、日本、我國臺灣地區、香港地區等。《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501條規定了七種免征特權,其中就包括“不作對配偶不利的證言的特權”、“維護夫妻關系信任的特權”。法國的《刑事訴訟法》第335條規定下列親屬的證言不得經宣誓接受之:即,(1)被告人或在場并接受同一庭審的被告人之一父親母親或其他任何直系尊血系,(2)子女或其他任何直系卑血系,(3)兄弟姐妹,(4)同親等的姻系,(5)夫或妻,對已離婚的夫婦也適用。盡管在不同的國家或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在容隱的主體范圍、適用條件等方面的確存在區別,但不論在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親屬容隱的內在價值是得到普遍承認的。親屬容隱的原則之所以能成為不同民族、國家的共識,是因為它體現了人性對于親情的需求,體現了對倫理道德的尊重,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
二、我國現行立法中親屬作為窩藏、包庇罪主體之檢討
現行立法中關于親屬作為窩藏、包庇罪主體的規定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缺乏期待可能性
美國學者羅爾斯說:“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為應該是人們合理地被期望去做或不做的行為。”這也正是“法律不強人所難”這一古老的法律格言所要求的。“法律不強人所難”的格言上升為刑法理論,便是期待可能性理論。圊自1897年德國帝國法院“癖馬案”的判決以來,該理論在大陸法系中迅速確立了其責任判斷中的重要地位,旨在于為行為人在特定情況下所實施的違法行為尋找阻卻責任的理由。
盡管期待可能性理論對我國而言是個舶來品,但從本質上來看,“親屬容隱”符合期待可能性思想,而“大義滅親”則是缺乏期待可能性的。誠然,親屬之間確實可以選擇揭發、指證犯罪人,可以選擇大義滅親,但這似乎是道德的至高境界,正因如此,包青天大義滅親鍘侄兒的故事才會成為千古流傳的佳話。但是法律畢竟是適用于全社會的規范,當然不能以圣人、英雄的道德水平為標準,就一般人性而言,要求人們在親屬犯罪后,不偽造證據、不隱匿、主動告發,顯然勉為其難。顯然,我國現行立法中要求親屬不為窩藏、包庇行為的規定缺乏期待可能性。
(二)難以實現個案正義
根據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窩藏、包庇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而在實踐中,窩藏、包庇被告人最多的便是其親屬,和親屬窩藏、包庇行為相對的是“大義滅親”。盡管法律規定對“大義滅親”的行為持鼓勵態度,但相關的個案卻無法得到公眾輿論的認同。雖然“大義滅親”行為有助于早日抓獲罪犯、提高破案效率、降低訴訟成本,但其同時也割裂了血緣親情、忽視了倫理關系有違親屬容隱的原則。如有的學者所說的,從法律自身與其所處環境來分析法律秩序未能形成之原,的確能夠帶給我們種種有益的啟示。然而,如若忽略秩序中人的因素,很難真正把握住問題的核心。
此前曾有過這樣的案例:弟弟為了籌集哥哥上大學的費用而偷竊了室友4萬元。在警方的動員下,哥哥將弟弟騙到自己的住處,埋伏在那里的警察將其抓獲。哥哥的大義滅親之舉受到了社會的強烈譴責。歌手滿文軍作證稱妻子組織吸毒的事件也曾一度引發社會對“大義滅親”的爭論,社會大眾的感情似乎更傾向于“親屬容隱”這種傳統理念。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究竟能期待多少人去完成“大義滅親”以實現個案正義?
(三)不利于法律文化的培育
德國學者耶塞克認為,“建立和實施法治屬于國家的重要任務,其原因在于沒有法治,人類就不可能和諧地共同生活。”刑法規范的背后,總是會蘊含著一種文化。只有講求人倫的社會,才能真正形成樂于為善、恥于為惡的人文氛圍。
窩藏、包庇行為或許的確會在客觀上對司法機關的偵查和抓捕造成一定的阻礙,但從人性角度來說,親屬之間互相窩藏、包庇的行為是出于親情的一種本能反應,例如“曹云凱等故意殺人、窩藏案”中的父母收留兒子同住,“婁光澤等綁架、搶劫、窩藏案”中的妻子陪同犯罪的丈夫逃跑。在立法上將這種“本能”一律作為犯罪,與其他主體一樣進行處罰。完全忽視了親屬的特殊性,摒棄了傳統的倫理文化心理,漠視了刑法的倫理文化功能。2012年5月的一則新聞在社會上引發了熱議,一個12歲孩子的家長涉嫌詐騙外逃,警察向其所在學校提出要詢問孩子,以獲得犯罪嫌疑人的最新動向。校長拒絕了警方。理由是“學校不鼓勵孩子揭發自己的父母、撕裂親情,這是一種違反人性的做法”。“最牛校長”的美譽不脛而走。當一個制度需要人們打破根深蒂固的或者來自本能的選擇傾向時,它就有可能不斷的被人們違反。這樣反倒可能使社會公眾對行為人產生同情,從而造成刑法尊嚴和威信的喪失,不利于法律文化的培育。
三、窩藏、包庇罪親屬主體的完善
(一)在窩藏、包庇罪中適用親屬容隱原則的可行性
我國目前的立法以及司法上,實際上已經對親屬的特殊身份有所考慮。
1.親屬相犯從寬處理的司法解釋。以親屬間的盜竊行為為例,司法解釋中明確規定,對于家庭成員及親屬間盜竊行為一般可不按犯罪處理,確有追究刑事責任的必要的,在處理時也是有別于一般盜竊案的。例如1985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要把偷竊自己家里或近親屬的同在社會上作案的加以區別>如何理解和處理的請示報告》、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2006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條中進一步規定:“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盜竊自己家庭或者近親屬財物,或者盜竊其他親屬財物但其他親屬要求不予追究的,可不按犯罪處理。”發生于親屬間的搶劫行為也有類似的司法解釋,對于以暴力、脅迫等手段取得家庭成員或近親屬財產的,一般不以搶劫罪定罪處罰,例如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這些司法解釋都表明了我國刑法是注重人性化的,是尊重親情的。因而,在窩藏、包庇罪的主體上適用親屬容隱原則是有現實基礎的。
2.新刑事訴訟法關于親屬拒絕出庭作證的規定。盡管新《刑事訴訟法》在第60條“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的規定表明我國親屬沒有拒證權,但其在第188條規定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享有拒絕出庭作證的權利。2011年8月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中擬規定“除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親屬有拒絕作證的權利。”雖然由于諸多原因本條關于親屬拒證權規定在修正案中未能通過,但是從中可以看出立法者“以人為本”的立法理念,考慮了人最基本的情感,體現了法與情的交融,這是社會的進步。可以說,“親屬拒絕當庭指控”是“親屬容隱”理念在刑事訴訟法上的體現,刑事實體法在價值目標上應當與程序法具有統一性,因此,相應地修改刑事實體法中關于親屬作為窩藏、包庇罪主體的立法規定也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3.司法實務中對被告人親屬協助偵破案件的司法政策。除了現行的立法,司法實務中的一些政策也是考慮到親情倫理而制定的。例如在2010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就有類似的規定。該規定36條第3款明確將“被告人的近親屬是否協助抓獲被告人”作為量刑情節。2010年9月29日河北省高院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中更是將此進一步量化:“被告人親屬舉報被告人犯罪,提供被告人隱匿地點或帶領司法人員抓獲被告人,以及有其他協助司法機關偵破案件、抓獲被告人情形的,可以酌情減少被告人基準刑的20%以下。”在量刑中納入親屬的立功行為,是“鼓勵揭發”,而之所以要對親屬的行為進行鼓勵,正是考慮到親屬對犯罪行為人的親情。對親屬的揭發進行鼓勵與賦予親屬拒絕作證的權利并不沖突,這些政策里都體現出了對親屬之情的理解和人性的考慮。
(二)立法設計
縱觀今日的世界各國,在窩藏、包庇罪中適用容隱原則的不乏其例;親屬容隱在我國也是歷史悠久,至秦漢到民國歷經兩千年。親屬相隱原則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既是古典的,也是現代的。今天的社會實在沒有理由將這樣一項具有相當深厚的社會人倫基礎的法律原則草率歸為封建殘余而予以拋棄。因此,為體現刑法對人性的理解和保護,有必要將親屬容隱原則適用于窩藏、包庇罪的規定中,在打擊犯罪的同時,滿足人們對親情倫理的需要。
但筆者并不主張將親屬容隱作為阻卻犯罪的事由完全排除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正如陳興良教授說的:“如果對于親屬犯罪予以庇護者一律定罪處罰,恐怕不太符合當前社會的倫理道德。因此,對于同居相隱不為罪的原則在總體上我們雖然應予否定,但對于刑罰適用中的倫理因素不能不加以考慮。”從親屬容隱和期待可能性理論的角度,結合我國的司法現實,借鑒目前其它國家的立法例,筆者建議:在原法條的基礎之上,窩藏、包庇罪還應增加第三款規定:“犯罪的人的近親屬犯第一款罪的,可以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但是,犯罪的人所犯罪行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國防利益的除外。”因此,《刑法》第310條可以修改為:
“明知是犯罪的人而為其提供隱藏處所、財物,幫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證明包庇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款罪,事前同謀的,以共同犯罪論處。
“犯罪的人的近親屬犯第一款罪的,可以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但是,犯罪的人所犯罪行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國防利益的除外。”
1.親屬范圍的界定。關于適用親屬相隱制度的親屬范圍,各國規定各異。如美、英兩國僅限于配偶,日本刑法規定為配偶、直系親屬、同居的親屬及其配偶,筆者認為,應將“親屬”范圍限定為“近親屬”。
至于哪些親屬是近親屬,我國各部門法的規定不同。例如:新《刑事訴訟法》第106條第(六)項規定:“近親屬”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民法通則意見》第12條規定,民法通則中規定的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1條第一款規定:行政訴訟法第24條規定的“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和其他具有扶養、贍養關系的親屬。而我國的臺灣地區則規定為較廣泛的配偶、五代以內血親和三代以內姻親。
而學者間也有不同的意見:有的主張采用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將近親屬界定為“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有的學者則認為應“將適用親親相隱制度的對象限定為配偶、直系親屬、同居的親屬及其配偶。”也有學者認為“應限定在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外)祖父母及(外)孫子女和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喪偶兒媳與喪偶女婿以及同居的親屬范圍之類。”還有的學者甚至主張“對直系血親、配偶或者在一個家庭共同生活的成員都適用從寬規定”。借鑒各國立法中對容隱親屬范圍的具體規定,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考慮到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在親屬范圍上保持一致性,可以更好地保持法律體系的完整,筆者認為我國刑法中容隱親屬應當與《刑事訴訟法》第106條第(六)項規定的“犯罪的人”的近親屬范圍一致。因而,窩藏、包庇罪立法設計中所指的“近親屬”是“犯罪的人”的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2.從寬量刑情節。根據期待可能性理論,期待可能性是排除責任事由。在日本,期待可能性甚至是超法規的責任阻卻事由。我國有學者認為“宜以行為人缺乏期待可能性為由宣告無罪。”還有學者以中立的幫助行為理論為根據,認為“對于親屬之間的日常生活行為,即使客觀上對于親屬犯罪后的逃匿起了促進作用,但只要沒有超出社會相當性的范圍。就可以認為沒有達到可罰的違法性的程度,從而不作為犯罪處理。”
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免除刑事責任可能一時難以實現,但減輕刑事責任是可能的。要求親屬不窩藏、包庇犯罪的親人,期待可能性極低,因而行為人的罪責極小,所以親屬雖然構成犯罪,但對于親屬應考慮免除處罰、從輕處罰或減輕處罰。借鑒各國立法中的具體量刑規定,筆者建議對親屬犯窩藏、包庇罪的“可以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可以”從寬而不是“應當”從寬。至于是否從寬,如何從寬則可由法官在審判過程中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靈活掌握,這樣具有較多主動性。
3.例外規定。不論是在中國古代還是其它國家的現行立法,親屬間的容隱都不是絕對的。一方面我們應當將親屬容隱原則的可取之處予以吸納,另一方面還應當結合時代和社會特點作出一定的限制。筆者認為,當親屬包庇如下罪行時不能給予從寬處罰,即犯罪的人所犯罪行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嚴重危害國防利益的。這三種類型的犯罪,由于關乎到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前途,關系到社會公眾的利益,其危害性極大,因而不能適用親屬容隱的原則。
責任編輯肖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