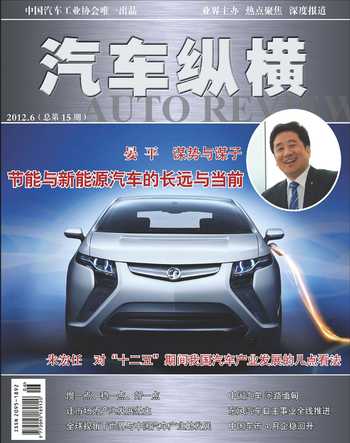讓市場為產業發展作主
賈翔 甄文媛

《規劃》指出,以純電驅動為汽車工業轉型的主要戰略取向,當前重點推進純電動汽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產業化,推廣普及非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節能內燃機汽車,提升我國汽車產業整體技術水平。
對于這種發展思路的調整,宋健卻認為:“這種變化太靈活,反而看不出有什么變化。”國家只是將非純電驅動和節能汽車的重要性“升了一級”,但鼓勵的重心仍在純電驅動上。宋健形成這種看法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家給混合動力汽車的微不足道的補貼無法刺激生產商做普通混合動力車的積極性。“沒有補貼力度,都是三千元人民幣,只當成節能汽車,我認為都是不合理的。”宋健表示。
據了解,節能汽車的節能率最多為六到七個百分點,而混合動力汽車卻可以高達50%。因此宋健建議,補貼一定要與合理的節能比率掛鉤才合適,比如三千元是5%,10%是否該六千,50%應該可以達到三萬。 而且,“將節能汽車按照節能率來補貼也是一種科學的方法。不管采用何種渠道或方式,低于國家油耗標準一定的百分比就應該可以得到優惠”。
“發展新能源汽車應當是多渠道、多途徑的,不應該只限制在某一方面或非此即彼。”宋健總結道,補貼的重點也不應該只側重某一方面,“產業發展需要的不是文字表述而是行動,比如三千與六萬,這兩個數字不在一個數量級上,這就是行動的差別。”
宋健還提出,制定的節能比率標準不能太寬松,而且檢測結果一定要來自社會上的抽檢。他希望國家能夠投資設立一個純事業單位性質的抽檢中心,不接受社會各方的資金來源,以保證補貼的發放公正有效。
此外,“國家在補貼時應當限制廠家的銷售價格”,宋健表示,目前國內電動車補貼后的價格依然較高,比如比亞迪有款電動車,補貼后尚賣二十萬,而原車(非電動版)僅六、七萬左右。近幾年來,在各國補貼等優惠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新能源汽車產業化進程加速。宋健則認為“最終能否投產主要由市場決定”。經過經濟基礎分析指出,成本的大幅下降往往由技術突破引起,“但目前為止看不出技術上的突破點,經濟上不可行,沒有性價比可言,除非補貼力度相當大,否則三五年之內產業化可能性不大。”
而實現產業化也必須重視對市場的培育。“有了市場,技術才能有價值,”宋健指出,“如果看不到市場,企業主動培育這一市場的積極性就沒有。只有靠政府補貼培育。有性價比才有吸引力,才會有方方面面的利益相關方介入。”比如純電動和插電式汽車需要在社區實現便捷充電,雖有很多人認為充電不貴,但如果在街道上大量建起充電樁則是另一番光景。在各種條件都滿足的情況下,停車場也會愿意建充電設施。
雖然市場的培育離不開政府補貼的支持,但如果技術沒有突破,最終政府也會因為看不到市場前景而停止補貼。
技術突破最終還是為大幅降低成本,利于新能源汽車的市場推廣。當前我國無論是政府階層還是業內人士,都格外強調要掌握新能源汽車的關鍵技術。據宋健介紹,我國目前電機的發電效率、驅動效率比國外平均差五個百分點,電池充放電效率約差三個百分點。盡管與發達國家“有些差距,但差距不大”。在他眼中,根本的差距在于出發點是否“為節能”。“我認為,一些中國企業推動節能與新能源汽車不像是為了節能而做,而是為了做這件事而做,為了政府而做。”宋健認為,節能應當從整個社會角度和能源角度判斷其效果。據他介紹,燃油驅動的汽車和電驅動的汽車在燃油利用效率方面效果相當。但純電驅動的汽車還有兩個耗能之處:一是重量。在電池方面,純電動的汽車續航里程達到150公里最少要附加30%的重量;另一方面主要集中在空調應用方面。因此純電驅動的整體效果并不節能。
從資源角度看,宋健強調,同等功率的電機(包括驅動控制器)和傳統內燃機在成本上相差不少。做電機的材料,銅、稀土永磁材料都是地球上寶貴的資源。而做內燃機的材料,鐵、鋁等在地球上大量存在,“這種材料成本上的差別不可同日而語” 。宋健認為:“市場培育最終還是性價比問題,消費者會按照性價比做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