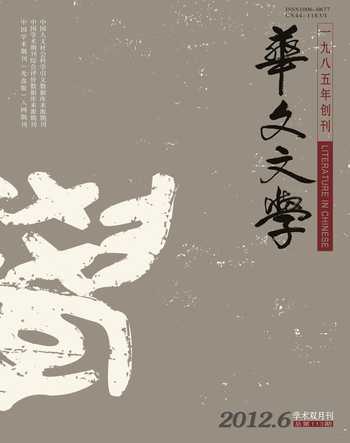從馬華“旅臺”文學到“在臺”馬華文學
摘 要:不同時期的臺灣文壇孕育出風格迥異的各世代馬華作家,其自我定位和國家意識也不盡相同。若從他們與臺灣文壇的關系來區分,可以劃分為“留臺”、“旅臺”、“在臺”等三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從馬華“旅臺”文學到“在臺”馬華文學的發展,擴大了版圖,增強了陣容,馬華作家群遂成為臺灣文學版圖內唯一的外來兵團。臺灣文學作品及其體制對馬華文學未來的發展勢必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馬華文學;旅臺;在臺;斷代;文學獎
中圖分類號:I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77(2012)6-0043-07
一、定義
臺灣的僑教政策實施了接近一甲子,其中無心插柳的重大成果之一,即是培育了龐大的馬華文學作家群。從1963年以馬華詩人為主干的星座詩社創立以來,至今整整半個世紀,不同時期的臺灣文壇孕育出風格迥異的各世代馬華作家,他們的自我定位和國家意識也不盡相同,若從他們與臺灣文壇的臍帶關系來區分,可以劃分為“留臺”、“旅臺”、“在臺”等三個截然不同的概念。
“留臺”單指曾經在臺灣留學,目前已離開回馬或到其它國家謀生的作家。這個陣容是非常龐大的,他們構成了馬華文學的創作主力。
“旅臺”只包括:目前在臺求學、就業、定居的寫作人口(雖然主要的作家和學者都定居或入籍臺灣),不含學成歸馬的“留臺”學生,也不含從未在臺居留(旅行不算)卻有文學著作在臺出版的馬華作家。從客觀層面看來,“旅臺”的意義著重于臺灣文學及文化語境對旅居的創作者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那是一個完整的教育體制與文學資源,在一定的時間長度中(大學四年或更久),從單純的文藝少年開始啟蒙-孕育-養成-茁壯其文學生命(間中或經由各大文學獎的洗禮而速成),直到在臺結集出書,終成臺灣文壇一份子的過程。從結果來看,這個過程并非單向的孕育,臺灣文學跟馬華旅臺作家之間產生了雙向滲透,旅臺作家以強烈的赤道風格回饋了臺灣文學,成為臺灣文學史當中唯一的外來創作群體。稱之為外來,一則是它絕非臺灣的土產,二則是創作主體對馬來西亞仍舊保持著不同程度的——包括實質或精神層面——歸屬與認同。
其實,對每一位旅臺作家而言,馬來西亞是有著不可取代的重要性,那是一片累積了童年和少年生活經驗的出生地,也是國籍與國家認同的發生地,十九年的人物事構成難以動搖的原鄉內容(從出生到高三畢業共十八年,接著再花九個月等候臺灣“教育部”的分發和開學),更成為日后創作的最為重要的鈾礦。那是旅臺作家的“(現實)生命原鄉”。其次,是作為“(中華)文化母體”的“唐山/中國”,這個無孔不入的文化符號在其成長經驗及大馬華人社會的知識系統中糾纏不清,甚至成為他們赴臺留學(來臺取經)的部分動力,雖然它在日后的創作行為中迅速萎縮,乃至無足輕重,但“中國”這個空洞的文化印記,往往成為陌生的讀者用來誤讀旅臺作家的刻板媒介。其三,即是最關鍵的文學核子實驗室——臺灣,要是缺少了臺灣階段的淬煉,旅臺作家的大馬鈾礦很難轉化成文學核武。嚴格來說,旅臺文學跟馬華本地文學只有血緣上的關系,極大部分的旅臺作家都是“臺灣制造”。他們的創作源泉,或來自中國古典文哲經典,或來自在臺灣出版的內地和臺港現代文學著作,以及各種翻譯書籍(所以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馬華旅臺文學也算是臺灣現代文學的一環,盡管他們關注的題材、文學視野、發聲的姿態有異于一般臺灣作家)。臺灣,正是大部分旅臺(和小部分留臺)作家正式取得作家身份的“(華文)文學母體”。
隨著時間的推移,旅臺作家群起了結構性變化,原本僅有留學身份的旅居者,在轉為教職之后即變成定居者,有半數入籍臺灣。但其自我定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歸屬于馬華,有的是“人在臺,心在馬”,有的是“臺馬雙棲”或“臺馬相融”,不管什么樣的情形下,幾位已經取得臺灣護照和身份證,或以居留證在臺工作的馬華作家,在其內心深處仍舊脫離不了馬華的原籍。從這個角度來看,“旅臺”仍舊是一個不變的事實。
變化的還有整個文學出版環境。“在臺”則是現階段馬華文學在臺灣發展的一個現象,它的存在依據有一部分來自“在臺得獎”,更大的一部分來自“在臺出版”。自1990年代旅臺作家群在臺灣各大文學獎迅速崛起,進而雄踞西馬華文副刊的版面之后,具有高度公信力和競爭力的臺灣文學獎,便成為馬華在地作家眼中的成名快捷方式,或朝圣之路,任何一項臺灣大獎的含金量都遠高于馬華的獎項。在臺得獎并獲得臺灣文壇認可的非留臺作家,首推黎紫書。其他零星得獎者,就沒有構成跟黎紫書相等的聲勢了。主要原因在于黎紫書透過小說集的在臺出版,很快展現了可觀的創作質量。
臺灣一直都是世界華文文學的出版中心,其出版業的規模雖然不及中國大陸,但臺灣作家在創作和出版方面擁有較大的自由度。當然,在臺出版的圖書不僅止于馬華文學,還包括大陸、香港及歐美華人作家的著作(包括重量級作品和爭議性作品),之所以未能形成“在臺大陸文學”、“在臺香港文學”、“在臺歐美文學”,其關鍵就在那些作家真正的創作位置不在臺灣。必須先有了“旅臺”作家成功建構出風格鮮明的“赤道形聲”,再加上其余“非旅臺”馬華作家在臺的出版成果,由此系連起來的馬華作家總體形象,方才構成“在臺馬華文學”的全部陣容。
“在臺”一詞,讓人很容易聯想到“美國在臺辦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簡稱AIT)。如果稱作“馬華在臺文學”,則以馬華為本位,意指馬華文學(留駐)在臺灣的一個創作部隊,跟AIT有點類似。若稱作“在臺馬華文學”,則以臺灣為本位,它屬于臺灣文學的一部分。兩者都成立,都是事實。
“馬華在臺作家”等同于“馬華旅臺作家”,是以人為依據的概念,只有真正住在臺灣的才算。
“馬華在臺文學”卻大于“馬華旅臺文學”,是以書為依據的概念,只要在臺灣出版、發表、得獎都算。
所以“在臺”的馬華文學很難討論,人多書雜,尤其近幾年在臺出版的書越來越多,質量逐漸失控,有些言情小說或軟性讀物也加入“在臺”陣容,導致這個名稱的含沙量越來越高。真正能夠維護這個品牌地位的,還是旅臺創作和研究。
唯有回到旅臺文學的內部,才會發現許多值得關注的現象和議題。
經過近五十年的在臺發展,旅臺文學逐步成為馬華文壇愛恨交織的一個關鍵詞,它甚至可以形容為一枚核武。它既產生過最富有活力和爆發力的文學團體,也多次引爆過影響深遠和具爭議性的話題,當然更少不了許多大幅提高馬華文學國際能見度的重量級得獎作品。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戰斗性格十分明顯的旅臺作家群,是一支讓馬華文壇產生莫大敵意的隊伍。其實,旅臺文學的人數不多,同時期活躍在臺、馬文壇上的名字,通常保持在個位數。
二、斷代
旅臺文學發展了五十年,雖然作家人數不多,但不同時期崛起的作家自然帶上屬于自己的時空烙印,為了廓清旅臺文學的發展形貌,故有必要進行代際的劃分。
文學史的時期劃分和代際劃分都是見仁見智的,不管怎么劃分都有爭議,沒有絕對權威或客觀的方法。關于旅臺的世代劃分,首先必須舍棄了粗糙的“年齡分代法”,從撰寫文學史角度來看,一位作家以其創作崛起文壇的時間點,比他的實際年齡更有意義。以作家的生理年齡來分代,是權宜性的行為,一如以往我們用“字輩”來劃分馬華文學的世代,勢必模糊掉很多關鍵性的問題。一個寫作人之所以被稱為或被認可為作家,跟年齡無關,唯一的憑借是其創作。沒有一部擲地有聲的書,他只不過是路人甲。所以一部文集的成書/出版年份,以及此書所表現出來的文學高度或影響力,在文學史上的意義絕對遠大于作者當年幾歲。作家的存在價值跟書脫離不了關系,甚至可以說:“書在人在”。不管是早慧成名,或大器晚成,“成”所依據的也是書的出版,著作的出版=作家的誕生。我們必須精準錨定其成名作的時間,才能精準鏈接到其它的層面,包括文壇的風潮,或時代語境等等。從這部書,再進一步扣合作家的生命歷程和創作歷程,會得到很多隱密的訊息。書,是最客觀、最合理的刻度。其次,是創作形態。無論是將結盟結社的一代人歸納在一塊,或是將藉文學獎舞臺崛起的一代人湊在一起,其實已經蘊含了那個時代的氛圍、他們所面對的挑戰,以及為了因應外在環境所采取的寫作策略。崛起時間及創作形態,是大原則所在。有關旅臺作家的代際劃分,當然會有很多爭議,沒有絕對完美的看法。我必須再度強調的是:根據旅臺作家“崛起臺灣文壇的坐標”作為代際劃分的第一優先憑借,經一書一獎或一事,被主流副刊和重要出版社接受發表/出版其創作,由無人聞問的“寫手”晉級為具有能見度的“作家”。創作成果即是坐標,這個時間點即是代際劃分的首要依據。
根據旅臺作家在臺灣文壇的崛起時間及創作形態來劃分,可區分為三代。
第一代,是詩人透過結社來發聲的一代,時間跨度是1963~1980年。
第一代的旅臺作家主要有:王潤華(1941-)、林綠(丁善雄,1941-)、陳慧樺(陳鵬翔,1942-)、淡瑩(1943-)、溫瑞安(1954-)、方娥真(1954-)六位詩人(前四人兼具學者身份)。從1950年代至1980年代,這三十年的臺灣詩壇非常流行結社,笠、現代詩、創世紀、藍星等詩社各據一方,年輕詩人要取得一席之地,除了加入各大詩社,只能自行聚眾結伙,才有機會打出自己的旗號,否則很快被淹沒。當時的馬華旅臺詩人群都選擇以結社方式來發聲,先后組織了星座詩社(1963~1969)和神州詩社(1976~1980,其前身“天狼星詩社——臺北分社”始于1974年,或可視為“前神州”時期),以及馬華成色較低的大地詩社(1972~1982)。真正重要是星座和神州詩社,大地詩社通常不納入馬華文學的討論。這些包含臺灣本地作家在內的詩社,連結在一起,便代表了1960及1970年代馬華旅臺文學的活動形態。他們的詩作入選了當時臺灣最具代表性的三部選集:張默、洛夫、痖弦編《七十年代詩選》(1967)、張漢良編《八十年代詩選》(1976)、痖弦編《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詩卷)》(1980),這是旅臺新詩的第一個黃金時期,雖然星座詩人與神州詩人之間有十二屆的學籍差距,但神州詩人在詩社活躍期間即完成創作風格上的熟成與定型(隨即中斷或長期休止了進展),而且他們都以詩人結社的形式崛起并活躍于臺灣文壇,所面對的社會文化語境相近,正好前后承接合為一代。這一代以星座創社的1963年為起點,以1980年的神州冤獄為終點。
第二代,是小說家從兩大報文學獎崛起的一代,時間跨度是1977~1987年。
第二代的旅臺作家主要有:商晚筠(1952~1995)、李永平(1947-)、潘雨桐(1937-)、張貴興(1956-)四人。商、李二人的創作生涯始于1970年代后期,跟神州詩社是重疊的,但前者獨立自主的創作心態、文學獎的成名路徑、赤道風格,以及風格煉成的速度跟后者截然不同,很難湊成一代。潘雨桐來臺雖早,但他的創作生涯太過晚成(遲至1981年才首次在臺得獎,七年后才結集出書),跟星座一伙擺在一起更顯怪異。故神州眾人宜以“詩社結伙”的形態往上提,跟星座合為一代,商等四人自成“小說獎崛起”的一代。從1977年商晚筠獲得《聯合報》短篇小說獎為起點,到1987年張貴興獲得《中國時報》中篇小說獎為止,短短十年間,商等四人共奪下12項次的兩大報小說獎,聲勢驚人,不但創造了旅臺小說的第一個黃金時期,也開拓了未來旅臺作家進軍臺灣文壇的主要路徑(商等四人的得獎紀錄自1987年之后,中斷了十年,遲至1998年才再戰江湖),這些帶有赤道風格的得獎作品,為馬華品牌的誕生累積了巨大的能量。
第二代旅臺作家有別于第一代之處,除了透過“結社發聲”與“個人得獎”的成名路徑/模式不同,兩者對馬來西亞現實鄉土的關照也是截然不同的。第一代的星座詩的現代主義創作道路,徹底將個人的文化背景和家國經驗完全消隱無蹤,全心全意埋首于純粹的創作素材當中(在選材上,一則以符合存在主義思想為優先,二則以可以翻新出奇的中國古典素材為考慮),馬來西亞原鄉事物經常被排除在外。星座詩人、神州詩人的浪漫主義創作,除了對古典文學素材或情境的高度移情,對馬華現實社會的問題雖有關系,但多半由激昂的情緒來驅動(馬華現實多半隱身背后成為行俠天下的悲憤力量來源之一),對馬華的現實社會概況或實質的文化地理樣貌,完全沒有著墨。總的來說,要在第一代旅臺作家的文章里讀出馬來西亞的形象與內容,如同緣木求魚。
真正把馬來西亞作為一個故事的舞臺或敘事的重心,并且在其創作文本中初步建構出獨樹一幟的“赤道形象”的,是第二代旅臺作家。以小說為創作主力的第二代旅臺作家,正好遇上1970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戰,鄉土小說創作亦躍居文壇的主流,旅臺眾人獨家擁有的馬來半島與婆羅洲的鄉土圖像,正是奇貨可居,很自然地植入創作當中。盡管他們服膺及運用的是現代主義技巧,但具有高度辨識性與陌異感的赤道人文風景,絕對是一道利器。從商晚筠以馬來西亞三大種族的文化差異糅合而成的華玲鎮,潘雨桐將雨林傳說與禁忌融入了自然寫作,李永平創造了吉陵鎮來淬煉最純正的中文,到張貴興在雨林與都市題材的擺蕩中開發出具有鄉野傳奇色彩的敘事才華,這是旅臺文學空前的成就。盡管李永平和張貴興的長篇巨作還要再等上十余年才面世,但此階段的磨練卻已透露出許多重要的訊息,包括雨林史詩的原始構想和筆法,包括眾多評論家糾纏不止的議題。從整體的創作成果來審視,其實它不止是旅臺,而是整個馬華小說的第一個黃金十年,完全覆蓋新詩和散文兩大文類。(李、張二人潛伏十年后,再奮起,結合第三代旅臺作家,創造另一個由三大文類并駕齊驅的黃金十年。馬華文學史最強勢的文學地景和品牌形象,遂大功告成)
第三代,是以三大文類從文學獎崛起,再轉型為學院派作家的一代,時間跨度是1986~2007年。
第三代旅臺作家最早浮上臺面的有四人:林幸謙(1963-)、黃錦樹(1967-)、陳大為(1969-)、鐘怡雯(1969-),后來又有張草(1971-)、辛金順(1963-)、滄海未知生(吳龍川,1967-)三人。這個“學者化的得獎世代”以1989年林幸謙奪得“中國時報”散文獎為起點,以吳龍川奪得“溫世仁武俠小說百萬大賞”的《找死拳法》(2007)正式面世為終點,所得獎項跨越了臺灣、香港、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五個地區,更涵蓋了散文、新詩、小說、科幻小說、武俠小說等五個不同的征稿文類。上述七人,除了張草在畢業后返回東馬行醫,其余六人為中文系學者,學者化的創作思維是在所難免的(尤其林、黃二人)。從文學獎舞臺崛起,然后投身學術研究工作的學院派作家,正是臺灣文壇近十余年來最明顯的兩棲化趨勢。
1989年,林幸謙以赤道色彩鮮明的《赤道在線》一文奪得“中國時報”散文獎之后,翌年黃錦樹也開始了以小說為主的得獎歷程,接著是陳大為的新詩和鐘怡雯的散文加入文學獎的征伐行列,全面掀開旅臺文學在三大文類的全方位得獎時期。十年下來,四人共贏得十一次兩大報文學獎,以及數十種其它公開性文學獎。他們的作品在前人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構筑起赤道形象,色彩鮮明且獨特的意象系統,龐大、沉重,且深具思考性的創作主題,再加上三大文類齊頭并進的態勢,“馬華旅臺文學”開始受到重視。就在1995年9月中旬的“聯合報”文學獎和10月上旬的“中國時報”文學獎公布之后不久(當年黃錦樹和陳大為共獲三項大獎),兩大報的閱讀版不約而同地在11月23日當天,同步推出兩個旅臺文學特輯:徐淑卿《鄉關何處:馬華在臺作家的遞嬗》(《中國時報·開卷周報》,1995-11-23)、楊錦郁《馬華文學新生代在臺灣》(《聯合報·讀書人周報》,1995-11-23),這是旅臺文學史無前例的大曝光,從此這一票人就被結集在馬華的旌旗之下,在大部分臺灣文人的視野中,他們代表了當代馬華文學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內容。
從風格上來看,林幸謙散文走的是大散文路線,那是一種在長篇大幅的敘述中,站在一個感傷的制高點,動用龐大且沉重的民族符號或象征,以激昂的口吻和手勢來展示一道國家級的巨大傷口。那里頭常常堆積著我們都很熟悉的中國傳統文化事物,雖然無比慷慨的宣言有時顯得大而無當,對問題的探勘顯得膚淺且刻板,但保證是憂國憂民的,有血有淚,還有很高的分貝,這是大散文的操作方向和原則。黃錦樹所進行的則是一條學術議題化的小說創作路線,他在將小說與評論熔鑄為一體的過程中,并沒有忘記“說故事”的重要性,以及形式技巧上的創意,所以黃錦樹的跨界融合呈現出十分多樣的形貌,而且富有敘事魅力。林幸謙的大散文沒有一個發聲的舞臺,他緊緊抱著幾個龐大的主題在隱喻的黃河上漂浮,黃錦樹的敘事十分立體、生動地根植在真實的膠林經驗之中,這一片膠林對故事(包辯證性的議題,或現象的批判)的承載能力,讓原本生硬的議題陳述,獲得充滿彈性的土壤。鐘怡雯則矗立了一座赤道散文的新形象,她將家國主題的探討自前人的高分貝批判路線中抽離,不再仰賴巨大的象征和符號,她企圖轉向一種更具體、更切身的追尋,透過感性與理性交融的筆調,完成生動的故事及其寓意。所以她筆下的馬來西亞社會是感性的,以個人家庭生活的小歷史取代了華社的大歷史,她在散文里建構了自己的世界,同時蘊藏著光明與黑暗的油棕園,所有血肉肌理都是觸感十足的。
旅臺作家到1990年代后期才算完成真正堅強的創作陣容,不但個人風格都已成熟,也出版了幾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進入2000年以后,先后擔任大學教職的林幸謙、黃錦樹、鐘怡雯、陳大為四人,跟所有旅臺前輩一樣先后退出了文學獎競爭的舞臺,得獎的大任交由仍就讀博士班的辛金順來接棒。2006年,吳龍川異軍突起,以《找死拳法》一舉奪下“第一屆溫世仁武俠小說百萬大賞”的首獎,驚動文壇,完成了第三代旅臺作家最后一塊拼圖。
其實1998年至2010年間,李永平和張貴興才真正展現出他們旺盛的創作力,一連拿下多項重要的年度書籍大獎,《群象》、《猴杯》、《大河盡頭》等重量級著作,進一步鞏固了馬華旅臺文學的赤道形象;自“中央研究院”退休后的李有成也重出江湖,展現了學者散文的新風貌。除了各世代的旅臺作家聯手出擊,馬華在地作家也加入戰局,馬華文學在臺灣文壇的聲勢,自然更上一層樓。
不過,三代旅臺文人的豐碩創作成果,更突顯了人材的嚴重斷層。無論從個人得獎還是書籍出版的質量來評定,后進作家始終成不了氣候。偶爾有幾個身影冒出:急于成名而在人行地下道免費發放自印詩集的寫手,在文學獎退色的年代只贏得一兩個獎項便消失的寫手,結束留學且離臺后才出版一本文集便斷炊的寫手。幾年內,第四代旅臺作家不會成形。
總的來說,文學獎對第二代和第三代旅臺作家的崛起,有決定性的影響。但兩代作家的主要差異是第三代作家的得獎不但跨越三大文類(連同科幻與武俠),他們的征戰范圍涵蓋了東亞和東南亞華文文壇,同時又在馬華文壇發動了幾波論戰,而且是文學創作與學術評論雙管齊下。所以必須劃分為兩個不同的世代。此外必須強調的是,旅臺并不是一個真實的群體(唯有“神州社”例外),它只是幾個各自為政的旅臺作家的歸類,他們對很多議題的看法、創作理念也不盡相同,沒有誰可以成為代言人。他們的創作都是自己的選擇,各自累積,最后被論者歸納出一個具體的成果。
三、近況
近十余年來的馬華文學在臺灣發展的實況,至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觀察:
(一)學術研究:自2000年民進黨執政以后,臺灣本土論述迅速成為研究的主流,并掌握了最重要的學術資源;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后,過去挫敗的經驗讓馬政府比任何一屆的執政者更著重于眼前的短程效應,永遠處于選舉狀態的執政思維,根本沒有余力開展出更大的格局,在學術研究方面當然也不會有建樹,反而陷溺于量化評比的泥淖當中。在缺乏資源和誘因的情況下,馬華文學在臺灣的研究不可能成大氣候。一般臺灣學者對海外華人社會的文化境況完全陌生,面對某些觸及族群或歷史文化議題的馬華文學作品時,不敢貿然動筆,所以近期發表的馬華研究論文始終圍繞在旅臺作家身上。增長幅度最快速的反而是碩士論文,幾乎每年都有以旅臺作家為題的碩士論文在年輕學者手中誕生。
不過,隨著旅臺學者數量的增加,一股旅臺評論力量儼然成形,從議題討論到文本詮釋,對整個馬華文學評論水平的提升,都有非常顯著的影響,在短短十余年間至少累積了130萬字的論文。這支由陳鵬翔、李有成、張錦忠、林建國、黃錦樹、鐘怡雯、陳大為、高嘉謙等人組成的學術團隊,已成為臺灣學界中的馬華研究主力,支撐著各種學術會議中的馬華論述。
臺灣年輕學者楊宗翰在《從神州人到馬華人》一文中,討論了馬華旅臺文學在臺灣文學史上的價值與意義,他站在臺灣學界的立場指出:“此刻人們更該清楚地認識到:旅臺詩人的‘臺灣經驗/創作也是文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該再讓他們在臺灣詩史里‘流亡了。文學史家除了要精讀文本,尚需努力思考他們的適切位置;而非藉‘臺灣大敘述尚未竣工、仍待補強此類理由,再度使這群旅臺作家成為被放逐者──若真是如此,逐漸成熟的新一代臺灣作家與史家,難保不會也把這類殘缺的史著一起放逐”(《赤道回聲》,第182頁)。當時沒有人知道撰述中的臺灣文學史會采取什么樣的態度/策略來處理馬華旅臺文學,所以楊宗翰才感到憂心。
2011年10月,陳芳明撰寫的《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2011)終于問世,作為臺灣文學史唯一的權威論述,此書以“馬華文學的中國性與臺灣性”為題,討論了神州詩社的溫瑞安和方娥真,以及李永平、張貴興、陳大為、鐘怡雯、黃錦樹七人(此節共十二頁,全書內文近八百頁)。陳芳明在書中表示:“在臺馬華作家所建立的文學藝術與文學論述,是不容忽視的重要聲音。這牽涉到馬華作家本身的文化認同,以及在臺灣文壇所據有的文化位置”(《臺灣新文學史》,第708頁),“他們建立起來的馬華文學論述,已經成為國內學術重鎮。他們的發言與研究,與臺灣社會現實緊扣在一起。縱然他們的立場是屬于邊緣聲音,而這樣的詬語無庸置疑也同時在建構臺灣性。具體而言,馬華文學及其論述如果從1980年代以后的歷史脈絡抽離,臺灣文學必然出現巨大的缺口”(《臺灣新文學史》,第720頁)。從陳芳明的論述中可以說明,馬華旅臺/在臺文學在臺灣文學史中的地位,已經受到肯定。
除了單一的文學史專著,我們也可以從更寬闊的角度來檢視一個大時代的文學(接受史)視野──由文學史專著、文學辭典、文學年鑒、年度選集、文學大系,乃至高中、高職及大專教科書。從閱讀人口的長期效率而言,國中及高中教科書是最重要的讀本,其次是各大學自行編選的國文課本,旅臺眾人當中,鐘怡雯的散文是被收錄篇次最多的一位,直接培育了她廣大的讀者群。在上述八大類書籍的編選成果當中,旅臺作家不但沒有缺席,他們還受邀主編了多部以臺灣現代文學為主的重要選集:《天下散文選Ⅰ,Ⅱ:1970~2010臺灣》、《天下散文選Ⅲ:1970~2010大陸及海外》、《天下小說選Ⅰ,Ⅱ:1970~2010世界中文小說》、《臺灣現代文學教程2:散文讀本》、《臺灣現代文學教程5:當代文學讀本》、《九十四年散文選》、《九歌一○○年散文選》、《原鄉人:族群的故事》,這些選集的平均銷售量都在一萬冊左右,廣受臺灣讀者的肯定。
(二)文學獎:原本是新人崛起的最佳擂臺,但臺灣的文學獎在近十年來泛濫成災,逐獎維生的年輕寫手越來越多,得獎作品的水平卻大幅滑落,得獎者的光芒也黯然失色,一獎成名天下知的時代一去不返,連中文系學生都不再關心各項大獎的得主。文壇的注意力一度轉移到一年一度的“十大好書榜”,后來“中央日報”和“聯合報”的十大好書評選也停辦了,只剩下“中國時報”還在苦撐,關注于此的讀者也不多了。書市,成為臺灣作家最后的逐鹿舞臺。不過臺灣的出版品,從1989年的6,802種,暴增到1999年的34,563種,到了2011年更高達42,586種(出版數據詳見:《ISBN全國新書信息網.書目數據庫/ISBN/CIP各年度統計》)。尤其BOD少量印刷技術成熟之后,新人出書十分容易,當然也更容易被書海淹沒。臺灣文壇的前景實在令人擔憂,新一代馬華新銳作家在各項大獎里往往只是曇花一現,很難取得立錐之地,更別說打出旗號。
事實上,在文學獎效應消失之初,第二、三代馬華旅臺作家已經轉向常態創作,維持了相當穩定的著作質量,偶有突破性的創作表現。遲遲無法成形的第四代,除了未能樹立鮮明的個人風格,生不逢時也是原因之一。高度網絡化的時代,個人部落格(博客)的書寫并沒有提升他們的文字技巧,大量的網絡語匯和習慣性語法的使用,反而模糊掉個人的敘事特色;五花八門的文學獎,更是嚴重稀釋了他們偶爾得到的一項大獎之光芒,況且他們得獎數量大幅下減,無法跟前兩代旅臺作家相提并論,就更難出頭了。
結語
從馬華“旅臺”文學到“在臺”馬華文學的發展,可說是擴大了版圖,也增強了陣容,再加上由旅臺作家組成的學術團隊,馬華作家群遂成為臺灣文學版圖內唯一的外來兵團,而且是創作與學術的兩棲部隊。進入學院體制內的馬華旅臺作家,借重臺灣學術資源先后編選了三部具有文學史架構的重要選集:《馬華散文史讀本1957~2007》(三卷本)、《馬華新詩史讀本1957~2007》,連同另一部臺馬合作編選的《回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1937~2007》,交織出馬華文學史的輪廓。這項成果很正面地響應了多年來馬華本地文壇對旅臺作家返回大馬的呼吁。
從更年輕的馬華七字輩(1970~1979年生)和八字輩(1980~1989年生)作家對臺灣文學經典的推崇與模仿,以及殘留在創作里的陰影,再加上他們對在臺得獎和出書的熱衷程度,可以斷定臺灣文學作品及其體制對馬華文學未來的發展,勢必產生更深遠的影響。表面上旅臺一脈看似后繼無人,但骨子里潛流著臺灣文學基因,以臺灣文學為精神糧食的“精神旅臺”作家群卻日益龐大。或者,可權稱為“遠距旅臺”——因為他們透過網絡進入臺灣文壇沃土的精神旅臺狀態,是現在進行式的。這支隱形的“遠距旅臺”隊伍,遠大于“在臺”量化后的陣容,會不會導致未來馬華文學在風格與特質演化上的危機,還很難說。
參引書目:
《ISBN全國新書信息網. 書目數據庫/ISBN/CIP各年度統計》,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main_ProcessMenuItems.php?PHPSESSID=q4mif7akia838etsq9ockistu0&Ptarget=30&Pact=ViewCharts&Pval=B40&Pfld=Ffile.
徐淑卿:《鄉關何處:馬華在臺作家的遞嬗》,《中國時報·開卷周報》(1995-11-23)
陳大為、鐘怡雯、胡金倫編:《赤道回聲》(臺北:萬卷樓,2003)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2011)
楊錦郁:《馬華文學新生代在臺灣》,《聯合報·讀書人周報》(1995-11-23)
(責任編輯:張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