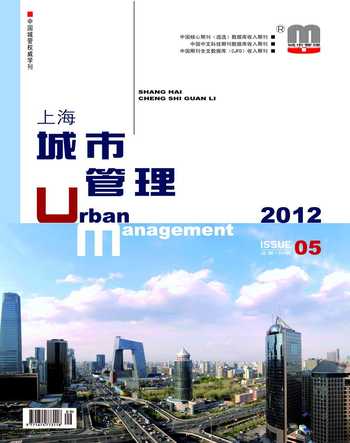中國城市文化安全的潛在危機與多元維護
徐翔
導讀:城市文化安全問題的提出,意味著城市文化建設和發展中文化自主性、自覺性、內生性的缺失,這關系到城市本土性安全、原生性安全、地方性安全、傳統性安全的文化危機和文化重塑。因此,對城市文化安全的維護,需要加強國家、民族的文化安全向城市文化安全的拓展與結合,需要加強城市文化學向文化城市學的轉變,也需要加強全球化、現代化城市擴張背景下城市政治學的審視和應對。
一、“城市文化安全”的概念內涵及戰略審視
在當前全球激烈的文化競爭和強勢的文化發展背景下,在文化帝國主義和文化后殖民的威脅和侵蝕下,作為非傳統安全的國家文化安全問題從軍事、領土等傳統安全問題中日益凸顯,并成為我國文化建設和文化管理中高度重要的現實語境。
(一)“城市文化安全”的概念與內涵
“所謂文化安全是指一國針對異質文化對本國文化的滲透、入侵和控制,通過反滲透、反入侵、反控制來保護本國人民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和社會制度的完整性、獨立性和延續性。文化安全是對當前國際關系中,文化霸權損害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文化主權這一事實而提出的應對性概念,其著眼點在于對后者文化主權的保護。”[1]文化安全針對的是國家或民族的文化和精神領域“不受外來文化的干擾、控制和同化,能夠保持本國意識形態(如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保持本民族價值觀念、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的民族性和獨特性”[2]。文化安全所面臨的威脅和風險具有多種內容、方式和形態。例如,湯林森指出,西方的文化帝國主義指涉如下層面:一是媒介帝國主義,利用媒介霸權和文化產品的大量輸出,把西方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強加給他國;二是作為民族主義話語的文化帝國主義,破壞不發達國家的文化傳統和本土文化認同;三是消費資本主義的擴張,從而導致全球文化同質化;四是現代性的擴張,即把技術、科學和理性主宰的意識形態、大眾文化、城市化和民族國家等現代性當做全球文化發展的方向和唯一模式強加給世界[3]。這些都是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和現代化語境下對本國、本民族、本土的文化安全維護所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二)“城市文化安全”的戰略審視
在高度關注國家文化安全問題的同時,要注意到作為國家和地區文化重要承載的城市所面臨的文化安全威脅,它是國家文化安全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城市不僅是城市自身的問題,也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本土性、文化傳統性、文化獨特性、文化自主性、文化價值性的問題。所謂城市文化安全,指的是城市在其文化發展和城市化進程中,保持自身城市文化形態、文化元素、文化精神、文化價值、文化生活、文化特征等的獨立性、多樣性和自主性的狀態,它針對的是強勢文化霸權通過現代城市文化和城市文明體系擴張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侵蝕。城市是國家文化體系和現代文明體系中的重要節點、承載與結晶,既是文化的容器,也是文化的機器與媒介。“縱觀世界各國,不同的國家和民族有著不同的城市形態和空間組合,展示了包括國家政治、價值取向、民族傳統、時代主張等各要素在內的文化,形成了多樣化的世界城市體系。”[4]事實上,城市作為一種文化載體與文化場域,其重要性并不低于大眾傳媒、文化產品、消費主義等形態,然而在對文化安全的研究中,城市文化安全多少是被忽視的問題,并未作為一種顯著的理論話語而得以提煉和突出,尤其是缺乏從國家文化戰略和意識形態維度的“城市自覺”。如果說“當城市成功的時候,整個國家也會成功”;那么可以說,當城市文化失敗的時候,國家的文化戰略和文化自主性也會陷入被動。城市文化安全不僅是城市文化的安全,而且更是城市的文化安全,其邏輯起點不是城市而是國家,不是城市的文化性而是城市的文化間性,關系到國家和地區文化共同體的文化價值獨立性和意識形態自主性。完整的城市文化安全觀不僅僅指向城市文化本身的問題和危機,而是將這種危機與國際文化競爭和文化帝國主義的背景加以理論和機制的關聯,從城市霸權和城市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依附”的角度加以審視。在城市文化安全的威脅下,中國城市的崛起要“避免成為全球化浪潮中地位日趨重要卻逐漸喪失其主體性(特別是完整價值體系)”[5]的城市。
二、中國城市文化安全的構成與潛在危機
城市文化安全的危機與挑戰,體現在城市文化的表現、內涵、模式等層面,并進而通過城市文化影響到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安全,包括其文化自主權、文化獨立性、文化延續性、文化民族性、文化話語權等。城市帝國主義的侵蝕形成城市與地方、城市與文化的多重斷裂,形成對我國城市本土性安全、原生性安全城市、地方性安全、傳統性安全的文化沖擊。因此,我國的城市文化必須加強以下諸方面的安全性關注。
(一)城市文化的本土性安全
城市是一種植根于特定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集聚,城市應體現著本土性、民族性的文化價值訴求。然而,在“城市帝國主義”的沖擊下,蘊藉本土性和民族性的城市被外來文化所滲透,在城市文化表征、城市文化要素、城市文化模式等多方面體現去本土化、城市的民族價值異化。其典型表現之一是城市風貌在西方城市理念和城市模式影響下的同化問題,誠如有研究者指出,“在經濟與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性城市、‘城市全球化和‘全球城市化,正在席卷世界各地的城市,城市形態和空間組合正在趨同,例如上海與紐約的空間樣態正在相似,深圳與西方世界的城市正在雷同。北京、南京、西安這樣有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城,正在以現代化整合關系,表現著同一的文化樣態。這種發展潮流……表現為民族性、地方性和多樣性的城市形態正在喪失。”[6]中國城市建設和城市化過程出現了對西方發達城市文化、城市規劃、城市設計、城市范式的較為普遍的模仿和移植,帶來城市趨同和千城一面、膜拜西方城市價值和城市神話、喪失本民族和地區的城市文化靈魂的后果。具體而言,我國城市形態的本土性、民族性的喪失,表現出“城市景觀文化的西方化、城市文化符號的西方化、城市空間——廣場和街區等等超大尺度的開發、城市建筑文化民族性符號的缺失與喪失、城市傳統街坊格局的消失、城市色彩傳統文化特質的變異、城市空間輪廓的整體性‘失語以及城市地名的西方化等”。[7]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進程中,生成著城市“本土要素的虛無化”及其對民族文化的損害,造成民族文化傳承性、凝聚力和認同度的下降。這種城市本土性的安全問題還會“在城市中出現典型‘合理性危機與‘合法化危機,其表現就是人們對中國城市結構與空間缺乏整體的文化認同,對城市化的發展和社會的整體文化價值的建構缺乏參與感”。[8]城市本土性的弱化是在全球化語境下文化“后殖民”和文化失語癥的表現,體現著強勢文化霸權通過城市對本土文化自主性的壓迫和異化。
(二)城市文化的原生性安全
城市文化安全也包括對城市中所承載和凝結的文化習俗、日常生活、文化生產和消費的原生態保護,也即保護城市文化符號和文化表達中的原生性的文化內涵和文化價值,避免其在文化保護的表層現象之下實質上卻構成對地方文化內容的潛在置換,使其在文化形式的存留中卻發生實際文化內涵的消褪乃至湮滅。其中,現代化、商業化的城市開發和大眾傳媒性、他者性的城市傳播對城市文化的安全形成嚴峻沖擊。由于不可阻擋的現代性發展話語和城市物質性擴張,中國城市在文化建設中走向文化物質化和文化產業化、文化商品化,“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屢見不鮮,并往往帶來原生文化“保護性破壞”、“開發性破壞”的異化,帶來文化自覺性的缺失。例如,“隨著外來旅游者的大量涌入,……傳統的民間習俗和慶典活動為迎合旅游者的觀看被披上了表演的外衣,很多活動雖然被保留下來了,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了傳統上的意義和價值。原本當地人視為神圣的活動,因為用來作為招攬游客的消費活動,這種神圣的性質被完全消解,而淪為純粹的旅游消費品,從而‘真實的文化變為‘展演性的文化。”[9]現代性體系和文化資本邏輯對原生日常生活和文化實踐的殖民、人口和信息流動對地域文化的同化、現代傳媒和敘述對地方的想象和規訓,都對城市原生文化特質和文化風貌產生著文化內容、文化語境、文化生態的破壞,并影響到城市的地方性、內生性文脈的傳承,帶來城市文化與城市、與文化的分離。
(三)城市文化的地方性安全
全球城市擴張體系以及城市帝國主義對城市的沖擊不僅在于其城市性的改變,也在于其城市間性的改變,城市文化的地方性和自足性趨于弱化,而是處于超地方的城市文化體系和文化間性中,成為全球文化擴張體系中的“城市機器”。同時,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地域文化逐漸失去其“本地生活在場的有效性”,城市文化與地方的固有聯結被其與“流動空間”的“脫域”[10](disembedding)關系所替換。在這種城市構架中,地方文化面臨著世界城市體系將其納入全球化語境下的城市文化對話和互動、傳播體系中的“收編”要求。而未很好融入現有城市體系的城市,則往往被以城市“異托邦”(heterotopias)和“敵托邦”(dystopia)的形式加以邊緣化處置,例如Short把平壤、巴格達、德黑蘭等被西方主導性城市體系排斥或主動抵抗國際化話語體系的城市,作為全球城市網絡中的“黑洞”和世界城市乃至城市的反面類型[11]。拒絕西方霸權所主導的全球化、保持地方性的城市文化也應具有城市敘事的合法性,并非所有的地方文化都必須所謂“世界化”尤其是納入西方的話語體系才具有其文化價值,民族或地方的“文化遺存或文化傳統的意義是自洽的,它可能不會成為世界的甚至可能根本不為世界所了解,但這并不能夠否定它的價值和意義。”[12]面對全球化的浪潮,城市應有“地方性文化”的自覺和自信,面對強勢文化體系和城市體系的擴張,城市可以而且需要保持自身被納入或不被納入、被“收編”或不被“收編”的自主和權力,而這關系到本地城市文化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四)城市文化的傳統性安全
城市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傳統和文脈的延續,這指涉到城市文化的獨特性和不可復制性。或者說,城市不只是文化景觀和文化對象的物性堆積,也是它們與城市以及城市主體的關系,城市文化是具有其自身“體溫”的傳達,而非外來城市文化模式所能簡單替換。以城市建筑為例,“建筑是有‘靈魂的,而不是一個無生命的對象。在傳統建筑中,它更是人們文化、價值體系的載體,而這一切在我國當前的城市建筑中都已經消失,城市景觀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技術的載體,成為商業的代碼。”[13]世界上許多著名都市如巴黎、東京等,在現代化浪潮下并未迷失自身歷史傳統、民族風貌和本土特色,而是成為堅守國家和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堡壘。然而我國的城市化發展進程中,體現出對自身地域文化、文脈、城市記憶、城市情感的自覺和自信的缺乏,存在著將城市現代化狹隘理解為高樓大廈、玻璃幕墻等類同的模式,“名城的特色在消失,個性在泯滅,歷史文化內涵在削弱。”[14]當城市的獨特性僅僅是一種城市建筑、場所、景觀的設計獨特性而割斷其獨特的文化傳統、文化記憶、本地“植根性”(rootness)的時候,它是可以復制、移植乃至規模化再生產的,這對城市的文化競爭力、文化軟實力方面的特殊性和不可復制性帶來威脅和挑戰。城市文化傳統性的消解也會進而威脅到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傳統和“集體記憶”的延續及傳承,“正如故宮、天壇對于北京,西湖、靈隱寺對于杭州,外灘、豫園對于上海,中山陵、夫子廟對于南京,瘦西湖和‘煙花三月的概念對于揚州一樣,城市的形態創造的歷史積淀,既是城市本身的記憶,也是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賦予城市以個性化的鮮活生命力。”[15]我國高速的城市化進程和大規模的城市改造中,許多城市在城市規劃和城市景觀設計上大都在引入、模仿發達國家的城市化,忽視對地方文脈的延續與融合,這種移植往往帶來城市文化價值、文化內涵、文化傳統、文化認同在城市迅猛的物質性擴張和物象增殖中的重要風險。
三、中國城市文化安全的維護與多元策略
城市文化安全是我國高速城市化進程中的重要問題,是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組成,也是關系到城市發展的文化自主性、文化自覺性、文化內生性的重要文化問題。然而,城市文化安全問題在我國的文化安全與城市文化研究中還比較薄弱,雖然有學者注意到這個問題,但是還缺乏從理論自覺的層面對之進行提煉與細化的系統分析,在國家和地方的文化政策實踐中也缺乏足夠的文化的“城市自覺”。我國城市文化建設和城市化發展進程中,需要著力加強城市文化安全的維護和應對。
(一)加強城市文化本土性安全的打造
要增強城市文化的本土性理念,優化城市文化的地方性規劃,構建與國家文化安全相一致的本地城市文化設計;樹立對本土文化的自信意識乃至敬畏之心,保持城市文化對民族和傳統文化資源、文化要素的自覺傳承與弘揚,使城市文化的本土化重塑成為具有國家和民族意義的文化之根與文化之魂;避免城市風貌在傳統與現代、地方與全球的矛盾搖擺中帶來的拼貼化乃至碎片化,防止城市在被外來城市文化的入侵和同化中迷失本土的精神氣質和文化特質。
(二)加強城市文化原生性安全的維護
要避免城市文化保護的標本化、靜止化、切片化,注重對其所處的社會文化系統的生態整體性保護;在對城市中各種物質性或非物質性的文化遺產、文化景觀、文化元素進行保護的同時,還要加強對“地方”作為文化生態圈的尊重和整體保護及其“活態”文化和城市日常生活系統的保護,這也涉及到城市內部、城市整體乃至城市群等不同層級的“文化生態保護區”的設置與維持。
(三)加強城市文化多樣性安全的自主
城市正如文化也有其多樣性和多元性,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城市多樣性遭到的入侵也意味著其文化多樣性和自主性遭到的潛在入侵。新世紀以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和實施《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和《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強調對不同時間和空間的文化多樣性的尊重和保護,重申各國制定文化政策的主權。我國要維護本國制定城市文化政策和戰略的自主性,提倡多樣化和“中國性”的城市文化典范與城市文化競爭力模式;加強國家性的文化名城、特色文化城市、文化魅力之都體系的構建與推廣,打造可與國際主導性文化城市話語權相抗衡的中國城市范式和多樣化形態。
(四)加強城市文化傳統性安全的保護
要加強城市歷史文化的整體保護,保存和維系國家和民族集體記憶的城市表達;加強傳統城市建筑和景觀、地方性文化元素與城市的有機融合;注重城市街區、城市景觀、城市標志、城市活動中特殊的文化記憶和情感內涵,激活城市對于人的特殊性以及城市在“流動空間”時代所散發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認同感;加強對城市“文脈”的保護傳承,維護城市文化的獨特性和不可復制性。
四、結語
面對城市文化安全的危機和挑戰,中國城市文化必須擔負起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價值進行現代城市表達的職能,打造具有文化價值的代表性、范式性、引領性的本土城市、地方城市、原生城市、特色城市,在現代化、全球化的城市發展進程中加強對城市帝國主義和西方強勢城市霸權的戰略回應,維護中國城市的文化自主權和文化話語權,維護選擇自身城市文化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的意愿與能力。
說明:本文是2011北京市優秀人才培養資助項目(2011D002035000002)的部分成果。
參考文獻:
[1] 王公龍.文化主權與文化安全[J].探索與爭鳴,2001(9).
[2] 田文林.國際政治視野中的文化因素[J].現代國際關系,1999(9).
[3] 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6][7][15] 張鴻雁.中國本土化城市形態論[J].城市問題,2006(8).
[5] 張煉紅.中國經驗與文化自覺:拓展“中國城市文化”的觀念與格局[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1(8).
[8] 張鴻雁.城市定位的本土化回歸與創新:“找回失去100年的自我”[J].社會科學,2008(8).
[9] 涂成林,史嘯虎,等.國家軟實力與文化安全研究[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203.
[10] [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上海:譯林出版社,2000:18~26.
[11] John Rennie Short. Black Holes and Loose Connections in a Global Urban Network[J].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04,56(2).
[12] 周曉虹.城市文化與城市性格的歷煉與再造——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關懷[J].浙江學刊,2004(4).
[13] 呂寧興,耿虹.中國城市建筑景觀與后殖民主義批評——中國城市建筑景觀“趨同”的思想根源及其出路[J].城市發展研究,2011(8).
[14] 趙鳳.探求中國城市發展的本土化與個性化之路[J].甘肅理論學刊,2007(5).
責任編輯:張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