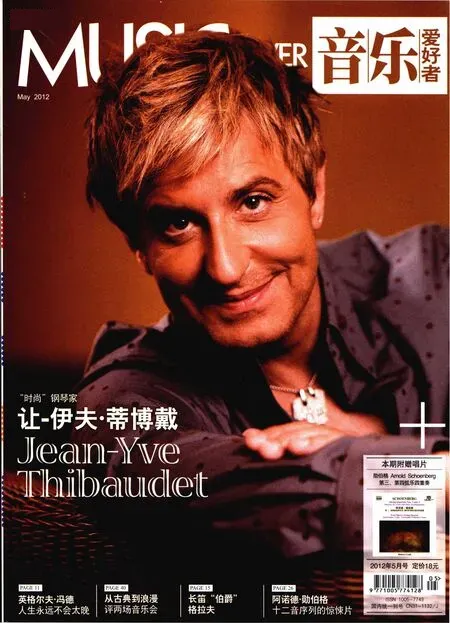阿諾德·勛伯格:十二音序列的驚悚片
卓爾

就在晚期浪漫主義的音樂創作變化似乎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勛伯格發明了一種大膽激進的作曲方式,而它所帶來的影響,既具有積極的一面,同時也引起了當時音樂界的一陣軒然大波。
勛伯格曾經說過一個一戰期間他在奧地利軍隊服役時的故事。一位軍官問他是否就是“那個臭名昭著的作曲家”。“這樣說吧,先生,”身為士兵的勛伯格以地道的維也納方言回答道,“就好比有人登廣告招聘工作,但沒有人愿意做,只有我接受了這份工作”。
然而,不是每個人都覺得“有人必須接受這份工作”,甚至到現在也不是。在浪漫主義的發展已經奄奄一息時,這是嘗試給音樂帶來一種全新的秩序。如果沒有勛伯格的話,我們很難想象二十世紀的音樂歷史將會是怎樣的。不管你是喜歡還是厭惡他的作品,都是一個無法回避將音樂引向一條新道路的杰出人物。
阿諾德·勛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年出生于維也納,小時候家境貧寒,十六歲時父親去世,但這些不利的環境并沒能阻止他熱愛音樂和學習音樂的決心。他從小學習小提琴,后來又自學大提琴,和他的同學奧斯卡·阿德勒(Oskar Adler)一起演奏室內樂,同時自己嘗試作曲。由于家境日益困窘,勛伯格到一家銀行當了辦事員,以增加一些家庭收入。就在這個時候,他偶然結識了后來成為他大舅子的作曲家亞歷山大·策姆林斯基(Alexander Zemlinsky),并跟他學了幾個月的對位法,這也許是勛伯格受到的唯一的正規音樂教育了。其間,他在演奏、指揮以及改編其他作曲家的作品上獲得了一些實際的經驗。雖然成長于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等偉大的維也納音樂傳統,但勛伯格不僅僅滿足于對過去風格的禮貌模仿。他受到理查德·戴默爾(Richard Dehmel)一首詩歌的啟發,于1899年創作了弦樂六重奏《升華之夜》(Verkl rte Nacht),在當時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它聽上去就好像有人在瓦格納《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的樂譜還沒干的時候又進行了涂改。”輕歌劇作曲家理查德·霍伊貝格(Richard Heuberger)輕蔑地譏諷道,不過《升華之夜》卻一直是勛伯格本人最喜歡的作品之一。接著就有了《古雷之歌》(Gurrelieder),為大型聲樂和管弦樂而作的抒情康塔塔,這是一部浪漫主義晚期的的巔峰之作,那時勛伯格年僅二十六歲。
1901到1902年間,勛伯格擔任柏林一家酒館樂隊的音樂總監,然后因為得到了理查·施特勞斯和馬勒的支持,他在維也納確立了作為一名作曲教師的聲譽。自學成才的勛伯格在教學上擁有驚人的才華,并且把他對音調語言(Tonal language)改革的理解體現在了里程碑式的教科書《和聲學》(Harmonielehre)中。這本書最早在1911年出版,它的開首語非常有名:“這本書是我從我的學生那兒學到的。”他最早的一批學生,同時也是他熱情的支持者,包括阿爾班·貝爾格和安東·韋伯恩,創立了所謂“第二維也納樂派”的核心。勛伯格的嗓音嘶啞,脾氣暴躁,是個老煙槍,但卻充滿迷人的魅力以及黑色的幽默。他就像是一個在緊張時會產生能量的發電機。
1906年,勛伯格為十五位演奏家創作了《室內樂交響曲》(Chamber Symphony),其大膽新穎的和聲反映了無限的自信心。但是在1908年,他遭遇了一次悲慘的個人危機:他的妻子瑪蒂爾德(Mathilde)和他的密友、年輕的畫家理查德·蓋斯特爾(Richard Gerstl)有了外遇——不過當她回到勛伯格的懷抱之后,蓋斯特爾自殺了。再加上他在藝術上受到的爭議,他的音樂劇烈地轉向了極端和充滿焦慮的主觀性。結果是一種來自下意識的基本沖動,促成了至今為止仍然難以想象的作品,比如《交響樂作品五首》和獨幕獨唱劇《期待》(Erwartung),這兩部作品都是用閃電速度寫成的。
這些完全用半音階寫成的作品常常被錯誤地認為是“無調性”的。當赤裸裸的情感覆蓋了之前所有的音樂規則,創造了一個音樂上的表現主義,傳統的調性感便消失了。勛伯格自己也開始畫畫,和瓦西里·康定斯基(Vassily Kandinsky)成為了朋友,并和他共同舉辦了第一個表現主義的畫展。同時他還是個發明家,發明了一臺音樂打字機,一個做眼科手術的儀器,在巴士、有軌電車和地鐵使用的聯合車票,控制城市交通擁堵的方案,以及有著一百格而不是傳統六十四格的國際象棋新形式。
在1911年移居柏林之后,勛伯格變得更加聲名狼藉了,但同時也取得了成功,特別是作品《月迷皮埃羅》(Pierrot Lunaire,1912年),他為朗誦者和器樂而作的最出色的“表現主義酒館歌舞”。在戰時服役結束后,勛伯格繼續教學,并且在維也納創立了“非公開音樂演出社”,專門演奏二十世紀的新音樂,后來成為了許多現代音樂組織效仿的對象。
這個時候,勛伯格陷入了一個創作上的僵局,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發明了“用十二個互相有聯系的音來作曲的方法”才被打破。同時,他培養了新一代的作曲家,包括馬克思主義者漢斯·艾斯勒(Hanns Eisler)、西班牙作曲家羅伯托·杰哈德(Roberto Gerhard)、最后死于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維克多·厄爾曼(Viktor Ullmann)以及魯道夫·科利施(Rudolf Kolisch)。1925年,勛伯格接替布索尼擔任柏林藝術學院作曲大師班的指導,來自世界各地才華橫溢的學生都向他涌來。
早在1923年,勛伯格就預見了希特勒的崛起。1933年,納粹奪取政權后,指責其音樂頹廢,是毒害德國青年的垃圾,把身為猶太人的勛伯格趕出了德國。他只好流亡法國,在那兒他先是改信了基督教,后來又正式地改回了猶太教。那時,他已經寫了《摩西與亞倫》的大部分,這部十二音的史詩歌劇取材于《圣經·舊約》的“出埃及記”,結構雄渾一體,音樂表現力極強,被公認為二十世紀的不朽杰作。和其他流亡者一樣,勛伯格發現自己“被驅逐到了天堂”,他乘船前往美國,在波士頓一家小型音樂學校任教。他最終定居在好萊塢,并在洛杉磯的加利福尼亞大學(UCLA)任教,直到七十歲時被迫以微薄的養老金退休。他培養了新一代的一批學生,包括約翰·凱奇和羅·哈里森(Lou Harrison),但是讓他感到難過的是,他的音樂幾乎不被聽到,人們更多地只是談論而不是演奏它。晚年的勛伯格創作了不少讓人滿意的作品——《第四弦樂四重奏》、小提琴和鋼琴協奏曲,以及弦樂三重奏等。他還寫了一些有調性的作品,聲稱“還有很多好音樂可以用C大調寫成”,并且在音調和聲的方向擴大了十二音作曲體系的詞匯量。
在大西洋另一邊的大屠殺中,勛伯格失去了很多家庭成員和朋友。他抵制納粹恐怖活動的個人見證,就是康塔塔《一個華沙的幸存者》(A Survivor of Warsaw),取材于華沙猶太人區的一個故事。這部作品中的十二音作曲技巧有著極富魅力的戲劇性效果,在美國的阿爾伯克基(Albuquerque)首演時,合唱團主要由當地農民組成,雖然聽眾對勛伯格的作曲風格并不熟悉,但這部作品獲得了長久的熱烈鼓掌。
由于沒能得到足夠的資金來完成剩下的一些作品,以及還有三個孩子要撫養,晚年的勛伯格在健康、教學和作曲方面狀況不佳。他于1951年去世時,遺言竟然是“和聲!和聲!和聲!”
雖然生來就如此有爭議,勛伯格的理論從來都是受到他作曲實踐的推動,而不是相反。作為三代學生的導師,他的作曲方法被不計其數的其他人借鑒并延伸,成為了后來許多革新者的基礎。雖然他的反對者人數眾多,但是他那充滿煽動性的作品和觀點,使任何只想“按常規方法”來創作音樂都成為不可能。
音樂風格
更多的傳統
勛伯格信奉從巴赫開始的德奧傳統——包括約翰·施特勞斯和雷哈爾。他的早期作品將勃拉姆斯式的古典風格與瓦格納浪漫的半音化和聲結合在一起,產生了一種全新的、具有高度表現力的音樂語言。
十二音作曲方法
從1908年左右開始,勛伯格迅速創作了一系列由半音音階構成的十二個音循環的音樂,使“調性”變得很難去感覺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早期,他找到了一種組織音樂材料的新方法,形成了所謂十二音音樂:他使用半音音階中的十二個音,自由地組成一個音列,音列可以原形使用,也可以逆行、倒置、倒置逆行。所有的主題、動機及和弦都從中產生,以確保和弦與和聲的統一。雖然音階的順序是固定的,但作曲家可以自由地發展和聲、節奏、強弱等等。
多種聲音
事實上,勛伯格的所有音樂都是高度對位的,有同時進行的幾條旋律。他發現十九世紀晚期的半音和聲導致了對于感官的依賴,它們拘泥于復雜的和聲,而失去了樂思的自由流動。于是他復興了許多擁有嚴格對位的古典形式——卡農、倒置、模進(mirror form)等;十二音體系非常適合以一種全新的方式來使用這些作曲技巧。
——評《勛伯格與救贖》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