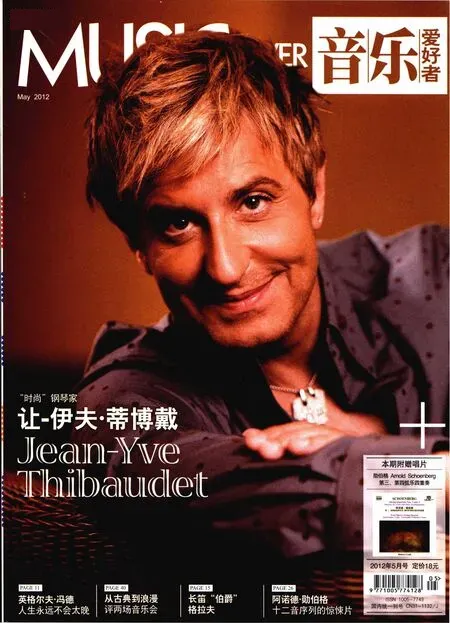從古典到浪漫
孫國忠



四月初的上海,風和日麗,鳥語花香,音樂會舞臺也是春意盎然,生機勃勃。由洛林·馬澤爾率領的英國愛樂樂團與特邀穆洛娃加盟的瑞士巴塞爾室內樂團相繼訪滬演出,令上海的樂迷們大飽耳福,欣喜不已。
在古典音樂界,盡管沒有流行音樂界或影視圈那種瘋狂的追星現象及“粉絲”人潮,但“明星效應”同樣存在,大師魅力依舊神奇。馬澤爾與英國愛樂樂團這場音樂會至演出前一星期已是一票難求,吊足了樂迷們的胃口,這一現象無疑證明了愛樂人群中普遍存在的“大師崇拜”情結。穆洛娃的影響力雖然沒有馬澤爾這么深廣,但是這位“天后級”的小提琴家在愛樂圈中也是人氣極高,從音樂會上申城觀眾對她表現出的不一般的熱情就能感受到演奏大師的特殊光彩和強大氣場。
對照一下巴塞爾室內樂團與英國愛樂此次訪滬音樂會的節目單是很有意思的:前者奉獻的幾乎稱得上是“完全貝多芬”(另奏一首瑞士當代作曲家魯道夫·凱爾特伯恩的作品《為古典時期樂隊而作的四個樂章》),后者展示的則可謂“浪漫的絢麗”(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與馬勒)。兩者合在一起,我們面對的正好是從古典到浪漫的音樂歷程與交響精華。換個角度看,這兩個樂團的樂隊建制、歷史傳統和藝術風格又大顯異趣:巴塞爾室內樂團的演奏帶來了本真實踐的清純甘美和舒朗灑脫,英國愛樂的表演則盡顯浪漫交響的重彩濃抹和豪放宏廓。
巴塞爾室內樂團是第一次訪滬演出,從音樂會的曲目和特邀演奏家來看,樂團為這次上海之行做了精心的準備,力圖全面展示自己獨具的風采。當今世界的專業性樂團主要分成兩大類:大型的交響樂團(Symphony Orchestra)和中小型的特色性樂團。以四管編制為典型建構的大型交響樂隊已是目前正規交響樂團的“規范模式”,在此無需贅言;而中小型的特色性樂團可謂五花八門,在此不妨多說幾句。在這類中小型樂團中,有一大部分都是專門演奏早期音樂(或者干脆說是巴洛克音樂)的樂團,樂隊編制較小,整個弦樂只有十人左右,再加上若干個管樂器(木管為主)。當然,這樣的樂隊組合非得有一個羽管鍵琴的演奏,它的主要功能一方面是為了呈現作曲家以通奏低音(Basso Continuo)形式標出的和聲,另一方面則是引導和掌控整個樂隊演奏的速度、力度、情緒和氣息。因此,通奏低音在樂隊中的核心地位使它顯現出“靈魂”的意義。這類小型組合的樂團名稱繁多,常見的有Consort、Ensemble、Concert等,其基本的涵義都是“小型合奏團”。還有一部分則是中型規模的室內樂團(Chamber Orchestra)。這類樂團通常以一個弦樂隊為主體,再加上一些管樂器,有些樂團已達到完整的雙管編制,擅長演奏海頓、莫扎特和貝多芬時代的交響音樂作品,也可演奏浪漫時代或現代派的一些樂曲,尤以演奏弦樂隊作品而聞名。像圣馬丁室內學院樂團(Academy of St. Martin in the Field)和倫敦室內樂團(London Chamber Orchestra)就是這類樂團中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室內樂團已經去除了羽管鍵琴,因為它們的演奏曲目主要是“前古典”(PreClassical)以來的音樂,通奏低音此時已經淡出了歷史舞臺。巴塞爾室內樂團就屬于這一類型的管弦樂表演團體。
巴塞爾室內樂團的歷史不長,但近年來的發展勢頭令人矚目,其卓越的成就贏得了音樂界的高度贊譽,這次率團前來上海演出的常任指揮喬萬尼·安東尼尼(Giovanni Antonini,1965-)對此功不可沒。講到安東尼尼與巴塞爾室內樂團的合作我們就會聯系到“表演實踐”(Performance Practice)的話題。“表演實踐”的興起自然引發了音樂“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探討。“本真性”這一術語可以引出一連串相關的詞語:本真性演奏、本真主義、本真運動等。我認為:“本真性”既是一種音樂觀念與藝術理想,也是一種演奏(唱)方法和表現姿態。例如,“本真性”音樂表演特別強調的用“時代樂器”(Period Instruments)來演奏先前時代的作品(“古樂”)就是走向音樂歷史和貼近時代風尚的有意義的探索。在我看來,音樂表演藝術中不可能有嚴格意義上的“原汁原味”,只有在各個音樂時代特定語境的“構想”中呈現的“典型體現”及“相對準確”,因為以樂譜形態為承載樣式并需通過“二度創作”(音樂表演)來展示的音樂藝術永不存在“時間”與“空間”意義上的“釋義定本”——任何探求音樂“原旨”和時代“真義”的演奏實踐只是接近“本真”的一種嘗試。從擴展音樂表演的路徑和豐富音樂生活的角度看,“本真性”音樂表演可謂功德無量,它讓愛樂人有了更多體驗藝術,品味風格,感懷時代和想象歷史的音樂審美選擇。
安東尼尼這位早年以豎笛演奏和創建“和諧花園”古樂團而嶄露頭角的意大利指揮家與巴塞爾室內樂團合作以來,已產生了一系列絢麗多彩的“化學效應”,其中最突出的成果就是近幾年先后錄制的貝多芬的“第一”至“第六”交響曲,頗有直追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加德納與“革命與浪漫管弦樂團”那套評價極高的“本真版”《貝多芬交響曲全集》的強勁態勢。因此,安東尼尼和他的巴塞爾室內樂團在滬音樂會上所呈現的“完全貝多芬”正是他們對貝多芬作品詮釋充滿熱情與自信的明確體現。這場音樂會上有三部貝多芬的作品,分別是《科里奧蘭》序曲、《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Op. 61)和《A大調第七交響曲》(Op. 92),這三種不同體裁的作品組合形成極為典型的交響音樂“綜合展示”。
《科里奧蘭》序曲是一部很有張力的音樂作品,雖然“名氣”不如《艾格蒙特》序曲,但它的藝術分量和歷史意義并不亞于后者。盡管學界對這首器樂曲的“文本”來源有不同的看法,但它的問世的確與海因里希·約瑟夫·馮·科林(Heinrich Joseph von Collin,1771-1811)的戲劇《科里奧蘭》相關。另外,也有文獻證明貝多芬在為科林的戲劇創作這首序曲時,仍念念不忘莎士比亞的同名劇作。還有學者提出,貝多芬心目中的科里奧蘭形象甚至有可能受到普魯塔克(Plutarch)的名作《傳記集》中科里奧蘭這個傳奇人物的影響。以上三種“文本”對科里奧蘭的敘述角度不同,結局有異,但它們都著重于刻畫科里奧蘭這個古羅馬貴族的矛盾個性、復雜心理與悲劇命運。貝多芬的這首序曲雖然源自科里奧蘭的“故事”,但它的藝術蘊涵明顯已經超越了對戲劇情節本身的音樂描述,上升到一種展示悲劇意識與體現英雄情懷的交響敘事的高度。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首序曲的主調為C小調,這正是貫通貝多芬音樂血脈的永遠的“悲劇性基調”。
作為巴塞爾室內樂團訪滬音樂會的“開場曲”,《科里奧蘭》序曲的演奏是激動人心的。安東尼尼對樂曲開始處那三個強勁的C音及其三次被突然打斷的藝術處理極具戲劇性,那是一種震撼,一種逼人身心的命運重壓。主部主題進入后,悲劇的氣氛更加濃烈。安東尼尼的速度奇快,樂隊的演奏自然呈現出一種張力十足的緊迫感。正是有了主部主題這一緊張的情境組建,樂隊奏出的副部主題才顯得如此舒展明暢。我一直認為《科里奧蘭》序曲的副部主題是貝多芬最優美的旋律之一,英雄情懷中永遠包含著愛之渴望、愛之力量。安東尼尼的指揮動作幅度較大,帶出了樂隊棱角分明的層次變化和情緒對比,非常符合貝多芬中期音樂風格中那種特有的大開大合的氣勢和昂揚奮進的品質。樂隊演奏員們用的是“時代樂器”或稱“仿古樂器”(主要指銅管樂器),音響通透,音色清朗,這種帶有粗豪質感的聲響構筑使得貝多芬這首具有“標題”意味的交響序曲在音樂會一開頭就形成了強大的氣場。在現場聆聽中體悟《科里奧蘭》序曲的藝術蘊涵,我深深感到貝多芬巨大的創造力和影響力,因為這首“戲劇性”序曲的問世已經為浪漫主義時代音樂會序曲(Concert Overture)的誕生奠定了實實在在的基礎。
巴塞爾室內樂團訪滬音樂會上的最大亮點當然是穆洛娃演奏的貝多芬《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穆洛娃堪稱蘇聯小提琴學派的杰出代表,功底扎實、技藝驚人,除擅長演奏俄羅斯-蘇聯作曲家的作品之外,這些年也演出、錄制了不少其他西方作曲家的小提琴名作,包括協奏曲和奏鳴曲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在四十歲之后開始對本真性演奏產生了興趣,與加德納及其“革命與浪漫管弦樂團”合作的貝多芬《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更是達到了她事業上的新高峰。與安東尼尼及巴塞爾室內樂團合作首次來滬演出她的拿手曲目,穆洛娃自然是傾力展現其獨具魅力的演奏藝術。
觀舞臺上穆洛娃演奏的貝多芬《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我想用“爐火純青”四個字來形容是恰當的。穆洛娃有著強大的氣場,從她剛走上舞臺的那一刻起,整個音樂廳就被她牢牢地吸引。年過半百的她著裝優雅,儀態大方,琴音未起,高貴的舞臺形象就已經征服了全場。為了更好地融入追求“本真”理想的巴塞爾室內樂團的音色,穆洛娃演出時在她那把名貴的斯特拉迪瓦里琴上安裝了羊腸琴弦。不僅如此,為了展現貝多芬這部作品中古典底蘊的高雅純凈,穆洛娃的揉弦是比較控制的,換言之,她力圖去除過度揉弦所導致的甜美纏綿,而是想用一種相對清朗的聲響和澄明的音色來構建“本真”話語中的古典精神。作為大師級的女性演奏家,穆洛娃的表演自有她獨到的細膩表現與藝術精致。例如,穆洛娃琴聲中的第一樂章的副部主題不僅有寬廣流暢的線條脈絡,更有細致入微的氣息轉折。同樣,在第三樂章演奏中,穆洛娃對回旋主題的每次出現都賦予情趣與韻味的變化,時而輕巧歡愉,時而激情豪放。這樣收放自如與灑脫超逸的演奏只能出自大師之手,這是底氣、功力、品位與修養的展示。我以為,表演藝術上的“爐火純青”實際上就是一種藝術“表現度”的高超控制,它既是純熟技藝的表現,更是獨特的藝術理解和個性風采的展示。無疑,穆洛娃演奏的貝多芬《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確實已經達到了令人贊嘆的至高藝術境界。
巴塞爾室內樂團演奏的貝多芬《第七交響曲》也給上海的樂迷們帶來了驚喜。聽慣了卡拉揚指揮的大交響樂團演奏的貝多芬作品,“本真實踐”中的貝多芬交響曲的確“不同凡響”。“時代樂器”的運用自然是構建“時代音響”的基本手段,但更為重要的是具有本真主義理想的指揮家及樂團對古典音樂“精、氣、神”的準確把握與詮釋。在貝多芬整個交響曲的創作中,《第七交響曲》占有一席特殊地位,這部作品與差不多同時完成的《F大調第八交響曲》(Op. 93)已是貝多芬中期創作的尾聲,作曲家本人非常看重此曲,稱之為“我最優秀的作品之一”。《第七交響曲》既有“第三”“第五”交響曲那種宏大的氣勢,又延續了“第四”“第六”交響曲所呈現的抒情性表達,更為重要的是這部交響曲具有自己獨特的品格——通過舞蹈的歡騰表達民俗的生機與生命的張力。正如瓦格納所言,這是舞蹈的頌歌、生命的禮贊。我覺得安東尼尼與他手下的樂團對貝多芬這部作品的演釋是比較準確的,透亮的音色、流暢的氣息、直率的情緒與充滿活力的韻律將整部交響曲的民間意態和質樸趣致栩栩如生地展現在我們面前。觀安東尼尼的指揮藝術和音樂演釋我會聯想到自己傾心的本真主義大師加德納(John Eliot Gardiner,1943- ),因為兩者的表演風格有著某種相似之處,那就是在音樂演釋中用熱情率真的氣韻和明暢健朗的意象重“古樂”的淳樸品格與世俗精神。
坦率而言,馬澤爾并不是我最心儀的指揮家,但他的才氣、素養令我敬佩,尤其是他在八十高齡之后依然活躍于他所熱愛的音樂舞臺,著實讓我感動。四年前馬澤爾率領紐約愛樂樂團來滬演出,我也曾興致勃勃地趕去上海大劇院捧場,但聽后感覺一般,音樂會上作為“重頭曲目”的柴科夫斯基《第六交響曲》并不見什么特殊的精彩。這次馬澤爾率領英國愛樂樂團來東方藝術中心演出,我依然欣然前往。說白了,我是沖著馬澤爾的馬勒《第一交響曲》而去的。眾所周知,馬澤爾是當今有影響的“馬勒專家”之一,所以我很有興趣到現場去領略一下這位“專家”所詮釋的馬勒音樂。
聽到音樂會上第一首樂曲——勃拉姆斯《學院慶典序曲》(Op. 80)的演奏,我心里就有點犯怵,頗為后面兩部作品的演出而擔憂。勃拉姆斯的這首序曲本是一部應景之作,專為答謝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的布雷斯勞大學而作(1880年),曲中引用了幾首流行的學生歌曲,聽上去比較熱鬧,其實并沒有什么藝術深意,遠不及他同年寫成的另一部單樂章管弦樂曲《悲劇序曲》(Op. 81)。《學院慶典序曲》的音樂本來就顯得有些松散,加上馬澤爾與樂隊似乎都未進入狀態,因此整首樂曲的演奏根本無法讓人興奮起來。
音樂會上半場的第二首作品是柴科夫斯基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Op. 35),由上海籍的青年小提琴家陳佳峰擔任獨奏,這是東方藝術中心為提攜本地青年藝術家專門向馬澤爾及英國愛樂推薦的“特別曲目”。陳佳峰是近年來上海涌現出的多位青年音樂才俊之一,畢業于上海音樂學院,先后師從趙基陽、張世祥和方蕾教授,榮獲多項國際重要音樂比賽的獎項,包括2003年維尼亞夫斯基國際小提琴比賽的金獎。目前正在朱利亞音樂學校從名師林昭亮教授學習的陳佳峰此次是專程趕回上海來與馬澤爾大師及英國愛樂合作,演奏他的拿手曲目柴科夫斯基的協奏曲。
柴科夫斯基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位列“四大小提琴協奏曲”之一,旋律優美,風味獨特,與德國及西歐音樂傳統的協奏曲在風格氣質上有很大的不同,歷來深得大眾之心,也是諸多小提琴家樂意演奏的名曲,既能展示演奏者的技藝,又會有強烈的演出效果。
陳佳峰的演奏技巧熟練,表演自然,聽得出他對這部協奏曲是下過很大功夫的。他的演奏中有種獨特的抒情氣質,這不僅表現在其優美的音色中,也顯示于他對長氣息樂句抒情性的自如把握中。這一特點在第二樂章中得到了盡情的發揮。第二樂章的音樂是柴科夫斯基“俄羅斯憂郁”的典型展示:第一主題纏綿悱惻,幽情婉麗,第二主題稍許明朗,寬慰之中透露出一絲暖人的溫情。這兩個抒情主題雖有對比,但音樂的底蘊都是孤凄的情味和憂悒的感懷。陳佳峰的演釋相當感人,他對第一主題的悠長氣息與顫音意趣控制得極好,寧靜的悲涼之中仿佛有種詩意的嘆息,而他琴聲傳遞的第二主題又能呈現內含激情的幻象訴求。當然,這位青年小提琴家的演奏也有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例如,個別高把位音區的音樂表達略欠精準,與樂隊的配合似乎還不夠默契,這在幾處快速段落的演奏中聽來尤為明顯。當然,這些小小的瑕疵都不影響陳佳峰對這部協奏曲名作的整體演釋,應該說演出是成功的。
值得一提的是,馬澤爾在指揮這首協奏曲時完全背譜,這確實讓人肅然起敬。許多指揮家盡管在指揮交響曲、交響詩序曲及其他管弦樂體裁的作品時愿意背譜指揮,但指揮協奏曲時都會在指揮臺前的譜架上放上總譜,因為協奏曲這一體裁的音樂特殊性——獨奏樂器與管弦樂隊在從頭至尾的“對話”中展示音樂話語及其藝術蘊涵——要求指揮家格外精準、明確地整合獨奏與樂隊的關系,展現這兩者間既分又合的“對話原則”與協奏邏輯,稍有閃失,后果嚴重。因此,指揮家看譜指揮協奏曲可算是合情合理的音樂會演出常態。馬澤爾在八十高齡依然背譜演奏包括協奏曲在內的交響樂作品,一方面是他卓越才華的自然體現,另一方面則是他永遠全神投入音樂演釋、身心融入藝術神圣表達的最好寫照。需要說明的是,是否背譜演出并不是判斷一位指揮家藝術水準的唯一標桿,但是,我認為背譜指揮應該是指揮家演出時的理想狀態(真正偉大的指揮家幾乎都是背譜演出),這不僅是指揮家完全融入音樂的實際體現,它也使音樂會聽(觀)眾視野中的指揮家形象(關聯到指揮藝術的獨特作用與重要意義)增添了一種信任度和親切感。
馬澤爾與英國愛樂的演出在下半場才真正進入了高潮,眾人期盼的“馬澤爾的馬勒”登場了。我對2009年夏伊指揮萊比錫布商大廈管弦樂團在上海大劇院演奏的馬勒《D大調第一交響曲》記憶猶新,那是一次非常精彩的演出。如今現場聆聽了馬澤爾的演出后,我能肯定地講:馬澤爾指揮棒下的馬勒“第一”絲毫不遜于夏伊的演釋,它同樣精彩紛呈,感人至深。
人們都說馬勒的交響曲復雜艱深,實際上他的《第一交響曲》還是比較容易理解的。這部交響曲的創作與作曲家的聲樂套曲《旅行者之歌》有聯系,作品初稿原有五個樂章,其標題分別為:一、不盡的春天;二、百花吐艷;三、滿帆向前;四、獵人與葬禮進行曲;五、從地獄到天堂。后來的正式版本去除了原先的第二樂章與全部標題。雖然這部作品與馬勒的其他交響曲一樣,都用“宏大敘事”的藝術呈現來展示作曲家的哲理思考和對人生意義的探索,但此曲的音樂話語有著馬勒早期創作風格中典型的抒情氣息與明朗表達。無論是第一樂章的田園景致、第二樂章的風俗舞蹈,還是第三樂章別樣的葬禮行進、第四樂章的生命贊歌,馬勒顯然是有意用貼近生活的音樂語言和表現手法來引導受眾對作品的理解。可以這么說,《第一交響曲》是走進馬勒音樂世界的最佳通道。
馬澤爾的馬勒“第一”意氣風發,光彩奪目,完全看不出年邁的老態。他的指揮動作不大(順便一提:三四十年前馬澤爾的指揮姿態那可是相當夸張。有興趣的樂迷可以看看他任克里夫蘭交響樂團音樂總監時的演出錄像),但拍點、提示極其清楚,樂隊在他魔力般的手勢下可以說要什么效果出什么效果。這部交響曲中有一些弦樂的抒情歌唱,我注意到馬澤爾在指揮這些段落時特別動情,效果奇佳,這或許與馬澤爾本人擅長小提琴演奏有關。馬澤爾在細節處理上的精致無需多說,但音樂“大模樣”上的光彩必須提及:第一樂章的寬廣瑰麗,第二樂章的酣暢淋漓和第三樂章的反諷意趣都明顯帶有指揮家自己的理解,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無疑,最讓我震撼的還是終樂章的演奏。這一樂章結構龐大,樂思紛雜,是典型的馬勒式交響思維。馬澤爾的詮釋邏輯清晰,層次分明,藝術效果強烈。他對其中幾個抒情主題的處理深得我心,這位“馬勒專家”拒絕夸張拖沓,強調的是明晰流暢的情致,這般的純情優美才讓人體悟到青年馬勒真情流露的感人。我想熱愛馬勒音樂的聽眾面對馬澤爾與英國愛樂呈現的終樂章戲劇性尾聲都會情緒高漲。八個圓號的起立吹奏和整體管樂能量的盡情釋放,這是何等的雄壯輝煌!我在觀眾席上望去,只見此時臺上的指揮大師和樂隊演奏員們同樣顯得非常興奮,與觀眾共同享受著馬勒作品帶來的激情與感動。
此曲奏畢,全場沸騰,雷鳴般的掌聲伴隨著“Bravo”的吼叫,東藝音樂廳頓時成為歡樂的海洋。毫無疑問,亢奮的觀眾都在熱切等待大師返場后的“Encore”。雖然我也很激動,但并不期盼“Encore”的出現。我認為,在馬勒“第一”這樣氣勢恢宏、蘊意深厚的交響杰作演出之后,很難有什么加演曲目能控制得住馬勒音樂的氣場,就此打住應該是最好的選擇,這會讓我們更好地保存感受壯麗之精彩后的美好印象。馬澤爾在多次謝幕后還是重返了指揮臺。說實話,那一刻的我心里有些緊張,希望聽到的不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更不是為表達國際友誼而奏響的“邊塞風情”。隨著馬澤爾的手勢一起,瓦格納歌劇《紐倫堡的名歌手》豪放壯美的前奏曲響徹大廳。我釋然了,且由衷地佩服:大師就是大師,這是多么恰當的“Encore”選擇!除了瓦格納,還有誰能鎮得住馬勒?
現場聆聽馬澤爾的馬勒“第一”,讓我對這位大師的指揮藝術有了新的認識。我盼望不久的將來能在上海聽到他執棒的慕尼黑愛樂樂團的精彩演出。
從貝多芬到馬勒,從序曲、協奏曲到交響曲,從古典到浪漫音樂經典的每一次精彩的現場演出都會讓人聯想到諸多的“音樂話題”,我想這或許就是古典音樂藝術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