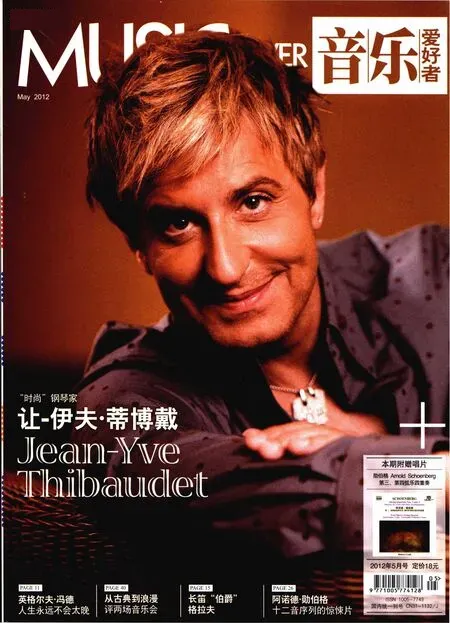愛樂隨筆兩則(十七)
劉蔚
穆洛娃的大氣與巴塞爾樂團的精致
2012年4月7日晚東方藝術中心瑞士巴塞爾樂團音樂會的上座率達到了九成,不可否認,攜團前來的俄羅斯小提琴家穆洛娃的號召力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然而,聽完整場音樂會,在贊嘆穆洛娃琴技高超的同時,我也要由衷地說一聲,巴塞爾樂團毫不遜色。
除了下半場的第一首樂曲是瑞士作曲家魯道夫創作的一部現代作品《為交響樂隊而作的四個樂章》以外,整場音樂會可以稱得上是一臺貝多芬作品專場。開場演奏貝多芬的《科里奧蘭》序曲作為暖場,小試身手之后,就是音樂會的重頭戲之一,由穆洛娃在巴塞爾樂團的協奏下演出貝多芬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
穆洛娃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奪得西貝柳斯國際小提琴比賽與柴科夫斯基國際小提琴比賽的頭獎,鋒芒初露。她在當時做的另一件轟動世界的事,就是出走蘇聯,前往美國避難,不久移居奧地利。穆洛娃還曾與指揮大師阿巴多相愛同居,并育有一子。當然,這些花邊新聞對一個藝術家來說都是“浮云”,她安身立命、在世界樂壇占有一席之地的畢竟是她的音樂造詣與藝術成就。因此,當身材修長、金發飄逸、一襲長裙的穆洛娃笑容滿面地走上東藝的舞臺時,全場聽眾報以熱烈的掌聲,便說明了中國樂迷對她琴藝的仰慕和期待。
穆洛娃一亮相果然出手不凡。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的第一樂章用的是協奏曲雙重呈示部的傳統寫法,小提琴通常是在樂隊的呈示部結束之后才進入,但穆洛娃一反常態,在樂隊呈示部結束前的若干小節就提前導入,令人耳目一新。等到她的獨奏聲部出現,那宏亮的琴音、從容自若的氣質立刻形成了一個氣場,吸引住了聽眾的注意力。穆洛娃師承俄羅斯一代小提琴巨匠柯岡,因此其藝術風格展露出地道的俄羅斯學派的印跡,演奏時上身基本不動,很少有美國學派慣有的五花八門的肢體動作,臺風穩健大氣,技術扎實,琴聲嘹亮凝練而又自然流暢,初聽略冷,細細回味之下,卻讓人感受到這位有“冰美人”之稱的小提琴家內心涌動的激情及其賦予音樂恰到好處的歌唱性。難怪友人感嘆:“果然名不虛傳,那位在阿姆斯特丹樂團音樂會上演出的荷蘭女小提琴家,炒作得厲害,但與穆洛娃相比根本不在一個檔次。”
下半場的第二部作品——貝多芬《第七交響曲》,則成了巴塞爾樂團與指揮喬萬尼·安東尼尼的表演時間。從節目單上看,該團的德語直譯應為巴塞爾室內樂團,演出“貝七”時,樂團的人數大約在四十人左右,的確是一支雙管編制的室內樂隊的規模。有意思的是,兩個圓號手使用的是沒有閥鍵的老式圓號,與我們通常見到的現代圓號不一樣,聲音古雅拙樸,參與全奏時稍顯吃力,難免使樂隊的音響效果有些損失;但另一方面,這可能正與巴塞爾樂團追求的室內樂化的演奏風格相一致,也成了該團的特色之一。
安東尼尼的指揮語言談不上漂亮,他那登山運動員般或者人體雕塑般拗造型的指揮動作,看著有些累人,然而正是他嚴謹細致的指揮牢牢地控制住了樂隊,樂隊奏出的輕、響、快、慢,層次分明,全奏的效果不亞于一個四管制的交響樂團,比如第二樂章“葬禮進行曲”從漸弱到漸強的那個著名的樂段,音響同樣氣勢磅礴,音色卻溫暖精致而富有彈性。第二、第三樂章中木管樂器的輪番演奏,鮮明悅耳,楚楚動人,亦展示了該團木管聲部不凡的實力。
音樂會結束后,與友人議論起了這樣一個話題:目前國內的一些交響樂團在編制上有盲目追求高、大、全的傾向,出來的音樂效果則是千篇一律的生、猛、粗、糙,甚至是亂。前些年,有個樂團去臺灣演出,在這方面就遭到了寶島音樂界毫不留情的批評。反觀巴塞爾樂團,不隨大流,而是有自己的定位,追求特色,這也許能為國內交響樂團的良性發展提供某種借鑒與啟示。
iPhone音樂之旅
清晨,行走在通往地鐵站的上班路上,我習慣性地拿出iPhone,戴上耳機,將白色的耳機線插進音孔,點開存在手機中的斯美塔那《伏爾塔瓦河》。頓時,長笛奏出了象征捷克母親河一個冰冷的源頭的旋律,小提琴的撥弦,仿佛是小溪在陽光的照耀下濺起的水花晶瑩閃爍,單簧管用它醇美的音色奏出的主題,象征這條河另一個溫暖的源頭,兩個源頭歡快地追逐,弦樂起伏宛如波浪,終于匯聚成了寬廣如歌、奔騰洶涌的伏爾塔瓦河。
《伏爾塔瓦河》縱情的歌唱讓我感到神清氣爽,昨夜殘存的睡意一掃而空。早春的晨風吹在臉上還有些冷意,然而,藍天相伴白云,街邊的梧桐樹已抽出嫩綠的新葉,預示著春天的來臨。我不禁加快腳步,走進了地鐵車站。
長期以來,用音響聽音樂早已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之一。工作之余的晚上,或者雙休日,在音響中放上一張唱片,邊聽邊看書,或者在電腦上寫點東西,是一件很愜意的事。本來,對于那么多人熱衷于用MP3、MP4,甚至在電腦中聽音樂,一直不以為然。古人彈奏古琴,品賞雅樂,講究焚香沐浴,凈心靜息,現代人聽樂當然不必如此,但那些東西的聲音效果怎么能跟音響媲美?所以對除音響之外的載體聽音樂,我基本上持排斥的態度。
直到不久前更換手機,買了iPhone,它大容量的內存,讓我意識到不能白白浪費,于是試著往里面儲存了自己喜歡的古典音樂。聽了之后發現, iPhone的音樂效果還不壞,雖然無法跟音響比,音質相對單薄,缺乏層次感,但聲音清晰,不刺耳。關鍵是,自從有了iPhone,原來那些碎片化的時間,比如上下班路上、乘地鐵、晚上散步,都可以利用起來,簡單隨意之間,變成獨有的聽樂時刻,平添了不少樂趣。
陸陸續續,我給iPhone中存了一百多部音樂作品,按照它的分類,有近五百段音樂。我發現在不同的時段欣賞這些音樂,可以收到不同的效果:早晨上班途中,一曲薩瑟蘭演唱的意大利歌曲《黎明》,華麗悅耳,節奏分明,仿佛晨露滴翠,鳥兒歌鳴,新鮮舒爽的氣息讓人精神為之一振,一天的工作有了好心情;舒伯特的《第九交響曲》,境界宏大,宛如漫漫長夜之后旭日初升,云開霧散,霞光披金,森林搖蕩,群峰起舞,心中塊壘驟然消散于無形,胸懷變得寬廣;當然,早晨聽得最多的還是莫扎特的音樂,小提琴協奏曲、鋼琴協奏曲、長笛協奏曲、歌劇序曲、嬉游曲,都可入耳。他的作品優美典雅,結構規整,非常適合行進時聆聽,而且明媚如陽光,清新如空氣,讓你感悟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傍晚下班,沐著落日余暉,乘上回家的地鐵,一天工作下來多少有些疲憊,情緒沉重激烈的大部頭音樂顯然不適宜。這時我喜歡聽夏布里埃的《西班牙狂想曲》、拉威爾的《波萊羅》、埃內斯庫的《羅馬尼亞狂想曲第二號》,此外,約翰·丹佛的鄉村歌曲《高高的落基山》《鄉村的路》《安妮之歌》,恩雅的《我的回家路》《非洲風暴》《樹的記憶》也是不錯的選擇,它們或熱情亮麗,或明快抒情,或空靈優雅,是緩解疲勞、放松身心的心靈按摩。
吃罷晚飯,照例會出去散步半小時到四十五分鐘。只見華燈齊放,霓虹閃亮,但街道上沒有了白晝的喧囂,萬物趨于寧靜。此時我會盡量選擇有林陰道的馬路行走,同時點開iPhone上的iPod,從播放列表中挑出我喜歡的貝多芬的交響曲、小提琴協奏曲、合唱幻想曲,勃拉姆斯的兩部鋼琴協奏曲,德沃夏克的“第八”“第九”交響曲以及西貝柳斯的作品,慢慢地走,細細地品味,隨大師們的樂思和旋律神游八荒。
科技改變生活,喬布斯的“蘋果”擴展了我們的愛樂方式。高科技原來并不是冷冰冰的,它的成功,是以人性化的手段,讓我們更加貼近藝術、貼近自然、貼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