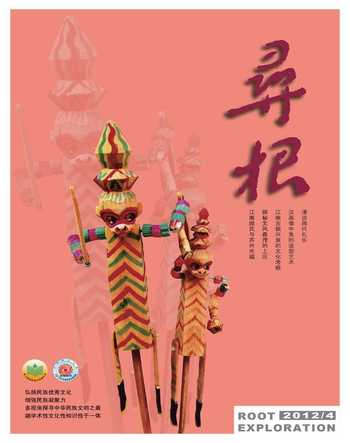《施耐庵墓志》之謎
陳傳坤
關于小說《水滸傳》的作者,從明代初年到現在,有四種說法。一是羅貫中獨立編撰;二是施耐庵、羅貫中合作完成;三是施耐庵自己創作的;四是當代學者提出來的,認為這是一部積累型小說,是經過民間藝人口頭加工、書商編纂整理、文人最后潤色而成的。
自上世紀30年代前后,隨著蘇北坊間陸續出現一些有關興化施彥端字耐庵并涉及《水滸傳》作者的文字資料,這個問題逐漸被人重視起來。到了上世紀50年代,蘇北文聯對蘇北這個施耐庵生平作了調查,并在《文藝報》上發表了《施耐庵生平調查報告》。跟著,劉冬、黃清江兩位先生在同期的《文藝報》上發表了《施耐庵與(水滸傳)》一文。從此,有關興化施彥端字耐庵問題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但是,因限于史料和文物證據之稀缺,迄今為止學界主偽派和認真派相互責難不已。其中,1951年發現的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興化縣續志》,因其載有《施耐庵墓志》,又把有關施耐庵其人其事的研究推向了高潮。但正因其提供了確切的施耐庵行狀之證據而備受反對方責難。下文即以《興化縣續志》所載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為論述主線,從其文本語源和典章故實等方面,鉤稽史料論證懷疑論者之妄說,揭橥該墓志之用語和典章故實并無違背其他文獻史料之處,佐證《施耐庵墓志》所述當無異議。
起源:施耐庵實有其人?
1928年11月8日,胡瑞亭在上海《新聞報》刊發了《施耐庵世籍考》一文,披露蘇北坊間流傳之“施耐庵墓志”,考訂施耐庵乃元末明初泰州白駒場(今江蘇興化、大豐)人,但可惜并沒有引發學人進一步探究的興趣。
1951年夏,《蘇北大眾報》負責人劉冬聽聞興化一帶有施耐庵遺跡,即安排同事黃清江實地查訪,勘察收獲了施耐庵神主、施耐庵墓碑以及民國《興化縣續志》中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等新材料。1952年9月,他們合寫《施耐庵與(水滸傳>》一文,刊于《文藝報》1952年第21號,旋即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1952年10月,文化部以聶紺弩為首的施耐庵調查組首次實地勘察取證,1953年調查組以徐放執筆撰寫了《再次調查有關施耐庵歷史資料的報告》。但是,該報告未能及時發表,而且經多次政治運動,輾轉秘藏,直到1985年12月才得以刊于《耐庵學刊》。
至1979年,江蘇興化縣新垛公社施家橋又發現施廷佐墓磚及銘文《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內有“口祖彥端”字樣。1981年10月29日,大豐縣大道公社和瑞大隊第五生產隊社員施俊杰獻出《施氏長門譜》(即《施氏家簿譜》),這個家譜為民國七年(1918年)手抄本,自始祖“彥端公字耐庵”起至18世孫止。一系列文字材料和文物的發掘問世,使得興化-施彥端-耐庵-《水滸傳》的證據鏈串聯了起來,使得小說《水滸傳》題署之施耐庵實有其人且興化施家橋施家為其后裔之論,呼之欲出。
1982年,時為江蘇省社科院文學所負責人的劉冬再次趕赴興化實地考察,在判定文物的真實性后撰文《施耐庵四世孫施廷佐墓志銘考實》,指出《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為“施耐庵確有其人的鐵證”。
隨后,劉冬以江蘇省社科院的名義邀請國內數位知名學者前往一同考察。但是始料不及的是,主偽方與認真方就此產生嚴重分歧,隨后掀起了一場源于興化而波及全球的“80年代施耐庵熱”。熱歸熱,但諸如施耐庵墓志等資料是否為現代人偽造等諸問題,最終仍未達成學界共識。
墓志文本的來源問題
溯本清源,要搞清《施耐庵墓志》的真偽,首先要搞清文物的來龍去脈,其次是搞清史料的來源。《施耐庵墓志》從何而來?還要追溯到民國《興化縣續志》的版本源流及其中有關施耐庵材料的來龍去脈。
《興化縣志》共五修,即嘉靖三十八年以前的胡志、萬歷十九年的歐志、康熙年間的張志、咸豐年間的梁志和民國三十二年的李志。前四種版本不見有施耐庵的材料,唯民國版李志,即《興化縣續志》,載錄有關施耐庵的信息有四處:
1.施隱士墓:卷一《輿地志·宅墓補遺》:在縣境東合塔圍內施家橋,葬元隱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
2.卷十三《文苑補遺》有《施耐庵傳》。
3.卷十四《藝文志·書目·小說家類》:《水滸》,施耐庵著。
4.卷十四《藝文志·古文補遺》有《施耐庵墓志》。
據文化部調查組報告,1918年前后,中央研究院特約著述員李詳(李審言)為續修《興化縣志》總纂,分纂人劉仲書,在白駒鎮見施氏宗祠供有施耐庵神主,并在施家橋借得《施氏家譜》,載有淮安王道生作的《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的《家傳》,便抄了下來,留作縣志的補遺。
1953年,徐放在一份調查報告中說:“我們在興化王益謙先生手,得到《興化縣續志》有關施耐庵的材料原稿兩份……原稿《施耐庵墓志》和《興化縣續志》上所載的原文是毫無出入的。”至于《興化縣續志》所載《施耐庵墓志》,與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所錄的文字存在略微差異問題,該調查報告認定胡瑞亭是興化縣倉庫文書,為調查戶口1928年在白駒施熊處抄去《施氏家譜》,據此撰文《施耐庵世籍考》;劉仲書是在1919年纂修縣志時于施家橋通過楊雨孫看到了《施氏家譜》上載的《施耐庵墓志》。由于胡瑞亭是供報紙發表的,文字有所節錄,遂致詳略之別。
而且該調查報告還引劉仲書的話:“至于《興化縣續志》中的《施耐庵墓志》上所說施耐庵‘生于元元貞丙申歲,‘歿于明洪武庚戌歲,都是照《施氏家譜》親筆抄錄的,不會錯。”徹底排除了《興化縣續志》上的《施耐庵墓志》據胡瑞亭增益的可能。
既然續志所載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文本材料來自《施氏家譜》,顯然家譜的版本及其來源至關重要。目前看來,除了蘇北文聯丁正華、蘇從麟1952年發現的《施氏總譜》有兩個版本外,1952年文化部調查組又訪得了六個《施氏支譜》和一個尚未公布的《施氏族譜世系》。1979年,興化施家橋施耐庵墓地附近又出土了施廷佐墓磚及《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經專家辨認,出土的墓志銘表明,在興化施家橋和大豐白駒鎮一帶,元末明初曾有一位施以謙之父、施廷佐之曾祖的施彥端。結合1952年文化部調查所見的施祥珠版本家譜,其中載錄的“施氏族譜世系”曰:“第一世:始祖諱彥端字耐庵行一,元至順辛未進士,高尚不仕,元末自蘇遷興后徙海陵白駒,因占籍焉。明洪武初,征書下至,堅辭不出,隱居著《水滸》自遣,孔門第五十七賢之常公之裔,葬于白駒鎮西北圩施家橋。”
施氏族譜中的“始祖諱彥端字耐庵行一,元至順辛未進士……隱居著《水滸》自遣”,與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記述的“公諱子安字耐庵……為至順辛未進士……先生之著作有……《江湖豪客傳》即《水滸》”等,足可相互印證。
墓志文本的語源
興化施彥端是否字耐庵,是否為《水滸傳》作者?30年來,凡是給出肯定答案的,其主要根據有四點:一、《施氏家譜》中“始祖彥端公”右側下旁注著“字耐庵”三字,且經江蘇省公安廳于1982年10月檢驗證實“‘字耐庵三字與《施氏家譜》字跡為同一個人所寫”,非后人妄添;二、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文本材料來自《施氏家譜》,而《施氏族譜》中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中有“先公耐庵……著《水滸》”字樣;三、出土的施廷佐墓磚指明施以謙之父、施廷佐之曾祖即施彥端,確認實有其人;四、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中也有“字耐庵”以及“著《江湖豪客傳》即《水滸》”字樣。
而質疑派主要是就族譜、墓磚銘文、縣志所錄墓志三者之間的聯絡關系發難。杭州師大馬成生質疑族譜的真實性:江蘇省公安廳所證實的“‘字耐庵三字與《施氏家譜》字跡為同一個人所寫”,只證實“字耐庵”三字是民國七年僧滿家手錄《施氏家譜》時的手跡,但是此三字究竟是僧滿家于何時添注上去的?不得而知。馬成生在質疑的文中還強調:1979年出土的墓磚銘文《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中,施廷佐是施彥端曾孫,然而,磚上刻著的也是“曾祖彥端”,并無“耐庵”字樣。此銘是出土文物,無疑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這,就使旁添的“字耐庵”三字“疑”上加“疑”了。
對此,歐陽健先生認為,滿家于民國七年出家為僧,特手錄《施氏家譜》以為紀念,故“字耐庵”三字為滿家所錄;而且,據1953年徐放考察報告稱,他們當時看到的幾本《施氏家譜》,在“字耐庵”處,該三字一律寫在行側,否定了后來填補的可能。
其他的質疑問題還有不少,下面就以墓志為起點,看看歷來質疑派都有哪些疑點,以及這些質疑是否成立。
針對《興化縣續志》載錄文本,質疑聲音層出不窮,試一一辨析。
1.關于墓志語源是否近代或清代以后用語的問題
“校對”一詞的出處,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著述·國學刻書》:“近年北監奏請重刊二十一史,陸續竣事,進呈御覽,可謂盛舉矣。而校對魯莽,訛錯轉多。”由此可知,“校對”一詞在明代萬歷時代已在使用,并非現代人的用語。
“水滸”稱謂的出處,明王圻《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傳記類》:“《水滸》者,羅貫著。貫字貫中,杭州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敘宋江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此外,許自昌《樗齋漫錄》卷六、錢希言《戲瑕》卷一,均曾提到《水滸》,錢氏還說“施氏《水滸》,蓋有所本耳”。由此可知,稱謂《水滸》一名,在明代嘉靖、萬歷時已廣泛使用。
2.關于字或號“子安”在譜內重名犯諱的問題
有人認為,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中“公諱子安,字耐庵”之“子安”——施子安,指的是家譜中第12代的“子安”,由此反證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顯系偽造。對此,歐陽健先生認為,子安應為施耐庵之名,彥端為尊號,由于這個名為當時人所罕知,所以其12世孫也恰巧取了同一個名,正如江陰祝塘梧塍《徐氏族譜》凡例云:“人既散處,聞問鮮通,其幼輩之犯尊諱及等輩之多復名,既難枚舉,有一字號而三四人共之。”而且,在《施氏家譜》中不同代亦有同名者,如第9世和第15世,均有“東來”可證。
3.關于“某即某”是否“現代人才有”的問題
墓志有“《江湖豪客傳》即《水滸》”字樣,為此,何心等質疑稱:“《江湖豪客傳》即《水滸》”等“不是明代人的口語,而是近代的口語”。有學者唱和道:“為何這個王道生提前六百多年便運用起來?”其實仔細探究,明代已有例證。如袁無涯《忠義水滸全書》“發凡”:
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復見;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損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舊本,移置閻婆事,甚善。其于寇而去王、田而加遼國,猶是小家照應之法。
由“郭武定本即舊本”可見,明代即有某即某的說法,此并非六百年之后的現代人才有的語言口吻。
關于施耐庵科第問題
此問題來源于墓志中“至順辛未進士”一句。李騫先生在《誰是(水滸傳>的作者》(《文學自由談》,2007年第4期)中質疑稱:
先說“至順辛未進士”,根據《元史·選舉志》記載,元朝開科選士一共進行了七次,分別是仁宗延祜二年、延祜五年;至治元年;泰定元年、泰定四年;天歷三年(元文宗至順元年,公元1330年);元統元年。
《元史》雖然是皇家修訂的,或許有很多不利于統治者的史料會被刪除,但是開科考試這樣無足輕重的事是斷不會漏記的,而且這七次考試是有一定規律性的,即每次科考相隔三年。王道生所說的“至順辛未進士”,是指施耐庵在公元1331年考取進士,這純屬奇聞,因為至順辛未這年元朝根本就沒有開科考試,施耐庵又怎么考取進士?
那么是不是王道生將“至順元年”誤為“至順辛未”?然而,至順元年的進士名單中并無施耐庵的蹤影。進士已屬天子門生,高中皇榜的人史書上應該不會有誤。
再看王道生的“曾官錢塘二載”說,錢塘就是現在的杭州。如果施耐庵在杭州做過官,哪怕是個不入流的小官吏,即使《元史》上沒有記錄,地方志上也應該有零星記載。但《浙江通志》《杭州府志》《錢塘縣志》等地方史書上,元代的大小官員名單中就沒有施耐庵或施子安其人。以此推論,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完全是無中生有、道聽途說的閉門造車,因為歷史上就沒有施耐庵其人。
那么,史料上究竟有沒有“至順二年辛未及第”之說呢?這個問題,此前學界一直沒有一個合理的解釋,故今天仍被很多質疑者反復提及。
歐陽健先生在博文《古代小說與人生體驗》,對這一問題作了探討。歐文稱,“元至順辛未二年進士”實際上確實沒有發生過,這就是《元史》不載的原因。但是《浙江通志》卻載錄“至順二年辛未”榜,這便是有名無實的“至順二年辛未余闕榜”疑案。《浙江通志》歷來被稱為佳志,學術價值、歷史價值極高,《四庫全書》即予以收錄。但是,該志卻載錄“至順二年辛未”榜。《四庫全書》中錢惟善《江月松風集》卷十二之《楊隱君挽詩》序亦有此說:
君諱亮,字明叔,上饒人。其子觀,登至順二年進士第,授饒州錄事,再授翰林檢閱而君卒,學士揭公志其墓。
同治版《廣信府志·隱逸傳》卷九十七《揭文安集》亦如此載錄楊觀故實:
上饒楊亮,字明叔,元高士也,與錢惟善為友。子觀,至順二年進士,為翰林檢閱。亮卒,錢惟善挽詩有“身入鳳濤親在念,恩沾雨露子登科”之句,載《江月松風集》。
此外,有人以施耐庵之名不見于《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為怪。據歐陽健先生考證,錢大昕《元進士考》載:元統元年(即至順四年)癸酉科進士百人,自周同、李齊、余闕,至虎理翰、張兌,共41人。其中,它包括《浙江通志》已錄為元統癸酉李齊榜的許廣大、錄為至順三年壬申的宇文公諒、錄為至順二年辛未余闕榜的劉基、葉峴,尚缺59人,楊觀、施耐庵不在其列,不足為異。
《浙江通志》中“至順二年辛未余闕榜”“至順二年進士”的存在,是史料呈現于世人面前的,證明了“至順二年辛未進士”之說確實存在,證實了施耐庵墓志所記述之“耐庵……為至順辛未進士”并非后人向壁虛構。總之,家譜以及續志所載《施耐庵墓志》為后人偽造說之立論,難以成立。
(本文承蒙歐陽健先生不吝指教并提供有關文獻、資料,特此鳴謝)
作者單位:阜陽日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