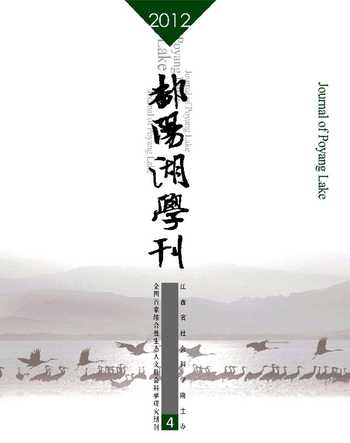生態(tài)環(huán)境多元共治模式的阻力因素分析
[摘要]在生態(tài)環(huán)境多元共治模式中,各治理主體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規(guī)則,當(dāng)生態(tài)環(huán)境問(wèn)題變得異常復(fù)雜,而彼此間的職責(zé)又不明確時(shí),會(huì)造成多元共治關(guān)系失效,給多元共治模式有效運(yùn)行帶來(lái)阻力。一般來(lái)說(shuō),構(gòu)建多元共治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模式,關(guān)鍵在于客觀公正地分析各個(gè)阻力因素的來(lái)源和強(qiáng)弱。
[關(guān)鍵詞]生態(tài)環(huán)境;多元共治模式;阻力因素
[中圖分類(lèi)號(hào)]D0-05[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hào)]1674-6848(2012)04-0095-07
[作者簡(jiǎn)介]田千山(1982—),男,苗族,湖南麻陽(yáng)人,中共韶關(guān)市委黨校黨建教研室講師、副主任,主要從事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研究。(廣東韶關(guān)512026)
[基金項(xiàng)目]廣東省黨校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規(guī)劃項(xiàng)目“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多元共治模式與運(yùn)行機(jī)制研究”(11GL04)的階段性成果。
一、問(wèn)題的提出
當(dāng)人們還在享受著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宏觀經(jīng)濟(jì)的快速增長(zhǎng)、物質(zhì)財(cái)富的巨大積累帶來(lái)的進(jìn)步之時(shí),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的問(wèn)題就像一把達(dá)摩克利斯的利劍一般高懸于頭頂。它以一種更為隱敝的方式對(duì)人類(lèi)的文明和生態(tài)系統(tǒng)構(gòu)成嚴(yán)重的存在性威脅。以1962年美國(guó)海洋生物學(xué)者雷切爾·卡爾遜(Rachel Carson,或譯為卡森)女士的著作《寂靜的春天》一書(shū)的出版為起點(diǎn),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日益成為一門(mén)“顯學(xué)”,研究者眾多,成果也頗豐。相比于國(guó)外,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問(wèn)題的研究起步較晚,但也不乏一些精品力作。由于學(xué)者們的理論基礎(chǔ)與研究視角存在差異,使得研究結(jié)論也不盡相同,但“多元共治”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模式顯然已在學(xué)術(shù)界達(dá)成共識(shí)。所謂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多元共治模式,是指政府、市場(chǎng)、公眾及社會(huì)其他主體能充分發(fā)揮各自?xún)?yōu)勢(shì),采取分工、合作、協(xié)商等方式解決生態(tài)環(huán)境問(wèn)題的全過(guò)程。其中,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多元主體治理如何有效整合、協(xié)調(diào)聯(lián)動(dòng)、并形成合力,成為提高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績(jī)效的關(guān)鍵。然而,在理論上認(rèn)為切實(shí)可行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多元共治模式,在實(shí)踐層面卻舉步維艱,兩者嚴(yán)重脫節(jié)。因此,我們有必要深入分析究竟是什么樣的阻力因素導(dǎo)致這一結(jié)果,以便通過(guò)建立一套相對(duì)完善的運(yùn)行機(jī)制,減少阻力的制約,使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多元共治模式得以順利推行并富有成效。
二、阻力因素分析
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多元共治模式,得益于政府、市場(chǎng)、社會(huì)等治理主體間的協(xié)商合作。但治理主體多元也意味著利益多元,因?yàn)槊恳粋€(gè)治理主體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規(guī)劃;加之生態(tài)環(huán)境問(wèn)題本身就復(fù)雜異常,特別是對(duì)于一些跨行政區(qū)域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問(wèn)題,由于職責(zé)不明確,往往造成多元主體間協(xié)商合作關(guān)系的失調(diào)、失效,反而給多元共治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模式帶來(lái)阻力和障礙。一般而言,這些阻力主要來(lái)自多元治理主體之間(如府際間、政企間、政社間等)的利益博弈,來(lái)自多元治理主體間的信息障礙,以及多元治理主體在合作過(guò)程中出現(xiàn)的治理結(jié)構(gòu)失效和本身的制度滯后等。
(一)利益博弈
生態(tài)環(huán)境問(wèn)題的有效治理其實(shí)也是公共利益的實(shí)現(xiàn)過(guò)程,而公共利益不可能由單一的主體來(lái)代表和界定。因此,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治理主體必然要求是多元化的。這些多元化的治理主體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如果不能有效協(xié)調(diào)各主體間的關(guān)系,會(huì)導(dǎo)致它們以自我利益為中心展開(kāi)博弈。
1.府際間的利益博弈
“府際關(guān)系”是指“國(guó)內(nèi)各級(jí)政府間和各地區(qū)政府間的關(guān)系,它包含縱向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關(guān)系、地方各級(jí)政府間關(guān)系和橫向的各地區(qū)政府間關(guān)系。”①基于這一認(rèn)識(shí),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中,府際間的利益博弈主要體現(xiàn)為以下兩種:一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目前,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已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命令—服從”關(guān)系,而是代表不同利益的博弈主體,盡管彼此間的目標(biāo)存在一致性,但差異性也不可避免。這是因?yàn)椋胤秸谏鷳B(tài)環(huán)境治理中的態(tài)度相對(duì)中央政府來(lái)說(shuō)要復(fù)雜得多。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力圖實(shí)現(xiàn)區(qū)域利益的最大化,經(jīng)濟(jì)發(fā)展自然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是中央政策的貫徹執(zhí)行者,對(duì)于中央所強(qiáng)調(diào)的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的全局性、發(fā)展與環(huán)境的協(xié)調(diào)性等問(wèn)題,表現(xiàn)出極度的糾結(jié)心理,往往一些地方會(huì)以獲取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為行動(dòng)指南。二是各地區(qū)政府間的利益博弈。由于行政區(qū)域的劃分,使得一些結(jié)構(gòu)復(fù)雜、范圍廣闊的環(huán)境資源(如森林、河流等)被人為地分割,并實(shí)施行政區(qū)域?qū)俚毓芾怼娜珖?guó)范圍來(lái)看,任何地方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的有效進(jìn)行都意味著國(guó)家整體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的提升。但在地方政府層面則不盡然,因?yàn)橄鄬?duì)于鄰近地區(qū),本地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治理效應(yīng)存在溢出的可能,從成本角度考慮,其理性的選擇就是減少該公共產(chǎn)品的供給。
2.政企間的利益博弈
當(dāng)企業(yè)處于一個(gè)沒(méi)有政府監(jiān)管、市場(chǎng)高度自由的環(huán)境下,企業(yè)對(duì)于其自身所造成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污染問(wèn)題可以選擇治理或不治理,且選擇不治理的可能性最大。因?yàn)椋髽I(yè)以獲取利潤(rùn)最大化為永恒的目標(biāo),而治理生態(tài)環(huán)境污染問(wèn)題需增加企業(yè)的生產(chǎn)成本,且這種行為是長(zhǎng)期性和正外部性的,長(zhǎng)此以往,企業(yè)將失去產(chǎn)品在市場(chǎng)上競(jìng)爭(zhēng)的價(jià)格優(yōu)勢(shì),甚至導(dǎo)致企業(yè)破產(chǎn)。這就為政府的干預(yù)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而一旦政府對(duì)企業(yè)進(jìn)行污染治理的責(zé)任實(shí)施監(jiān)督并采取相應(yīng)的措施對(duì)其行為進(jìn)行“矯正”時(shí),政府與企業(yè)間的監(jiān)管與成本博弈就開(kāi)始了。一般情況下,企業(yè)會(huì)擔(dān)憂(yōu)治污成本的高昂,擔(dān)心隱瞞排污量被發(fā)現(xiàn)后的社會(huì)成本;而政府也會(huì)考慮強(qiáng)制企業(yè)治污后的收益。當(dāng)政府疏于監(jiān)控或企業(yè)自身感覺(jué)到治污成本較高時(shí),企業(yè)一般會(huì)采取置之不理或降低治污標(biāo)準(zhǔn)來(lái)予以應(yīng)付;而此時(shí)政府也會(huì)針對(duì)企業(yè)這一行為適時(shí)調(diào)整策略加以應(yīng)對(duì)(如提高處罰額度甚至強(qiáng)制關(guān)停),企業(yè)則會(huì)再次以減少排污量或增加治污成本進(jìn)行妥協(xié),甚至直接行賄政府官員……如此反復(fù)博弈,直至政府與企業(yè)間找到平衡點(diǎn)。
3.政社間的利益博弈
新中國(guó)成立后的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存在“以政代社”、“以政管社”的政社不分現(xiàn)象,不可否認(rèn),這種社會(huì)管理體制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對(duì)于鞏固新生的政權(quán)、加快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步伐等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改革開(kāi)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隨著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不斷建立與完善,傳統(tǒng)社會(huì)管理體制的弊端也日益顯現(xiàn)。為此,“政社分離”就成為適應(yīng)當(dāng)前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必然要求。在生態(tài)環(huán)境領(lǐng)域,近年來(lái)環(huán)保組織的增速較快,據(jù)中華環(huán)保聯(lián)會(huì)發(fā)布的《中國(guó)環(huán)保NGO藍(lán)皮書(shū)》顯示,截至2008年10月,全國(guó)共有環(huán)保民間組織3539家,其中:由政府發(fā)起成立的環(huán)保組織1309家,學(xué)校社團(tuán)組織1382家,草根的環(huán)保組織有508家,國(guó)際環(huán)保組織駐中國(guó)的機(jī)構(gòu)有90家。①有關(guān)專(zhuān)家預(yù)測(cè),今后民間環(huán)保組織數(shù)量和參與人數(shù)將以每年10%至15%速度遞增。②這些環(huán)保組織以保護(hù)生態(tài)環(huán)境為宗旨,不以營(yíng)利為目的,不具備行政權(quán)力。在面對(duì)政府治理生態(tài)環(huán)境中的無(wú)為、無(wú)效行為時(shí),若單憑公民個(gè)體的力量去同政府交涉,其結(jié)果可想而知;而公民一旦結(jié)成擁有專(zhuān)業(yè)人士和先進(jìn)技術(shù)以及一定經(jīng)濟(jì)實(shí)力和社會(huì)影響力的社會(huì)環(huán)保組織時(shí),它們就有實(shí)力同侵權(quán)者平等對(duì)話(huà),并圍繞維護(hù)組織成員的合法權(quán)益開(kāi)展工作,從而在某種程度上矯正強(qiáng)弱兩者實(shí)力失衡的狀態(tài)。
(二)信息障礙
信息通暢是實(shí)現(xiàn)多元共治的各主體間彼此有效溝通與整合的前提條件,但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中,由于政府與企業(yè)往往會(huì)從各自利益的角度出發(fā),人為地制造一些信息公開(kāi)不透明、傳輸渠道不暢通的問(wèn)題,造成各治理主體間存在信任危機(jī),進(jìn)而制約并妨礙生態(tài)環(huán)境多元共治模式的順利進(jìn)行。
1.信息公開(kāi)不透明
信息公開(kāi)是指政府和各種組織機(jī)構(gòu)向社會(huì)公開(kāi)或開(kāi)放自己所擁有的信息,使其他組織機(jī)構(gòu)和社會(huì)可以以任何正當(dāng)?shù)睦碛珊捅M可能簡(jiǎn)便的方法獲得上述信息。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領(lǐng)域,環(huán)境信息公開(kāi)的主體無(wú)外乎政府與企業(yè),其透明的程度可以說(shuō)是多元共治模式得以有效運(yùn)行的關(guān)鍵性因素。我國(guó)信息公開(kāi)尚處于起步階段,還存在諸多需要改進(jìn)的地方。首先,是政府在信息公開(kāi)時(shí)的不透明性。政府作為生態(tài)環(huán)境信息的制作者、管理者和法律授權(quán)的權(quán)威發(fā)布者,其地位是其他任何組織和團(tuán)體無(wú)可比擬的。正因如此,政府往往以掌控信息的“主人”自居,將是否發(fā)布信息視為一種權(quán)力,而不是當(dāng)成義務(wù)來(lái)履行。特別是一些官員錯(cuò)誤地理解“公開(kāi)為原則、不公開(kāi)為例外”的精神,有意將“例外”的范疇擴(kuò)大化,造成權(quán)威信息源的“空白”。其次,是企業(yè)在信息公開(kāi)時(shí)的不透明性。企業(yè)既是社會(huì)財(cái)富的主要締造者,也是自然資源的主要消耗者,還是環(huán)境污染物的主要生產(chǎn)者。據(jù)統(tǒng)計(jì),目前生態(tài)環(huán)境遭受的污染中有80%來(lái)自于企業(yè)。可以說(shuō),企業(yè)對(duì)于生態(tài)環(huán)境問(wèn)題有著不可推卸的責(zé)任,理應(yīng)將其生產(chǎn)流程、相關(guān)技術(shù)、排污情況、污染物的危害等方面信息公之于眾。然而,無(wú)論是出于自愿或是被迫,企業(yè)常常逃避環(huán)境信息公開(kāi),逃避承擔(dān)環(huán)境責(zé)任,都是從自身營(yíng)利性的角度考慮,從而造成政府與社會(huì)無(wú)法全面了解企業(yè)的真實(shí)情況。
2.傳輸渠道不暢通
作為各治理主體間相互發(fā)送與接收信息的媒介物,傳輸渠道是否健全通暢是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問(wèn)題進(jìn)行準(zhǔn)確監(jiān)測(cè)、預(yù)防、快速反應(yīng)和及時(shí)控制的前提條件,決定著多元共治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模式的運(yùn)行質(zhì)量與治理效果。當(dāng)前,傳統(tǒng)的信息傳輸渠道如報(bào)紙、廣播、電視、展覽會(huì)等形式依然是政府、企業(yè)、社會(huì)間傳輸信息的主渠道,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我們也要看到,這種傳統(tǒng)的信息傳輸模式是以單向垂直傳輸為主要特點(diǎn),是一種以行政性命令為表述的自上而下的單向傳輸,其缺陷也在于以政府為主的單調(diào)信息來(lái)源難以形成覆蓋全社會(huì)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信息網(wǎng)絡(luò),缺乏信息反饋渠道。此外,現(xiàn)有的人民代表大會(huì)和中國(guó)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等制度性渠道,由于渠道單一、渠道擁擠等問(wèn)題,嚴(yán)重阻礙并降低了有用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信息的傳輸質(zhì)量和傳輸速度。加之等級(jí)森嚴(yán)的科層體制使生態(tài)環(huán)境信息的傳輸環(huán)節(jié)相對(duì)繁瑣,特別是某些官員基于績(jī)效考核利己因素的考慮,往往人為地制造一些信息傳輸渠道不暢的問(wèn)題。
同時(shí),由于缺乏專(zhuān)門(mén)的機(jī)構(gòu)和人員來(lái)管理生態(tài)環(huán)境信息,沒(méi)能從宏觀層面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相關(guān)信息進(jìn)行專(zhuān)門(mén)加工,造成生態(tài)環(huán)境信息在收集、分析、處理、傳遞、反饋和評(píng)估等方面,存在人員機(jī)構(gòu)不到位、責(zé)任分工不明確、操作行為不規(guī)范等問(wèn)題,因而加大了各治理主體間溝通和協(xié)商的成本,加劇了生態(tài)環(huán)境信息分析評(píng)估數(shù)據(jù)的科學(xué)性和真實(shí)性的風(fēng)險(xiǎn),成為影響生態(tài)環(huán)境信息高效傳輸?shù)挠忠恢匾蛩亍kS著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飛速發(fā)展,各治理主體本可充分利用原有的和新的信息傳輸媒介拓展自有的信息渠道,為生態(tài)環(huán)境信息的順暢傳輸提供便利,為各治理主體獲得便捷的信息打下良好基礎(chǔ)。但是,部分環(huán)保網(wǎng)站平臺(tái)在建立之后,普遍存在維護(hù)不夠、投入不足、更新不快等問(wèn)題,特別是一些網(wǎng)站建設(shè)質(zhì)量本身就不高、定位不準(zhǔn)確、信息分類(lèi)較混亂、兼容性差,造成人們?cè)谒阉飨嚓P(guān)信息時(shí)會(huì)耗費(fèi)大量時(shí)間,甚至出現(xiàn)頁(yè)面瀏覽錯(cuò)誤、亂碼或無(wú)法正常連接等。當(dāng)然,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水平、公眾受教育程度、企業(yè)的態(tài)度等也是造成各治理主體間“信息鴻溝”不斷加大的阻力因素。
(三)結(jié)構(gòu)失效
在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多元共治模式中,結(jié)構(gòu)為多元治理主體的協(xié)作提供了平臺(tái),其有效與否,將對(duì)多元共治格局的構(gòu)建產(chǎn)生最直接的影響。所謂結(jié)構(gòu),“是由各種相互關(guān)聯(lián)而又相互作用的角色構(gòu)成的”。①此處的“角色”一詞,其涵蓋的意思決不單指多元共治主體那么簡(jiǎn)單,更為重要的是,它強(qiáng)調(diào)了這些主體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中的實(shí)際作為。結(jié)構(gòu)失效,即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中,各治理主體間的聯(lián)系與互動(dòng)非但沒(méi)有形成動(dòng)力,反而造成阻力,成為多元共治功能發(fā)揮的嚴(yán)重障礙。
1.決策效率低下
治理生態(tài)環(huán)境問(wèn)題的相關(guān)決策,一般都是在掌握有限資源(如生態(tài)環(huán)境信息、人力、財(cái)力、物力)的條件下,通過(guò)對(duì)多種備選方案進(jìn)行分析判斷和選擇決斷的基礎(chǔ)上作出的。在生態(tài)環(huán)境多元共治模式下,政府不再是向社會(huì)提供生態(tài)環(huán)境公共產(chǎn)品和公共服務(wù)的唯一權(quán)力中心,企業(yè)和社會(huì)組織只要能夠得到社會(huì)公眾的認(rèn)可,均有機(jī)會(huì)成為提供該產(chǎn)品和服務(wù)的權(quán)力中心。這一多元共治的結(jié)構(gòu)也正是一個(gè)滿(mǎn)足多種公共需求的組織架構(gòu),它的有效運(yùn)行得益于社會(huì)中多元的治理主體基于一定的集體行動(dòng)規(guī)則,通過(guò)相互博弈、相互調(diào)適、相互協(xié)作等互動(dòng)關(guān)系,形成多元化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制度和組織模式。盡管在理論上,我們尋求通過(guò)多元治理主體的良性耦合使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取得大于單要素之和的結(jié)果,即實(shí)現(xiàn)“1+1>2”;但由于社會(huì)公眾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進(jìn)一步惡化的恐懼,以及對(duì)其在短期內(nèi)有所改善的期待,使得多元治理主體在作出相應(yīng)決策時(shí),易受到來(lái)自決策體系內(nèi)外部時(shí)間短、資源少的雙重壓力,最終限入“團(tuán)體迷思”的困境。“所謂團(tuán)體迷思,指團(tuán)體在決策過(guò)程中,由于成員傾向讓自己的觀點(diǎn)與團(tuán)體一致,因而令整個(gè)團(tuán)體缺乏不同的思考角度,不能進(jìn)行客觀分析。”①這種“團(tuán)體迷思”對(duì)于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多元共治模式而言,是一種嚴(yán)重的共識(shí)性危機(jī),要么導(dǎo)致各治理主體間無(wú)法作出有效的決策,要么導(dǎo)致各治理主體共同作出不合理甚至錯(cuò)誤的決策,進(jìn)而嚴(yán)重影響到多元共治結(jié)構(gòu)的決策效率。
2.對(duì)立性沖突頻發(fā)
在由生態(tài)環(huán)境多元共治模式的治理結(jié)構(gòu)中,企業(yè)、環(huán)保組織和社會(huì)公眾等不再僅僅被當(dāng)做政府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中的工具來(lái)使用,不再只滿(mǎn)足于被動(dòng)地消費(fèi)公共產(chǎn)品和接受公共服務(wù),而是要求參與到生態(tài)環(huán)境問(wèn)題的治理過(guò)程中去,并且在多元共治中實(shí)現(xiàn)自由全面發(fā)展。與此同時(shí),政府開(kāi)始明白不能繼續(xù)將整個(gè)世界視為對(duì)象,而是應(yīng)該當(dāng)做自己的合作伙伴。于是,企業(yè)、環(huán)保組織和社會(huì)公眾等逐漸從支配性關(guān)系中走出來(lái),享有與政府同等的地位,形成多元化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共同體。多元化治理主體的存在,也就意味著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中,各治理主體的專(zhuān)門(mén)化和自主化程度得到日益增強(qiáng)。正因如此,若按照形形色色的分化標(biāo)準(zhǔn)將其加以區(qū)分,會(huì)因?yàn)閰⑴c治理主體的越來(lái)越多而造成它們分化程度越來(lái)越高的局面,最終出現(xiàn)協(xié)調(diào)各治理主體間活動(dòng)的問(wèn)題變得越來(lái)越復(fù)雜。就政府而言,在其系統(tǒng)內(nèi)部結(jié)構(gòu)的運(yùn)行上,部門(mén)分割和條塊沖突等問(wèn)題會(huì)對(duì)多元共治的效果產(chǎn)生一系列負(fù)面影響,如部門(mén)之間的協(xié)作關(guān)系不明朗,條塊的職責(zé)劃分較為模糊等,造成實(shí)踐中時(shí)常出現(xiàn)條塊行動(dòng)銜接配合不夠、協(xié)調(diào)困難等問(wèn)題。與此同時(shí),政府與其他治理主體之間的職責(zé)分工也不甚明確,政府過(guò)多地干預(yù)其他治理主體在解決生態(tài)環(huán)境問(wèn)題中的工作,難以形成良性的多元共治格局。
3.結(jié)構(gòu)穩(wěn)定性擔(dān)憂(yōu)
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變的事物,多元共治結(jié)構(gòu)也是如此。多元共治穩(wěn)定性的結(jié)構(gòu)主要是指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中,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合作共治關(guān)系能夠長(zhǎng)期維持。但在外界環(huán)境不斷發(fā)生變化的今天,這種多元共治的結(jié)構(gòu)也將適時(shí)進(jìn)行相應(yīng)的調(diào)整。例如,政府與環(huán)保組織之間,政府受理性經(jīng)濟(jì)人的影響,且政府決策者可能會(huì)被少數(shù)人的利益訴求所左右,致使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中出現(xiàn)“政府失靈”現(xiàn)象。除了在少數(shù)時(shí)候會(huì)通過(guò)公民投票方式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進(jìn)行表決外,一般都是由少數(shù)社會(huì)精英(或政府官員、或公民代表)代表社會(huì)公眾作出決策。如果對(duì)這些社會(huì)精英沒(méi)有足夠的監(jiān)督,就可能出現(xiàn)忽視甚至損害大多數(shù)人利益的情況。而環(huán)保組織也由于需要國(guó)家為其功能的實(shí)現(xiàn)提供必要的社會(huì)條件,即通過(guò)經(jīng)濟(jì)發(fā)展為其提供資金,完善法律為其提供向?qū)В睒s文化為其提供支撐,因而過(guò)分依賴(lài)政府救濟(jì),造成獨(dú)立性的嚴(yán)重不足。在多元共治結(jié)構(gòu)中,政府與環(huán)保組織間相互依賴(lài)關(guān)系日益密切,一旦一方發(fā)生變故,導(dǎo)致治理不得力,那么彼此之間的合作互動(dòng)關(guān)系也將面臨破裂,進(jìn)而加劇社會(huì)對(duì)多元共治結(jié)構(gòu)穩(wěn)定性的擔(dān)憂(yōu)。
(四)制度滯后
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制度的存在與否、質(zhì)量的高低對(duì)人們政治生活和社會(huì)生活的方方面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中,也需要制度的規(guī)范和約束才能保證其正常運(yùn)行和發(fā)揮效用。但是,現(xiàn)有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多元共治模式的發(fā)展態(tài)勢(shì)。這里的“制度”,既包括了正式制度正效應(yīng)的發(fā)揮和建設(shè)滯后所導(dǎo)致的“盲區(qū)”,也涵蓋了非正式制度(即“潛規(guī)則”)負(fù)效應(yīng)的散發(fā)。
1.正式制度效用不足
正式制度包括從中央到地方制定頒布的有關(guān)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的法律、法規(guī)和規(guī)章,它們是保證生態(tài)環(huán)境多元共治模式作用有效發(fā)揮的基本前提,其主要特征在于以國(guó)家強(qiáng)制力為后盾來(lái)保證這些法律法規(guī)的實(shí)施。但是,目前我國(guó)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的法律法規(guī)體系建設(shè)相對(duì)滯后,影響了多元共治模式的推進(jìn)。
在立法方面,相關(guān)法律缺乏配套的實(shí)施細(xì)則,現(xiàn)有法律關(guān)于各治理主體的法律責(zé)任的規(guī)定并不明確。改革開(kāi)放后,我國(guó)逐步確立了在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前提下兼顧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的立法思想,經(jīng)過(guò)多年的努力,已經(jīng)建立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環(huán)境保護(hù)法》為基礎(chǔ),以各單項(xiàng)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法律為主體,并以生態(tài)環(huán)境法規(guī)、規(guī)章、標(biāo)準(zhǔn)和國(guó)際性條約為重要組成部分的法律體系和政策體系。但這些法律政策更多地是建立在與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相適應(yīng)的基礎(chǔ)上,環(huán)境保護(hù)的意識(shí)尚差,相關(guān)法律制度很不完善。盡管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在今天已經(jīng)建立并不斷完善,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的主體也已呈多元化的趨勢(shì),但與之相應(yīng)的立法卻依然遵循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原則,忽視了其先導(dǎo)性,許多法律條文明顯滯后,甚至與現(xiàn)實(shí)脫節(jié),在解決新情況、新問(wèn)題時(shí)往往造成無(wú)法可依。例如,對(duì)于污染源之一的工業(yè)污染,目前已有大量的法律法規(guī)在加以控制,但像農(nóng)業(yè)污染和生活污染等這些過(guò)去沒(méi)有顯現(xiàn)的污染因素,隨著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危害日益突顯,卻因缺乏應(yīng)有的法律法規(guī)而對(duì)此無(wú)所適從。
在執(zhí)法方面,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不統(tǒng)一導(dǎo)致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工作缺乏統(tǒng)一與協(xié)調(diào),不利于構(gòu)建多元共治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格局。當(dāng)前,我國(guó)針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的執(zhí)法能力與水平較過(guò)去有了較大的提高,但執(zhí)法隊(duì)伍人員少、裝備差、監(jiān)控手段落后、運(yùn)轉(zhuǎn)經(jīng)費(fèi)難保障等問(wèn)題卻依然是導(dǎo)致監(jiān)督管理不力的軟肋。特別是在治理生態(tài)環(huán)境問(wèn)題的執(zhí)法過(guò)程中,若要確保法律的有效實(shí)施,必以法的嚴(yán)肅性(權(quán)威性)為前提。但多元共治的各主體卻由于缺乏行政強(qiáng)制權(quán)(如查封、凍結(jié)、扣押、沒(méi)收、強(qiáng)制劃撥等),使得它們?cè)诿鎸?duì)層出不窮的違法行為時(shí)常感到力不從心或束手無(wú)策,難以有效地進(jìn)行監(jiān)督管理。
2.“潛規(guī)則”大行其道
非正式制度是指各治理主體在參與治理生態(tài)環(huán)境問(wèn)題的實(shí)踐中無(wú)意識(shí)形成的并被彼此遵守的各種行為規(guī)則,包括傳統(tǒng)習(xí)慣、行為準(zhǔn)則、倫理道德和意識(shí)形態(tài)等。非正式制度的產(chǎn)生時(shí)間要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正式制度,因?yàn)橹灰腥伺c人之間的合作關(guān)系存在,就必然依賴(lài)非正式制度,而正式缺席卻是在國(guó)家和政府出現(xiàn)之后才誕生的。當(dāng)然,并不是有了正式制度以后非正式制度就自然消失,盡管當(dāng)前的正式制度已經(jīng)林林種種,但也只是作為規(guī)范人與人之間合作關(guān)系的一部分,并非全部更不可能是唯一。從這一意義上說(shuō),正式制度的出現(xiàn)是非正式制度的支持與補(bǔ)充,兩者間的親和力越強(qiáng),就越容易被人們所遵守、實(shí)施,反之則導(dǎo)致正式制度的普遍失效與無(wú)力。
對(duì)于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而言,真正能夠讓多元共治效果得以充分發(fā)揮的制度恰恰是被生態(tài)環(huán)境組織、社會(huì)公眾等治理主體一致認(rèn)同,并早就相互約定俗成的規(guī)定。而單單依賴(lài)國(guó)家的強(qiáng)制性權(quán)力才得以實(shí)施的法律制度,無(wú)論其在理論上有多成熟,表現(xiàn)得多公正,也逃脫不了失敗的結(jié)局。正如哈耶克所言:在一個(gè)傳統(tǒng)和慣例使人們的行為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可以預(yù)期的社會(huì)中,強(qiáng)制力可降低到最低限度。也就是說(shuō),真正促進(jìn)生態(tài)環(huán)境多元共治模式效用發(fā)揮的是非正式制度,而它也應(yīng)當(dāng)存在于各個(gè)治理主體的合作關(guān)系中,并且是理所當(dāng)然、無(wú)可厚非的。
不可否認(rèn),正式制度也許會(huì)通過(guò)特定的手段對(duì)非正式制度進(jìn)行變更、修正甚至消除,但對(duì)于非正式制度的改變卻是一個(gè)漫長(zhǎng)的過(guò)程,而非一時(shí)之所能。比如,當(dāng)政府過(guò)分地強(qiáng)調(diào)“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并采取極端的手段加以控制時(sh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觀念肯定會(huì)讓人們通過(guò)規(guī)避法律或不遵守的形式予以直接或間接的抵制與拒絕。誠(chéng)然,這種非正式制度也不可無(wú)限放大,當(dāng)它成為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中得到廣泛遵從的規(guī)矩,并背離公平正義的觀念,甚至侵犯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或正式制度所代表的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時(shí),就會(huì)嚴(yán)重影響到正式制度效力的發(fā)揮,使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中的多元共治模式偏離甚至脫離正常的運(yùn)行軌道,嚴(yán)重阻礙其發(fā)展進(jìn)程。①
三、結(jié)論
有效構(gòu)建并運(yùn)行多元共治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模式,關(guān)鍵在于能客觀地分析各個(gè)阻力因素的來(lái)源與強(qiáng)弱,“協(xié)作的需要源于參與者的相互依賴(lài),因?yàn)槊總€(gè)參與者擁有完成一項(xiàng)任務(wù)所需的不同類(lèi)型和不同層次的技術(shù)和資源”。②縱觀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多元共治模式,其合作共治主要包括兩個(gè)方面的問(wèn)題:一個(gè)是各治理主體的自身建設(shè)問(wèn)題;另一個(gè)是各治理主體間的互動(dòng)銜接問(wèn)題。推進(jìn)生態(tài)環(huán)境多元共治模式真實(shí)效用的發(fā)揮,必須以解決上述兩方面問(wèn)題為切入點(diǎn),不斷促進(jìn)各治理主體間的正和博弈,優(yōu)化共治組織結(jié)構(gòu),實(shí)現(xiàn)生態(tài)環(huán)境信息的彼此共享,強(qiáng)化制度建設(shè)。總之,構(gòu)建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多元共治模式,其格局的形成必須要以客觀公正地界定各治理主體的權(quán)力和責(zé)任為前提,通過(guò)制度的建立健全和組織結(jié)構(gòu)的創(chuàng)新等方式,在各治理主體間不斷確立以權(quán)力和權(quán)利互動(dòng)為主的合作共治關(guān)系,以政府的改革、組織的壯大、公眾的覺(jué)醒、市場(chǎng)的完善為發(fā)展動(dòng)力,提升合作共治能力,強(qiáng)化合作紐帶,避免因多元治理主體間的不合作、不協(xié)調(diào)導(dǎo)致甚至加劇生態(tài)環(huán)境問(wèn)題的進(jìn)一步惡化。
①林尚立:《國(guó)內(nèi)政府間關(guān)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頁(yè)。
①《中國(guó)環(huán)保NGO爭(zhēng)議中快速發(fā)展面臨注冊(cè)無(wú)門(mén)窘境》,中國(guó)新聞網(wǎng),http://www.china news. com/gn/2011/05-07/3023593.shtm1.
②《環(huán)保民間組織數(shù)量和人數(shù)將以10%至15%速度遞增》,新華網(wǎng),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28/content_5261315.htm.
①(美)加布里埃爾·A. 阿爾蒙德、小G. 賓厄姆·鮑威爾:《比較政治學(xué):體系、過(guò)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頁(yè)。
①夏美武、趙軍鋒:《危機(jī)管理中多元協(xié)作的動(dòng)力與阻力分析》,《江海學(xué)刊》2011年第6期。
①朱義坤:《公司治理制度的多元結(jié)構(gòu)》,《暨南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1998年第4期。
②(美)羅伯特·阿格拉諾夫、邁克爾·麥圭爾:《協(xié)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戰(zhàn)略》,李玲玲、鄞益奮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頁(yè)。
責(zé)任編輯: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