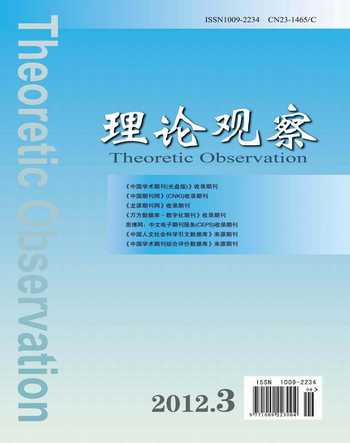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中國美術(shù)變革的特點(diǎn)和社會(huì)功能性
陸璐
[摘要]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這一革命的時(shí)代,“革命”無論對于政治、社會(huì)制度還是對于文學(xué)、美術(shù)都是勢在必行的時(shí)代趨勢,以東西方美術(shù)交融為特征的中國美術(shù)變革,徹底結(jié)束了千年來文人畫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主張美術(shù)變革的代表人物,都不約而同的提倡走融合中西之路徑,取長補(bǔ)短,同時(shí)他們心懷國族意識(shí)和時(shí)代使命感,期望中國繪畫無論從思想上和內(nèi)容上,還是技巧與技法和其表現(xiàn)形式上都煥然一新。他們對中國畫變革所作出的努力為日后新世紀(jì)中國畫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xiàn),使得后來人可以從中得到吸收和借鑒。
[關(guān)鍵詞]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美術(shù);變革;社會(huì)功能
[中圖分類號(hào)]J05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文章編號(hào)] 1009 — 2234(2012)03 — 0119 — 03
一、美術(shù)功能性簡述
美術(shù)屬于藝術(shù)范疇。藝術(shù)的產(chǎn)生是由人的特殊需要制約的,那么藝術(shù)的需要?jiǎng)t規(guī)定了它的某些特殊功能,藝術(shù)的功能就像對藝術(shù)本身的需要一樣,是先于藝術(shù)而存在的。美術(shù)是藝術(shù)分支的重要一支,美術(shù)的產(chǎn)生也是由人們的特殊需求制約的,美術(shù)的需要同樣也規(guī)定了它的某些特殊功能。遠(yuǎn)古時(shí)期人們需要用豐富的圖像把打獵時(shí)的場景記錄下來,把所見到的獵物的形狀描繪下來,或是為了把當(dāng)時(shí)的輝煌戰(zhàn)績作為紀(jì)念,或是僅僅需要在下次打獵時(shí)能夠準(zhǔn)確的判斷前方是何物,中國各朝各代的美術(shù)特點(diǎn)也都是結(jié)合當(dāng)時(shí)的風(fēng)土人情,人們無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zhì)上的需要和社會(huì)的需求而產(chǎn)生的。簡言之,美術(shù)的功能是先于美術(shù)本身而存在的。但是美術(shù)的功能不單單是表現(xiàn)在它的創(chuàng)作者的個(gè)人意圖,或者說是個(gè)人意識(shí)上,還需要社會(huì)知覺它和掌握它,這是一種互動(dòng)的關(guān)系。 一件美術(shù)作品有不同的用處就會(huì)產(chǎn)生不同的文化價(jià)值,它的美術(shù)功能也就不同。美術(shù)作為人類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社會(huì)功能性是其得以延續(xù)的血脈。
二、中國美術(shù)變革思潮的興起
1919年前后是一個(gè)革命的時(shí)代,戊戌維新運(yùn)動(dòng)和結(jié)束了幾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以及當(dāng)時(shí)出現(xiàn)的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和1919年爆發(fā)的五四運(yùn)動(dòng),打破陳舊的封建政治、文化體制,引入新時(shí)代的暖流,借鑒西方“民主”、“科學(xué)”的思想和經(jīng)驗(yàn),在中國大地上進(jìn)行了一場從政治、社會(huì)、文化、思想上全面的深刻的革命運(yùn)動(dòng)。
整個(gè)社會(huì)革命的浪潮引發(fā)國人對傳統(tǒng)文化的重估,藝術(shù)家們由“士”階層向現(xiàn)代知識(shí)分子轉(zhuǎn)化,西方知識(shí)體系和文化革新的傳入,改變了中國畫家原有的知識(shí)結(jié)構(gòu)和價(jià)值體系。近代學(xué)術(shù)的轉(zhuǎn)型和民族國家意識(shí)的重新認(rèn)識(shí)都引發(fā)美術(shù)內(nèi)部的革新轉(zhuǎn)變。隨著鴉片戰(zhàn)爭的爆發(fā),西方列強(qiáng)的侵入,打破了傳統(tǒng)的“中夏外夷”的民族意識(shí),“自強(qiáng)”的要求使國人把注意力轉(zhuǎn)向西方。最先意識(shí)到民族危患的一些先進(jìn)知識(shí)分子們告誡人們:“中國若再不改行新政,吾數(shù)年來,不見此國矣。”“中國人心至是紛紛欲舊邦新命矣。”[1]政治的衰敗被歸咎于傳統(tǒng)文化的禁錮,一些先進(jìn)知識(shí)分子開始質(zhì)疑中國固有的傳統(tǒng)文化思想,這些質(zhì)疑的呼聲催化了文化的革新,外加西方列強(qiáng)的成功侵入使得這些知識(shí)分子們對西方先進(jìn)文化思想敬仰和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憂患,從而引發(fā)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整體性重新評價(jià)。烏以峰在20年代發(fā)表于《造型藝術(shù)》雜志的《美術(shù)雜話》中的一段話這樣描述:“西洋繪畫進(jìn)步之速”,真是一日千里。自然派﹑印象派﹑后期印象派﹑立體派﹑未來派,二三百年之中,畫派之蔚起者甚多。然中國繪畫仍固守殘缺,息息待滅。一般學(xué)畫者非黃即王,非董即倪。總是相沿舊范中周旋,決不肯放大氣力自創(chuàng)新派也。”與此同時(shí),西畫東漸打破了中國畫唯我獨(dú)尊的格局,“國畫”﹑“美術(shù)”﹑“美術(shù)畫”﹑“藝術(shù)”等稱呼也成為當(dāng)時(shí)中國畫壇頻繁出現(xiàn)的新詞語,不僅反映出其中語境邏輯上的轉(zhuǎn)變,也反映出傳統(tǒng)畫學(xué)思維在西漸思潮沖擊下的消解和重建,同時(shí)也動(dòng)搖了實(shí)際應(yīng)用上的中國畫傳統(tǒng)的線型造形。水天中先生在《“中國畫”名稱的產(chǎn)生和變化》一文中指出:“‘西洋畫和‘中國畫這兩個(gè)名稱并列時(shí),中國畫家第一次發(fā)現(xiàn)他的行動(dòng)須控制在一條邊界之內(nèi)。”[2]“中國畫”一詞從誕生之日起就帶有某種濃重的民族意識(shí)涵義。這與中國畫作為元明以前唯一正宗的畫學(xué)大相徑庭,也與西洋畫引入尚未對中國畫造成威脅性影響的清代畫壇不可同日而語。西洋畫的引入不僅為中國畫拓寬了視野,更帶動(dòng)了中國畫某種自我意識(shí)的萌醒和反思,使有識(shí)之士們重新審視自己的過去和將來。
三、中國美術(shù)變革成為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重要組成部分
呂澂和陳獨(dú)秀同時(shí)在1919年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hào)上發(fā)表文章,呂澂的文章啟用《美術(shù)革命》的標(biāo)題,而陳獨(dú)秀的文章標(biāo)題為《美術(shù)革命——答呂澂》,他們的標(biāo)題都用了“美術(shù)革命”。呂澂之所以提出美術(shù)革命,主要是對現(xiàn)實(shí)中的繪畫現(xiàn)狀不滿,對因西畫的引入產(chǎn)生的混亂局面感到憂慮,并且擔(dān)憂毒害無知懵懂的青年人,因而他疾呼美術(shù)革命:“我國美術(shù)之弊,蓋莫甚于今日,誠不可不亟加革命也。革命之道何由始?曰:闡明美術(shù)之范圍與實(shí)質(zhì),使恒人曉然美術(shù)所以為美術(shù)者何在,其一事也。使恒人知我國固有之美術(shù)如何,此又一事也。闡明歐美美術(shù)之變遷,與夫現(xiàn)在各新派之真相,使恒人知美術(shù)界大勢之所趨向,此又一事也。即以美術(shù)真諦之學(xué)說,印證東西新舊各種美術(shù),得其真正之是非,而使有志美術(shù)者,各能求其歸宿而發(fā)揚(yáng)光大之,此又一事也,使此數(shù)事盡明,則社會(huì)知美術(shù)正途所在,視聽一新,嗜好漸變,而后陋俗之徙不足辟,美育之效不難期矣。”[3]而陳獨(dú)秀只是借呂澂的話題,作答的方式回應(yīng)并提出“美術(shù)革命”,背后潛藏著政治變革的意圖。相比之下,陳獨(dú)秀對于中國畫本體問題的提出則更加直接有力,他指出“若想把中國畫改良,首先要革王畫的命。因?yàn)楦牧贾袊嫞瑪嗖荒懿徊捎醚螽媽憣?shí)的精神。”[4]他認(rèn)為現(xiàn)實(shí)主義是近世歐洲的時(shí)代精神,在1915年10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一卷第二號(hào)上《今日之教育方針》中提出,近世歐洲之時(shí)代精神在哲學(xué)上的表現(xiàn)為經(jīng)驗(yàn)論、唯物論;在宗教上的表現(xiàn)為無神論;在文學(xué)美術(shù)上的表現(xiàn)為寫實(shí)主義、自然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誠今世貧弱國民教育之第一方針矣。”他的這種“現(xiàn)實(shí)主義”是一種廣義上的思想方法和哲學(xué)精神,是有理想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實(shí)的精神指導(dǎo)和最終方針,它包括文學(xué)美術(shù)在內(nèi)的寫實(shí)主義精神。而舊藝術(shù)、舊文學(xué)是其最大的阻礙,所以首先把要革王畫的命作為推翻舊思想模式的一種象征,從而立寫實(shí)主義精神的新思想模式。他還提出“文學(xué)革命”,他認(rèn)為“文學(xué)革命”對于“美術(shù)革命”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譬如文學(xué)家必用寫實(shí)主義,才能夠采古人的技術(shù),發(fā)揮自己的天才,做自己的文章,而不是抄古人。”他把文學(xué)革命所提倡的寫實(shí)精神換用到美術(shù)革命當(dāng)中,提出“畫家也必須用寫實(shí)主義,才能夠發(fā)揮自己的天才,畫自己的畫,不落古人的窠臼。呂澂和陳獨(dú)秀的美術(shù)革命有相同點(diǎn)但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點(diǎn)是都對美術(shù)現(xiàn)狀不滿,要在文學(xué)革命的同時(shí)也要美術(shù)革命;不同的是陳氏的矛頭主要指向士大夫的文人寫意畫,認(rèn)為只有革王畫的命,采用洋畫的寫實(shí)主義精神作為中國畫變革的唯一手段,而呂澂提出的問題則沒有這樣單一化,他所提倡的美術(shù)革命是多方面的,不僅包括對美術(shù)的實(shí)質(zhì)和范圍的分析,中國古代傳統(tǒng)美術(shù)的了解,還闡明西方美術(shù)的演變和當(dāng)代世界美術(shù)的趨勢,認(rèn)為綜合的基礎(chǔ)上破舊立新。
在呂、陳進(jìn)行“美術(shù)革命”思想傳播的同時(shí),另一位中國畫改良派的思想家康有為也寫了一篇《萬木草堂藏畫目序》作為思考中國傳統(tǒng)繪畫的整理,痛斥了中國傳統(tǒng)繪畫的弊端,提出用以歐美寫實(shí)主義來改良傳統(tǒng)文人寫意畫,求其復(fù)古來革新,恢復(fù)唐宋時(shí)期繪畫的寫實(shí)風(fēng)格。康有為之所以也提出變革中國畫,是他對中國畫深切的擔(dān)憂,他的中國畫改良思想是其政治上的延伸,希望中國畫能夠像中國社會(huì)一樣從低谷中走出來,奔向光明。
四、中國美術(shù)變革的幾位代表人物和主要貢獻(xiàn)
呂澂、陳獨(dú)秀、康有為的美術(shù)革命或變革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中國畫方面,他們提出的中國畫變革與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思想主張?jiān)诿佬g(shù)界引起轟動(dòng),也影響了徐悲鴻、林風(fēng)眠、劉海粟、高劍父等人。
徐悲鴻深受康有為的影響,對于中國畫的現(xiàn)狀提出了一系列的改良方法。他不僅用歷史的觀點(diǎn)比較中國當(dāng)今化與古代畫的優(yōu)劣,而且兼并中西,去西方繪畫之所長,補(bǔ)東方繪畫之所短。他在后來的《新國畫建立之步驟》中所提出的“故建立新中國畫,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僅直接師法造化而已。”揭示了要以寫實(shí)主義改造中國畫的實(shí)質(zhì)目的。其一,他反對抄襲古人,提倡師法自然。其二,他提倡用西方寫實(shí)主義來改良中國畫。1932年冬,他還在《畫范》序中提出了“新七法”作為改良中國畫的評判標(biāo)準(zhǔn)。這“新七法”是:一、位置得宜;二、比例正確;三、黑白分明;四、動(dòng)態(tài)天然;五、輕重和諧;六、性格畢現(xiàn);七、傳神阿堵。“新七法”是將西方寫實(shí)主義精神恰到好處的融入其中。其三,他強(qiáng)調(diào)素描與中國傳統(tǒng)繪畫特點(diǎn)的結(jié)合。徐悲鴻的社會(huì)交往活動(dòng)頻繁,其中很多與他的中國畫觀形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他敏銳的觀察普通大眾是美術(shù)展覽的主要觀眾,對于藝術(shù)大眾化的傾向無疑是他在繪畫創(chuàng)作主題上和風(fēng)格上得到啟發(fā)。1926年,徐悲鴻提出“采用歐洲之寫實(shí)主義,可使我國之理想主義繪畫大放光明于世界”的主張,他面對社會(huì)大眾呼吁寫實(shí)主義繪畫的重要性,這在當(dāng)時(shí)無疑是順應(yīng)時(shí)代潮流的,是社會(huì)所需要的。他認(rèn)為,藝術(shù)不再僅屬于有教養(yǎng)的知識(shí)分子,而應(yīng)更受益于群眾,即社會(huì)大多數(shù)的工農(nóng)無產(chǎn)者。
嶺南畫派代表人物高劍父被看作是“20世紀(jì)最早以懷疑主義的眼光審查傳統(tǒng)中國畫學(xué),并對變動(dòng)的世界保持強(qiáng)烈的好奇心的先驅(qū)者之一。”[5]在很長一段時(shí)間,嶺南派畫家以“折衷派”自居,所提出“折衷中外,融匯古今”的“新國畫”觀,既具有徐悲鴻的“引西潤中”的傾向,又結(jié)合了中國傳統(tǒng)繪畫的師徒制。高劍父曾作一文《我的現(xiàn)代國畫觀》,這是他“新國畫”觀思想的總匯。“新”與“現(xiàn)代”相對應(yīng),而“新”又與“西方”緊密相聯(lián),所以傳統(tǒng)繪畫中滲透西方畫學(xué)技法成為嶺南畫派中國畫改良的重要途徑。嶺南畫派的中西融合方案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最為明顯。由于廣東在當(dāng)時(shí)政治革命中的特殊狀況,嶺南畫派的“新中國畫”的改革思潮就與政治、文化革命緊密相連。高氏兄弟主辦的《真相畫報(bào)》較早的認(rèn)識(shí)了美術(shù)“即使是不識(shí)字、沒有文化的人也能一目了然”以及它在革命宣傳中的重要作用。作為辛亥革命元老的高劍父更是提出了“藝術(shù)救國”的主張,將中國畫的現(xiàn)代化與人民大眾結(jié)合起來,并提出了“現(xiàn)代畫,不是個(gè)人的、狹義的、封建思想的,是要普遍的、大眾化的”。
如果說徐悲鴻是以西方古典寫實(shí)主義來改造中國傳統(tǒng)繪畫,那么林風(fēng)眠則是從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中尋找東西結(jié)合的銜接點(diǎn);相對于高劍父的“折衷”思想,林風(fēng)眠則是強(qiáng)調(diào)東西方繪畫的互動(dòng)性和互補(bǔ)性。將“調(diào)和論”運(yùn)用到中國畫革新,并對現(xiàn)代中國畫的發(fā)展和推進(jìn)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代表人物,首選林風(fēng)眠。林氏的“調(diào)和論”主張是基于兩個(gè)重要前提:一是中西繪畫各有所長:東方繪畫重在情緒的表達(dá),西方繪畫偏重于繪畫形式的表達(dá)。二是繪畫本身的相通性,他曾多次提出“繪畫本身就是繪畫”,不難看出中西繪畫差異的相對性和可跨越性。“一方面在課內(nèi)畫著所謂‘西洋畫,一方面在課外也畫著我心目中的中國畫,這就在中西之間,使我發(fā)生了這樣一種興趣:繪畫在諸般藝術(shù)中的地位,不過是用色彩線條表現(xiàn)而純粹用視覺獲得的藝術(shù)而已,普通所謂‘中國畫同‘西洋畫者,在如是想法之下還不是全沒有區(qū)別的東西嗎?從此,我不再人云亦云地區(qū)別‘中國畫同‘西洋畫,我就稱繪畫藝術(shù)是繪畫藝術(shù);同時(shí),我也竭力在一般人以為是截然兩種繪畫之間,交互地使用彼此對手底方法。”[6]與高劍父提倡的“復(fù)興中國畫”運(yùn)動(dòng)相比,林風(fēng)眠所提倡的“藝術(shù)運(yùn)動(dòng)”關(guān)注的并不是社會(huì)和政治層面的問題,而是藝術(shù)本身,即“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問題。
劉海粟所向往的是一種不受自然支配、不受古人支配、不受理智約束、不受權(quán)貴限制的自由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狀態(tài),所以,他沒有沿著“寫形之精” 的路走下去,而是找到了適應(yīng)他走的路——中國畫的表現(xiàn)性繪畫。他在1923年撰寫《制作藝術(shù)就是生命的表現(xiàn)》的一文中指出:“宋有畫院,院體派的畫,千篇一律,好似刻版一樣,有工藝的價(jià)值,而沒有藝術(shù)的精神。八大、石濤、石溪輩藝術(shù)家,他們的作品超越于自然的形象,是主觀一種抽象的表現(xiàn),有一種強(qiáng)烈的情感,躍然現(xiàn)于紙上,他們從一切線條里表現(xiàn)他們狂熱的情感以及心狀,這就是他們的生命。”[7]劉海粟對西方的印象主義、新印象主義、后印象主義十分的重視,也做過深入的研究。1929年到1931年,他被派赴歐洲考察研究藝術(shù),這兩年多的時(shí)間里他認(rèn)真考察了法國、意大利、德國、比利時(shí)等國家的藝術(shù),1932年到1935年再度赴歐開展中外美術(shù)交流活動(dòng)。劉海粟還在1932年編印了《世界名畫集》叢書,可以看出劉海粟想把歐洲新鮮的血液注入到中國這片廣大的土地上,讓中國的青年學(xué)者在本國就能夠了解到外面世界的美術(shù)狀況,不做井底之蛙。他還翻譯了英國T·W·厄普的《現(xiàn)代繪畫論》(1936年,商務(wù)印書館發(fā)行),這無疑幫助了中國美術(shù)界系統(tǒng)的了解到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特點(diǎn)及思潮。上海美專是劉海粟新藝術(shù)主張的宣傳陣地。他鼓勵(lì)學(xué)員們“散到各省各地去從事藝術(shù)教育或鼓吹發(fā)揚(yáng)藝術(shù),都曉得竭力促進(jìn)社會(huì)的藝術(shù)化”[8]并指出“我們確信‘藝術(shù)是開掘新社會(huì)的鐵鏟子,導(dǎo)引新生活的安全燈”。劉海粟提出的“社會(huì)的藝術(shù)化”其實(shí)指的就是藝術(shù)的社會(huì)化,這與藝術(shù)的私密化和小眾化相抵制。作為一個(gè)美術(shù)教育家和社會(huì)活動(dòng)家,劉海粟時(shí)時(shí)刻刻關(guān)注美術(shù)界的未來,在社會(huì)公眾事務(wù)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希望中國現(xiàn)代美術(shù)能夠脫掉“傳統(tǒng)”盔甲束縛的外衣,靈活自如的施展能量。
五、中國美術(shù)變革的歷史意義和深遠(yuǎn)影響
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主張美術(shù)變革的代表人物,雖然在中國畫變革的征途中實(shí)施的具體辦法和措施不盡相同,但他們都不約而同的提倡走融合中西之路徑,取長補(bǔ)短,同時(shí)他們心懷國族意識(shí)和時(shí)代使命感,期望中國繪畫無論從思想上和內(nèi)容上,還是技巧與技法和其表現(xiàn)形式上都煥然一新。這一時(shí)期中國美術(shù)變革所持有的主張、思想與作品深刻影響了二十世紀(jì)中國畫的進(jìn)程方向,是中國美術(shù)發(fā)展史上的新紀(jì)元和里程碑。從康有為、陳獨(dú)秀到徐悲鴻、林風(fēng)眠、劉海粟、高劍父等對中國畫變革所作出的努力為日后新世紀(jì)中國畫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xiàn),也打開了中國傳統(tǒng)繪畫新走向的大門,給中國繪畫輸入了新鮮的血液,使得后來人可以從中得到吸收和借鑒,也為其后一系列的變革提供了許許多多循環(huán)往復(fù)的樣本。
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以來,以東西方美術(shù)交融為特征的中國美術(shù)變革,徹底結(jié)束了千年來文人畫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作為改造社會(huì)的重大措施,確立了美術(shù)教育在中國近現(xiàn)代全民教育上的重要地位,隨著“五四”時(shí)期留學(xué)海外的大批青年美術(shù)家歸來投身美術(shù)教育,中國美術(shù)進(jìn)入了一個(gè)人才輩出的新時(shí)代。同時(shí),從引進(jìn)西洋美術(shù)到西方美術(shù)思想在中國廣泛傳播,在比較中發(fā)現(xiàn)并創(chuàng)造自身價(jià)值,讓中國美術(shù)與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更加密切,日益散發(fā)出時(shí)代氣息和活力。在其后的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異常激烈的三四十年代,出色的美術(shù)家們紛紛以藝術(shù)為武器,投身于抗日戰(zhàn)爭和革命事業(yè),他們關(guān)心民間的疾苦,關(guān)注社會(huì)的變動(dòng),反映民眾的情緒,反映民眾的抗敵斗爭和解放運(yùn)動(dòng),更加深入地闡釋著中國美術(shù)的社會(huì)化功能。“中國古老的繪畫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不僅是在繼承下去,而且是在吸取著新鮮的題材、吸取著新鮮的繪畫技法的基礎(chǔ)上繼續(xù)地發(fā)揚(yáng)光大。”[9]
〔參考文獻(xiàn)〕
〔1〕文廷式.聞塵偶記〔J〕.近代史資料,1981,(01).
〔2〕水天中.“中國畫”名稱的產(chǎn)生和變化〔J〕.美術(shù),1986,(03).
〔3〕呂澂.美術(shù)革命〔J〕.新青年,1919,(06).
〔4〕陳獨(dú)秀.美術(shù)革命——答呂澂〔J〕.新青年,1919,(06).
〔5〕李偉銘.高劍父繪畫中的日本風(fēng)格及相關(guān)問題〔J〕.朵云,1982,(03).
〔6〕林風(fēng)眠.我的興趣〔J〕.東方雜志,1936,(03).
〔7〕劉海粟.制作藝術(shù)就是生命的表現(xiàn)〔J〕.學(xué)燈,1923,(03).
〔8〕袁志煌,陳祖恩.劉海粟年譜-上海美術(shù)學(xué)校同學(xué)錄序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20,(12):30.
〔9〕鄭振鐸.近百年來中國繪畫的發(fā)展-鄭振鐸藝術(shù)考古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09):189.
〔責(zé)任編輯:馮延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