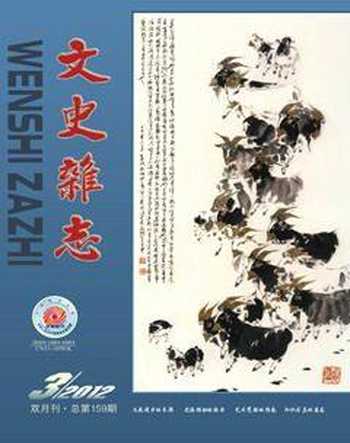“文人”與“官人”的身份糾結
高智
宋嘉祐年間,江蘇泰州人許平死了,葬在真州(治今江蘇儀征)揚子縣甘露鄉某處原野。許平生前任海陵縣主簿,主管文書,輔佐縣令,位卑職低,在冗官成災的北宋,簡直像一顆小小的芝麻,連官都算不上。
王安石卻慧眼識珠,情深意長地給他寫了一段墓志銘:“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于斯!誰或使之?”哀悼許君有才能而居下位,像這樣離俗獨行之士,命運多舛,仕進壅隔,“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而卒”。王荊公很是糾結:怎么到了這個職位就完了,是誰在主宰這些讀書人的命運,“誰或使之?”
王安石不是傷許平的死,他是在“嗚呼”所有個性文人的命運。在他看來,循規蹈矩唯唯諾諾的儒生,是不能成為“士”的。他寫了篇《讀孟嘗君傳》,力排眾議,把孟嘗君選拔人才的標準奚落了一番,認為他所招徠的“人才”無非是“雞鳴狗盜之徒”。荊公認為,“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悔,困辱而不悔”(《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志銘》),只按照自己意志行事,被人謾罵譏諷和欺辱卻不悔恨,才是真正的“文人”。王安石提高了文人的標準,要踏入“士”這道門坎,說白了,行動上要“特立獨行”,思想上要“卓犖不羈”,這就與傳統禮教相去甚遠。宋以文立國,以詩賦取士,數不清的溫柔敦厚的儒生,亦步亦趨,鸚鵡學舌,鑄成了這個龐大帝國金字塔的基座。讀書人引以自傲的,是知識不是思想,達到思想頂峰的人寥若晨星。而王安石卻要求“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游褒禪山記》),要他們像自己一樣時常保持清醒,“夢闌時,酒醒后,思量著”(《千秋歲引》),要讀書人在浩浩卷帙之中,提著燈籠找思想,簡直是要了他們的命。
王安石把自己站立成一棵孤零零的樹,獨立于儒林,俊秀、挺拔、堅硬,“天質自森森,孤高幾百尋。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虛心”(《孤桐》)。王安石這棵“個性”的“孤桐”,枝繁葉茂,迎風招展,很快便引來一片罵聲。最先罵他的是蘇洵。他寫了篇《辨奸論》,杜撰經典,假托西晉“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見王衍事,罵王安石“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把他說成野心家:“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最后抓住王安石私生活大做文章,說他不修邊幅,囚首喪面,形象委瑣,是為大奸:“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
對《辨奸論》的作者,新中國成立后爭論不休。邵伯溫(1057-1134)的《邵氏聞見錄》收錄此文,署名蘇洵。因蘇洵于王安石變法前三年去世,故清人李紱在《書〈辨奸論〉后二則》(《穆堂初稿》卷四十五),以為此文為邵伯溫冒蘇洵之名,以攻擊王安石之作。此說一起,聚訟紛起,真偽之辨,成為學術爭鳴熱點。
是誰罵王安石不太重要,但罵人的方式值得商榷。南宋的朱弁(?-1144,字少章,號觀如居士,江西婺源人)推崇司馬光,雖然對王安石不滿,但對把隱私和人品扯上干系的罵法卻不茍同。他所著《曲洧舊聞》卷十載:“王荊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污,飲食粗惡,一無所擇,自少時則然,蘇明允著《辨奸》,其言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以為不近人情者,何謂是也?”王安石生活邋遢,長時間不洗臉,不漱口,不換衣服,不洗澡。生活上的不修邊幅,卻讓蘇老泉拿來作為攻訐理由,確實也“下三濫”了些。
罵王安石最厲害的,其實是宋朝皇帝。宋高宗說:“安石之學雜以伯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于安石。”宋理宗更不解恨,淳祐元年下詔,以周濂溪、二程、張載、朱熹五人從祀孔廟的同時,撤銷了王安石的從祀地位,并指責“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語最為萬世之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庭,合與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說關系不小,令國子監日下施行”。其實高宗是沒有多少資格評價王安石的。他的執政業績在宋代實在一般,績效考核至多也只能算作基本稱職。皇帝為什么要罵?其實是為了轉移注意力。南宋在檢討造成危亡的原因時,將責任上溯到安石,于是王安石成為南宋重新收拾人心,聚攏民意的替罪羔羊;所有的皇族也都脫去了“國事失圖”的干系,王安石成了犧牲品,臣民又可“人思宋德、天眷趙宗”。宋理宗把王安石“請”出孔廟,其實是做了件天大的好事——讓他和其他五人分清界線。本來王氏和他們“合并同類頂”,就是一件滑稽的事情。道不同不相與謀。讓天下讀書人同時膜拜這六位,如同老百姓既拜關公又拜李逵,書生們不會答應;那五位溫柔敦厚的老先生,倘若活著,也是斷然不會答應的。
罵者氣急敗壞,說明王的改革確實觸動他們的利益。作為文人,王安石是個例外;作為官人,王安石也是個例外。整個北宋王朝就像負重前行的馬車,冗兵冗費冗員壓得車轱轆吱嘎作響。車子的四個轱轆,分別叫作士農工商。車夫叫皇帝。宋代的這駕馬車,前輪大后輪小,開起來實在別扭;到了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已經換了五位車夫。宋英宗趙曙在京城開封皇宮福寧殿病逝,宋朝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趙頊登上歷史舞臺。宋神宗登基時,只有20歲,正是血氣方剛的年齡。他繼位后不治宮室,不事游幸,勤于政事,勵精圖治,想成就一番事業。他先找老臣富弼問政。富弼建議“阜安宇內為先”,“當先布德澤,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強調和諧穩定。老邁的臣子與年輕的皇帝心理距離差得太大,神宗很不滿意。于是特立獨行的王安石便和他一拍即合,做了這輛破破爛爛老馬車的副駕駛。
作為“官人”的王安石的改革,觸動的是“官人”的利益。他打出“理天下之財”的旗幟,其實就是對儒家傳統經濟思想的公開背叛。趙益先生在《王霸義利——北宋王安石改革批判》一文中說道,“觸動的最根本原則就是‘王霸義利準則,這是一個微妙的平衡系統,表現為‘以義為上和‘公利可言的有機統一。假如動搖了這個平衡,便是對整個穩定的中國文化系統的破壞,必將被吞噬在一個無形的黑洞中”。
最先跳出來反對他的,便是那群持中保和的“官人”,由推薦過王安石的司馬光領銜。“官人”罵聲如潮。司馬光、李常等人的《上神宗論王安石》、劉琦的《上神宗論王安石專權謀利及引薛向領均輸非便》,罵得有理有節,文質彬彬。呂誨寫了篇《上神宗論王安石奸詐十事》,則一改風格,罵得痛快淋漓:“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其實王安石也無意與“官人”作對,他的改革主要是文化體制改革和經濟制度的改革。后者涉及金融稅收等政策,想辦法弄點錢,緩解財政危機。兵制改革,減少冗兵冗費而已,與土地所有制改革無關,更談不上政改。他的憂慮是“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他繼承法家富國強兵的思想理念,把“管桑之術”那種主張政府干預經濟,通過官營禁榷等方式來拯救當時財政困窘的理論,發展到了新的歷史高度。他給改革設計了—個好的路線圖,然而這個路線圖卻執行難,只能變成天空中那片美麗的云彩,成為浪漫主義的布景。他的改革不完整之處甚多;最為緊要的是,即便是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層官員手里,常常會走了樣。讓“官人”“批評與自我批評”容易,讓“官人”自己“改”自己,和自己的利益過不去,那就簡直是天方夜談了。所以“官人”們的應付方法,一個字:拖。以方田法為例,最初是在公元1072年提出的,直到1082年,開封府報告每年測量只及于兩縣,全府之19縣須10年才能測量完畢——已經蹉跎10年了。
作為文人,王安石看重思想注重實務。1070年,他改革貢舉法,在進士殿試中罷詩、賦、論而改試時務策;次年廢除考背誦的“明經科”,以進士一科取士,另設“明法科”,考律令斷案。他用學校平時的考核來取代科舉取士,選拔人才,搞素質教育。作為官人,他具有深遠卓見。他從基層干起,深諳官場規則,變法大部分措施能切中時弊。若不是中國傳統文化強大的磁場加上歷史的慣性把北宋那架破舊的馬車吸附進去,他說不定還能改出一片新天地來。
王安石是一個勇敢而孤獨的行者。他在前面引路,后面的人卻在他身后丟石頭。他的孤獨不可怕,可怕的是無人意會他的孤獨。他的功過是非,也只能留待后人“謾嗟榮辱”了。黃仁宇先生認為,王安石變法之所以未能取得成功,是因為當時社會發展尚未達到足以支持這項改革試驗成功的程度。從此角度講,他是那個時代的先行者,如同一個星際來客,神秘來訪,化作別館寒砧聲里,孤城畫角旁,悄然生長的一株石榴,花香馥郁,孤傲高潔。他的一生,恰如他的詩所言:“萬綠叢中一點紅,動人春色不須多”(《石榴》)。正是那抹紅色,成為中國歷史天空中極其燦爛的色彩,九百多年來熠熠生輝。
作者: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