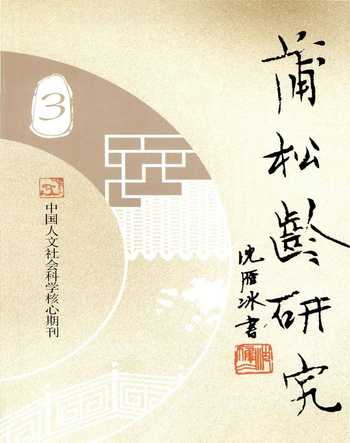紀曉嵐質(zhì)疑蒲松齡《聊齋志異》的創(chuàng)作方法史料分析
盛偉
摘要:在蒲松齡一生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他將“唐宋傳奇”的創(chuàng)作手法與“魏晉志怪”融于一體,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聊齋志異》的創(chuàng)作手法;但當清乾隆間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出,在清初的文壇上形成兩大文學創(chuàng)作高峰,這本是文學繁榮發(fā)展的好征兆,但以《閱微草堂筆記》為核心的紀氏弟子,成了“質(zhì)疑”蒲松齡《聊齋志異》創(chuàng)作手法的法寶,弄得清后期的文壇上,以此為核心爭論不休。該文,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論證紀氏及其弟子“質(zhì)疑”的歷史局限;而廣大蒲松齡《聊齋志異》的獨特的創(chuàng)作方法,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
關鍵詞:紀曉嵐;質(zhì)疑;聊齋創(chuàng)作方法;分析
中圖分類號:I207.419 文獻標識碼:A
紀曉嵐“質(zhì)疑”蒲松齡《聊齋志異》創(chuàng)作方法的直接的文字史料,見于《閱微草堂筆記》卷后,紀曉嵐為紀念其早逝之子紀汝佶,“附錄”紀汝佶仿蒲松齡《聊齋志異》所創(chuàng)作六則“志怪”故事的“附言”中。紀曉嵐自己的文藝觀,在此則“附言”中,表達的還是極為清楚的。但長期以來,它卻被研究蒲松齡與紀曉嵐文藝觀之分歧者所忽視。盛時彥為《閱微草堂筆記》中《姑妄聽之·跋》初版時,所寫于清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跋》,與嘉慶五年庚申(1800)盛時彥為整理合編《閱微草堂筆記》五種,他又寫了一篇《序》。這些文字都是盛氏手筆轉(zhuǎn)述紀曉嵐的文學觀點,并非紀曉嵐的談話實錄。所以,這些文字有無盛時彥自己的發(fā)揮,就很難說了。所以,盛時彥只能在其《序》尾說:“時彥夙從先生游,嘗刻先生《姑妄聽之》,附‘跋書尾,先生頗以為知言。”此說是“知言”,而不是“直言”。故在《序》中所說:“故誨淫導欲之書,以佳人才子相矜者,雖紙貴一時,終漸歸湮沒。”我想大學者紀曉嵐,其心胸未必這樣偏狹。若時彥能活到現(xiàn)在,他自己也會說:他偏狹。《聊齋》風行天下,時代變了。歷史是無情的。
下邊,我們看看紀曉嵐自己所陳述的文藝觀。
《灤陽續(xù)錄》(六)后,紀曉嵐附錄了其亡子紀汝佶所作“志怪”小說六則。為此紀曉嵐加了一段《跋》語,在這段《跋》中,紀曉嵐直接闡述了自己的文藝觀,《跋》不長,現(xiàn)錄于下:
亡兒汝佶,以乾隆甲子生。幼頗聰慧,讀書未多,即能作八比。乙酉舉于鄉(xiāng),始稍稍治詩古文,尚未識門徑也。會余從軍西域,乃自從詩社才士游,遂誤從公安、竟陵兩派入。后依朱子穎于泰安,見《聊齋志異》抄本(時,是書尚未刻--筆者,此為紀曉嵐自注),又誤墮其窠臼,竟沉淪不返,以訖于亡。故其遺詩、遺文,僅付孫樹庭等存乃父手澤,余未一為編次也。惟所作雜記,尚未成書。其間瑣事,時或可采。因為簡擇數(shù)條,附此錄之末,以不沒其篝燈呵凍之勞。又惜其一歸彼法,百事無成,徒以無關著述之詞,存其名字也。
文中,一大懸案,紀曉嵐將其子紀汝佶之死坐實歸罪于閱讀而摹擬《聊齋志異》,是不當?shù)模藙t有歷史為證。又把其迷而不回頭在《聊齋志異》窠臼,歸罪于朱子穎,真是冤大頭。
紀曉嵐《跋》中說:“會余從軍西域,乃自從詩社才士游,遂誤從‘公安、‘竟陵兩派入。”這段話中,涉及到兩個關鍵的問題需要說明。
其一,是紀曉嵐的“從軍西域”之事。
此事發(fā)生于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是年紀曉嵐45歲。事的起因: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獲罪,有旨籍其家,因盧見曾孫盧蔭文是紀曉嵐的貴婿,紀曉嵐徇私漏言,即事先將被抄家的消息告知了盧見曾,使盧家有了一定的準備。事發(fā)后,紀曉嵐獲罪,被革職戍烏魯木齊。其實,就是充軍、流放烏魯木齊。該事,在王昶《趙文哲墓志銘》中有記載:“戊子秋,侍學士紀昀,中書舍人徐步云泄兩淮鹽運使盧見曾事,君與余牽連得罪。”(后,盧見曾死于獄中)
對這次被充軍西域(烏魯木齊),紀曉嵐在被遣去的途中曾作《雜詩三首》記述其當時的矛盾心情。其詩:
少年事游俠,腰佩雙吳鉤。
平生受人恩,一一何曾酬。
瓊玖報木李,茲事已千秋。
撫己良多慚,紛紛焉足尤。
蝮蛇一螫手,斷腕乃無疑。
一體本自愛,勢迫當如斯。
世途多險阻,棄置復何辭?
惻惻《谷風詩》,無忘安樂時。
北風凄以厲,十月生寒林。
飄搖霜雪降,蕙草已成殘。
黃鵠接翼翔,豈礙天地寬。
前后相和鳴,亦足為君歡。
這組詩為紀曉嵐充軍西域時,途中因感于邊塞北風中的凄苦環(huán)境和自己因漏言而被充軍的感懷。詩中反映了紀曉嵐此時、此地的矛盾心情。由于自幼養(yǎng)成的“游俠”性格,受人之恩,當以涌泉相報。正因為“瓊玖報木李,茲事已千秋”。他認為“一體本自愛,勢迫當如斯。”自己這樣作,為勢所迫,因為這是手足之情。當然,這種舉動與君恩至上的封建社會的封建理念是相悖逆的。由于“蝮蛇一螫手,斷腕乃不疑。”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在那個社會“血染紅頂子”而高升者,多為自己的知情之人。所以,紀曉嵐深深地感到“世途多險阻,棄置復何辭?”世途歷來就是這樣。在無可奈何之下,紀曉嵐自嘲曰:“前后相和鳴,亦足為君歡。”也許正由于紀曉嵐經(jīng)歷了嚴酷社會現(xiàn)實的打擊,使紀曉嵐的性格磨礪成類似玩世不恭詭秘的神態(tài)。紀曉嵐被充軍三年,時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時年48歲,“恩命賜環(huán)”。即是年六月紀曉嵐初至京師,暫居珠巢街。此事,在紀曉嵐《烏魯木齊雜詩·序》中說:“余謫烏魯木齊,凡二載,鞅掌簿書,未遑吟詠。庚寅(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二月,‘恩命賜環(huán)。辛卯(乾隆三十六年1771)二月,治裝東歸。”
其二,是“遂誤從公安、竟陵兩派入。”
在明代的文學史上,受李贄思想直接影響的是大張“反復古”旗幟的“公安派”,其代表人物是袁宗道、袁宏道及袁中道兄弟三人。由于他們是湖北公安人,所以世稱“公安派”。“公安派”其主張:在文學發(fā)展觀上,他們認為文學是隨著時代發(fā)展的,各個時代的文學都有其自己的特色,不應該厚古薄今。他們發(fā)出:“古何必高?今何必卑?”的呼聲。在創(chuàng)作觀上,反對摹擬。他們認為文學是隨時代而發(fā)展,那么,就不應該去摹擬古人。他們強烈抨擊當時文人中的復古之風,嚴厲地指出復古事實上就是抄襲。“然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實質(zhì)就是沒有自己的文學見解,文章的內(nèi)容空洞無物,用摹古來裝點門面。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口號是“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其文學主張核心,是批判程朱理學,懷疑傳統(tǒng)封建教條,反對束縛個性。
竟陵派。在明代文學史上,正當“公安派”大張的時候,在文壇上另一個異軍突起的是“竟陵派”。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鍾惺和譚元春。鍾惺,字伯敬;譚元春,字友夏,他們都是湖北竟陵人,故被稱為“竟陵派”。其文學主張反對復古派的機械摹擬古人詞句,提倡抒寫“性靈”,和“公安派”有共同之處。但這兩派都有自己的弱點與不足之處。然而,他們所倡導反對“復古”的文學主張,卻是文學發(fā)展的時代潮流。這就是紀曉嵐所痛心的“誤從公安、竟陵兩派入”之所言。我之所以要將“公安派”與“竟陵派”的產(chǎn)生及文學主張說清楚,就是要全面地來了解紀曉嵐的文學觀。總的來看,他所反對的都是在文學發(fā)展史上的改革派,是逆時代潮流趨勢的。紀曉嵐是一位文學家,但他終生從事的考古、整理,使他的文學觀,必然趨于保守與守舊。
其三,“后依朱子穎于泰安,見《聊齋志異》抄本,(時,是書尚未刻--筆者,此為紀曉嵐自注)。”我們先簡說關于《聊齋志異》的刻本:“時,是書尚未刻”,其實,紀曉嵐此語差矣。此時,已有《聊齋志異》趙氏、王氏刻本問世。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趙起杲青柯亭本《聊齋志異》,已在浙江睦州刊刻問世;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王金范在山東周村刊刻《聊齋志異》十八卷本問世。“又誤墮其窠臼,竟沉淪不返,以訖于亡。”
關于朱子穎與抄本《聊齋志異》。據(jù)《紀曉嵐年譜》之附《譜余》載:“朱孝純,字子穎,漢軍正紅旗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舉人,出紀昀房,投作贄,紀昀最欣賞‘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句。朱孝純官至兩淮鹽運使。”《清史列傳》卷七十一載:“朱孝純(1735-1801),清漢軍旗人,字子穎,號思堂、海愚。乾隆二十七年(1762)舉人。由知縣歷官至兩淮鹽運使。劉海峰弟子,又承其父副都統(tǒng)龍翰家學,工畫能詩,畫孤松怪石有逸氣,詩豪放自喜。在揚州創(chuàng)設梅花書院,扶植文教。有《海愚詩草》、《昆彌拾悟詩草》。”紀文中說:“后依朱子穎”,這“后”是指何時?據(jù)《景城紀氏家譜》:“汝佶,字御調(diào),乾隆乙酉舉人,候選知縣。配宛平縣乾隆壬申科進士、吏部稽勛司郎中張諱模之女。”又據(jù)《紀曉嵐年譜》載:“汝佶(1742-1776),字御調(diào),生于乾隆七年(1742)12月27日,卒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乙酉舉人,候知縣。據(jù)《大清畿輔書徵》卷十八:‘御調(diào)字俠如,又字半漁,有《半舫詩抄》。陶醉于《聊齋志異》,著筆記小說若干,《閱微草堂筆記》附錄六篇。據(jù)有關資料可知,汝佶頗負文學才華,惜不永壽。”據(jù)李文藻說:“乾隆己丑夏(即乾隆三十四年)予以謁選客京師,時先生方戍西域,郎君半漁(即汝佶)招余檢曝書籍。”(紀曉嵐為李文藻會試房師)據(jù)此可說明,此時的紀汝佶還在京師。乾隆三十六年(1771),紀曉嵐由西域“賜環(huán)”,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四庫全書》館,選翰林院官專司篡輯。大學士劉統(tǒng)勛推薦紀曉嵐充篡修官。紀曉嵐在《詩序補義序》中亦說:“余于癸巳受詔校秘書。”據(jù)以上諸條資料推之,紀汝佶到泰安朱子穎處,當在紀曉嵐由西域回歸,因無暇顧及紀汝佶的學業(yè),又因紀汝佶“誤從”“公安”、“竟陵”兩派,使他極為反感。想改變他的處境,所以,親自薦其到泰安師從自己得意門生朱子穎,其時間當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以后。使紀曉嵐更為“痛心”的是,其門生朱子穎就是一位《聊齋志異》的信徒。并有資料記載他自己就編訂一部《聊齋志異》初稿,已準備付梓。所以,紀曉嵐才說“時,是書尚未刻”的話。但此則又有另說,據(jù)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卷八“朱孝純”條載:“朱子穎運使,名孝純,正紅旗漢軍。曉嵐先生門生也,以詩愛知。守泰安時,初見吾淄蒲柳泉先生《聊齋志異》抄本,喜而刻之。偶為刪潤,有長篇縮為二、三行者。先生見之,亦當心服。其余短章數(shù)篇,雖小有致,亦在所棄,不使敗葉溷方華也。自是坊間翻刻盛行,子穎之為功于柳泉大矣。”據(jù)王培荀所言,《聊齋志異》確有朱子穎編訂出版之事,但我多年來從事《聊齋志異》版本的搜集、校訂,出版多個版本,遺憾的是從未見到此版本。有能見者請告我,致謝。正由于朱子穎對《聊齋志異》的愛好,影響了紀汝佶,使他也成了《聊齋》迷,并摹仿寫了許多篇章的《聊齋》類的故事。這使紀曉嵐大為惱火,責其“誤墮其窠臼,竟沉淪不返,以訖于亡。”就是到死,也不回頭。后院起火,這對紀曉嵐來說,真是當頭一棒。但是,他自己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他沒有認識到自己文學創(chuàng)作觀的落伍,只在指責別人。文學創(chuàng)作發(fā)展的時代潮流,是有其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是阻擋不住的。紀曉嵐寫《閱微草堂筆記》是成功的作品,他借以與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抗衡,就錯了。因為他在該書中,所反映出的文學創(chuàng)作觀,并不代表文學發(fā)展時代新動向。所以,他痛惜自己的兒子“其一歸彼法(指汝佶借仿《聊齋志異》的創(chuàng)作方法——筆者),百事無成,徒以此無關著述之詞,存其名字也。”
綜上所述,我們可理出一條脈絡,紀曉嵐反對明朝萬歷后所出現(xiàn)的“公安派”、“竟陵派”。當時的“公安派”、“竟陵派”在文學觀上雖然還存在一些弱點,但是他們“反復古”的大旗是正確的,是當時的時代潮流。后來,他又反對《聊齋志異》的文學創(chuàng)作觀,也是錯誤的。這說明紀曉嵐沒有從舊文學傳統(tǒng)的規(guī)范里走出來,所以,他對新事物看不慣,這正反映了他落后于時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觀。
其他能反映紀曉嵐排斥《聊齋志異》創(chuàng)作方法的文字,見于他在《姑妄聽之》的前言。
今老矣,無復當年之意興,惟時拈紙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而已。故已成《灤陽消夏錄》等三書,復有此集。緬昔作者,如王仲任、應仲遠,引經(jīng)據(jù)古,博辨宏通;陶淵明、劉敬叔、劉義慶,簡淡數(shù)言,自然妙遠。誠不敢妄擬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風教。若懷挾恩怨,顛倒是非,如魏泰、陳善之所為,則自信無是矣。適盛子松云欲為剞劂,因率書數(shù)行并于首,以多得諸傳聞也。遂采莊子之語,名曰:《姑妄聽之》。
在這段文字中紀曉嵐很清楚的說明了自己的《姑妄聽之》的創(chuàng)作,是據(jù)王仲任之“引經(jīng)據(jù)古”、“博辨宏通”;據(jù)陶淵明之“簡淡數(shù)言,自然妙遠。誠不敢妄擬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風教。”這些古訓就是紀曉嵐創(chuàng)作《姑妄聽之》的原則。又以“魏晉志怪”之筆法,創(chuàng)作《閱微草堂筆記》也是紀曉嵐創(chuàng)作的法則。所以,他說“若懷挾恩怨”而“自信無是”,也只是一句空話。如前,所引紀曉嵐在為其子紀汝佶所附六則摹仿《聊齋》故事的《跋》中所表達的愛與憎的態(tài)度,而說對于《聊齋志異》之創(chuàng)作手法“不挾恩怨”是瞞天過海的謊話。
對于《聊齋志異》與《閱微草堂筆記》之間的創(chuàng)作方法上的差異及其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在清代就有學者已有較為公允的評論。俞樾在其《春在堂隨筆》中指出:“紀文達公嘗言:《聊齋志異》一書,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先君子云: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績,未脫唐宋人小說窠臼;若紀文達《閱微草堂五種》,專為觀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不屑屑于描頭畫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臺仙館筆記》,以《閱微》為法,而不襲《聊齋》筆意,秉先君子之訓也。然《聊齋》藻績,不失為古艷,后之繼《聊齋》而作者,則俗艷而已。甚或庸惡,不堪入目,猶自詡為步武《聊齋》,何留仙之不幸也。”俞樾對二者的評倫,還是公允的。他已朦朧地看到,在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唐宋傳奇小說與魏晉志怪小說在其各自的發(fā)展里程中,有清一代已經(jīng)形成了兩座文學上的高峰。他沒有厚此薄彼,雖在認識與語言的表達上,仍然有舊時代文學觀因襲烙印,其觀點還是客觀的。
紀曉嵐在編訂《四庫全書》時,在《子部》類中,未設“志怪”小說或“筆記小說”條目,而是將其拆開設了“小說家類”。在“小說家類”中分設“雜事之屬”、“異聞之屬”、“瑣語之屬”。在“雜事之屬”類中,清代只收了十六部著作。有我們較為熟知的《讀史隨筆》、《明語林》、《聞見集》、《筇竹杖》、《今林說》、《皇華紀聞》、《硯北叢錄》等。“異聞之屬”,清代共收錄十四部著作,有《蚓庵瑣語》、《觚剩續(xù)編》、《曠園雜志》、《述異記》、《信徵錄》、《見聞錄》等。“瑣語之屬”,清代只收錄四部著作,有《豆區(qū)友傳》、《筆史》、《青泥蓮花記》、《板橋雜志》。由以上所收錄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四庫全書》中將大量的《聊齋》類之“志怪”小說全部擯棄在外。這種編纂的宗旨,在紀曉嵐的詩中,也有表露。
前因后果驗無差,瑣記搜羅鬼一車。
傳語洛閩門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其實,他所收錄的所謂的“志怪”小說,完全是按“魏晉志怪”模式收錄,凡后起之受“唐宋傳奇”小說影響的著作,一概不收錄。
對于這種收錄原則,使大批民間喜聞樂見“志怪”著作,都被擯棄,特別是《聊齋志異》。與紀曉嵐同參與《四庫全書》編篡的余集,他認為這種編篡原則是不公平的。他在《聊齋志異·序》中就說:“夫《易》筮載鬼、《傳》記降神,妖降災異,炳于經(jīng)籍。天地至大,無所不有,小儒視不越幾席之外,履不出里巷之中,非以情揣,即以理格,是沾沾者又甚于井蠡之觀。”(乾隆三十年,仁和余集)
一部深受廣大民眾歡迎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的問世,它往往代表著一個時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新潮流,在文學發(fā)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談及“唐傳奇”,不同于“六朝志怪”時說:“雖尚不離于搜奇寫逸,然敘述宛轉(zhuǎn)、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故所成就乃特異,其間雖亦或托諷喻以紓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究在文采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從這一論斷中,我們已經(jīng)亦可明了,“唐宋傳奇”在中國小說發(fā)展史上的地位。“唐宋傳奇”是“魏晉志怪”的發(fā)展,“是時則有意為小說”。看來,紀曉嵐并不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對蒲松齡《聊齋志異》的創(chuàng)作方法耿耿于懷。其實,“唐宋傳奇”小說的出現(xiàn),它為后來諸小說體例的產(chǎn)生起到了開先河的作用。
在中國文言小說發(fā)展史上,時至宋、元、明三朝,由于話本小說的興起,而文言小說相對呈現(xiàn)出式微的趨勢。這一時段的文言小說的特點:“為志怪,既平實而乏文采;其傳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聞。擬古且遠不逮,更無獨創(chuàng)可言矣。”正因為蒲松齡發(fā)現(xiàn)了文言小說創(chuàng)作上所存在的弊病,他在《聊齋志異》中所寫雖然也不外是鬼神怪異故事,但是他“描寫委曲,敘次井然,用傳奇法,而以志怪,變化之狀如在目前;或易調(diào)改弦,別敘畸人異行,出于幻域,頓入人間;偶述瑣聞,亦多簡潔,故讀者耳目,為之一新。”(《中國小說史略》之《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這是魯迅先生對蒲松齡創(chuàng)作《聊齋志異》新成就的全面評價。而魯迅先生在談到紀曉嵐文藝創(chuàng)作觀時說:紀氏“蓋即訾其有唐人傳奇之詳,又雜以六朝志怪之簡,即非自敘之文,而盡描寫之致而已。”紀氏《閱微草堂筆記》的創(chuàng)作,就是單純模仿“六朝志怪”之“尚質(zhì)黜華,敘述簡古,力避唐人的作法。”
時到清代,“志怪”小說再不改革,已趨末路。蒲松齡的出現(xiàn),也許時代賦予他的使命,他創(chuàng)作了《聊齋志異》,因而引起了許多風波與別人的誹議。《聊齋志異》的出現(xiàn)應該說是個歷史的產(chǎn)物。蒲松齡在“志怪”小說走上末路時,他大膽的將“魏晉志怪”與“唐宋傳奇”創(chuàng)作方法融為一體,創(chuàng)作出一種《聊齋志異》創(chuàng)作新藝術手法。一種新生事物的誕生,是在高呼著、吶喊著,沖破重重藩籬而來到世間。蒲松齡最好的朋友張篤慶就對他的《聊齋志異》創(chuàng)作很不理解。他給蒲松齡的詩中說:“故人詩酒遲經(jīng)歲,海國文章賴數(shù)公。此后還期俱努力,聊齋且莫竟談空。”他的好友寶應縣知縣孫蕙在給他的信中說:“兄臺絕頂聰明,稍一斂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當時,蒲松齡的處境是很困難的。他自嘆“可憐一生無知己”。對此余集在其《聊齋志異·序》中說:“同在光天化日之中,而胡乃沉冥抑塞,托志幽遐,至于此極,余蓋卒讀之而悄悄然有以悲先生之志矣。”由此觀之,紀曉嵐“質(zhì)疑”《聊齋志異》的創(chuàng)作方法,是有其歷史源淵的,我們不能怪他,但是非是要說明白的。
嚴格地說: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它就是“筆記”類,不能稱之小說,就其實質(zhì),它是宗魏晉的“筆記”一脈承序的,大其言之,稱之為筆記小說。(當然,它較之魏晉筆記有發(fā)展,這是時代的發(fā)展使然)要能稱其短篇小說這一新概念者,只能是《聊齋志異》。它為早期的、完整的完成了由“筆記小說”向古代短篇小說發(fā)展的創(chuàng)作方法全過程。對在學界有其獨具特點。有學者、專家、研究者在研究《聊齋志異》的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上認為,這一點《閱微草堂筆記》是靠不上邊的。我們承認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為成功之作,是“魏晉筆記”小說的集大成者,是清代文學中的一個高峰,但它仍未脫離“筆記”小說的窠臼。紀曉嵐是清代大文學家、史學家,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留仙之才,余誠莫逮萬一,惟此二事,則夏蟲不免疑冰。”(自然,我們也并不認為這是紀氏的真心話。)說到家,紀曉嵐對蒲松齡《聊齋志異》的創(chuàng)作方法的“質(zhì)疑”,是基于他對新生事物的不理解,對小說發(fā)展的時代理念的不理解、不接受。所以,我們在研究《聊齋志異》與《閱微草堂筆記》他們間的異同點時,首先要明確:這二者,必須從創(chuàng)作文體的概念上,給以界定。一則為古代短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高峰;一則是“魏晉筆記”小說集大成者的創(chuàng)作高峰。此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盛時彥在《姑妄聽之》“跋”中說:“時彥嘗謂先生之書,雖托之小說,而義存勸戒,無一非典型之言,此天下之所知也。”其創(chuàng)作宗旨“引據(jù)古義,具有根柢,則學問見焉。”又曰“先生出其余技,以筆墨游戲耳。”或者“夫著書必取熔經(jīng)義,而后宗旨正;必參酌史裁,而后條理明;必博涉諸子百家,而后變化盡。”這一條條引經(jīng)據(jù)典、嗜古成癖、墨守成規(guī)的老套子,是紀曉嵐創(chuàng)作的法則。盛時彥說他老師創(chuàng)作《閱微草堂筆記》是“余技”、是“游戲”,他泄漏了紀曉嵐創(chuàng)作的“天機”。自然,紀曉嵐是一位博覽群書、學通古今的大學問家,用一點文字“游戲”的伎倆,寫就一部書,那是輕而易舉的事。他與蒲松齡這位倍受生活煎熬的鄉(xiāng)間窮秀才是不一樣的。窮極生風,蒲松齡曾寫過《祭窮神文》,他如屈原一樣,發(fā)出向蒼天的質(zhì)問。
民間,農(nóng)歷除夕之夜,是多禁忌的時刻,這是一年終人們送灶神歸天之日,家家戶戶期望灶神在天帝面前美言幾句,以求得自己一家來年平安幸福。但蒲松齡在此刻卻在“祭窮神”,寫了這篇千古奇文《除日祭窮神文》,文如心聲,讀其文,使人思緒萬端,涔然而淚下。下邊摘引兩段,供諸位品讀。
《除日祭窮神文》:窮神,窮神!我與你有何親,興騰騰的門兒你不去尋,偏把我的門兒進?難道說,這是你的衙門,居住不動身?你就是世襲在此,也該別處權(quán)權(quán)印;我就是你貼身的家丁、護駕的將軍,也該放假寬限施施恩。你為何步步把我跟,時時不離身,鰾粘膠合,卻像個纏熱了的情人。
……
自沈吟:我想那前輩古人也受貧,你看那乞食的鄭元和,休妻的朱買臣,住破窯的呂蒙正,錐刺股的蘇秦。我只有他前半截的遭際,那有他后半截的時運?可恨我終身酸丁,皆被你窮神混!……。(此則實為聲討窮神的“檄文”)
蒲松齡他沒有紀曉嵐那樣的閑情逸致,他所寫的《聊齋志異》是在窮愁、在“孤憤”中完成。這些文字,是在“憤怒”、在“吶喊”、在為人間的不平而“問天”。他與紀曉嵐不是一路人。高官厚祿、養(yǎng)尊處優(yōu)的紀曉嵐躲在皇家園林里,于消閑中所寫出的東西和所要寫的東西,其味道自然不同。魯迅先生說:血管里流出的是血。
下邊,我們再溫讀一遍蒲松齡為他《聊齋志異》所寫的《序》的兩個段落!以此,作為我文章的結(jié)束吧。
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為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魍魎見笑。
……
獨是子夜熒熒,燈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為裘,妄續(xù)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吊月秋蟲,偎欄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呼!
(責任編輯李漢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