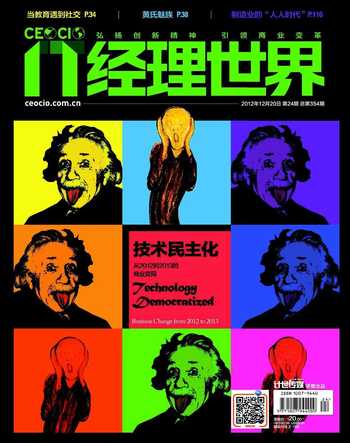基尼系數與分配杠桿
劉西曼
近兩年來,在貧富差距量化研究方面引起最大影響的人物中,包括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和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甘犁。前者提出一個引發廣泛討論的“灰色收入”概念,并給出了灰色收入與統計收入之比達90%的驚人數據;而后者則主要圍繞入戶調研展開,特別是分析了中國的實際失業率高達8.1%,近乎官方數據一倍。這兩大數據,之所以能夠引發廣泛討論,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確實做了比較扎實的研究,內容較為全面;也因為,這非常符合媒體的喜好。
甘犁報告指出,中國收入最高的20%的人控制著68.4%的收入,收入最低的20%的人僅控制著0.5%的收入;即便是在美國,收入最高的20%的人也只控制著50.3%的收入,收入最低的20%的人控制著3.4%的收入。由此導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61,比此前普遍估算出的0.44要高很多。
那么,如果我們重新梳理一下,造成偌大貧富差距的全面因子何在?
財富創造杠桿與財富分配杠桿
多勞多得,天經地義——你創造了更多財富,理應拿到更多,這也是市場經濟生生不息的動力。比如,一個企業家,白手起家創辦了一家企業,創造了源源不斷的利潤,從中拿到更高的“薪酬”、乃至“股權”,在目前已經幾乎成為“普世價值”。
這種表面如真理的說法,其實經不起推敲:第一,企業家帶領企業創造財富的時候,同時使用了工人、原材料、金融資本等生產資料。其中,原材料從根源上說是國有的、或者是全民所有的公共資源,而金融資本則由更多人的存款、信托等組成,企業家借助這三大資源創造了財富——或者說使用了杠桿,把自己的能力最大化了。
在這個過程中,企業為資源面向國家交付了稅收,為銀行借貸和信托等支付了利息,為功能支付了工資——剩下的歸屬管理層和股東有什么不對嗎?問題在于這個蛋糕分配的比例。誰分的多、誰分的少,最終是博弈的結果,誰掌握著更多的權力,誰就擁有更多的分配杠桿;誰擁有更多的資本誰就擁有更多分配權。
因此,只有“均衡博弈”才能導致相對的公平,問題是均衡的博弈根本不可能。比如,官員掌握審批權、資本家掌握足夠多的資金、富二代和官二代擁有更高的起點;再如,改革開放先從沿海開始,擁有長期政策紅利;城市居民比農村居民享受更多的隱形福利;甚至說,郊區拆遷戶擁有更多地利機會;先購房的用戶擁有更多的先發優勢;所在地的資源多寡……
這種不平等是廣泛、深刻存在于各個方面的,每個因子如果恰好疊加起來,就造成了“高副帥”和“屌絲”的巨大差距:一面是身處上海、經營大企業、80年代大學畢業、享受改革紅利的50歲成功人士;一面是身處貴州大山、出身赤貧、90年代小學輟學、本地無任何資源的農民,這背后是兩個差距巨大的杠桿!
解決復雜性問題的原則
這種先天和后天的不平等,造成了巨大的杠桿,應該如何去削平?
在一次分配中,由于其分配形態是由市場博弈所產生的,看起來是“自由競爭”。但是,大家初始化資本、權力不同,這種不平等并不能靠“一次分配”自發決定;如果,這種分配,通過政府設定“最低工資標準”等方式來干預,雖然有一點作用,但是不能從本質上改變背后的杠桿權力,所以效率并不高。一個典型例子是,現在很多工廠因勞動力緊缺人工漲價,這種市場作用,遠甚于最低工資標準;反倒是以前,即便設定了最低工資,也還有各種派遣工方式來逃避。更極端的,歐洲一些國家過于強大的工會,最終還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阻礙。
那么,二次分配又如何?二次分配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的稅收調節、轉移支付等方式來實現。這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第一,政府的效率往往比較低下,而且不透明,這種分配里包含著很大的成本;第二,二次分配的原則是什么?東部創造的財富能否直接轉移到西部?第三,稅收太高,直接影響到企業競爭力和消費者的購買力。
所以,我們看到,初始化條件、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中,各自有問題的復雜性,很難找到一刀切的處理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容易形成所謂“死結”,都說改革,到底怎么改?很多地方扶貧20年,那里依然貧窮,不造血很難解決;有些地方已經脫貧,但是不愿摘掉帽子,利益使然……中國的復雜性,通過貧富差距這個問題,足以折射出來。
我們只能得到一些基本的原則:第一,必須消除初始條件不平等當中的“非客觀”因素,比如,城鄉二元的政策;第二,必須提升最底層人群的基本尊嚴水準,比如人人受教育的權利;最后,還應該設定解決問題的序列,那就是優先削除阻礙生產力發展、又導致分配不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