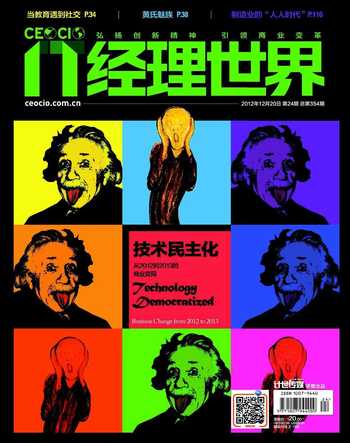制造業的“人人時代”
岳占仁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為商業和社會帶來的變革,可以用克萊·舍基一本著作的名字來概括:《人人時代》(Here Comes Everybody)。在這本書中,舍基充滿洞見地分析了高度互聯該群體動力學帶來的改變:構建群體變成一件“簡單得可笑”的事情,由此我們可以以之前無法想象的方式做很多事情,譬如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群,可以自己生產和發布新聞,可以一起編寫軟件,等等。當人們被賦予共同行動的工具,可以突破傳統組織局限的時候,接下來還會發生什么樣的事情,誰也無法預料。
而《長尾理論》的作者、《連線》雜志前總編輯克里斯·安德森已經篤定地認為,這種“大規模的業余化”、“無組織的組織力量”對傳統范式的改變和顛覆,已經從信息、商品等最早受到沖擊的領域,波及到制造業大本營。在自己的新著《創客:新工業革命》中,安德森指出,運用互聯網和最新的3D打印等工業技術,個體制造時代正在到來。他把這些運用新技術“自己動手”設計和制造產品的發明家和愛好者稱為創客(makers),并大膽斷言,正在醞釀中的“創客運動”正在將自己動手的DIY精神工業化,這必將改變現有的制造業格局,全球制造業將由此而掀開新的一頁。
而且安德森本人也跳出很多作者光說不練的窠臼,從《連線》雜志離職,全力投入自己于2009年創辦的3D Robotics公司。該公司讓科技發燒友通過網絡平臺上傳自己設計的遙控飛行器3D圖像,公司隨之利用3D打印機幫助他們做出模型,并提供制造實物所需的硬件零件和設備。3D Robotics目前已經有40多位員工,收入也達到數百萬美元。
“過去的10年,人們在找尋通過互聯網創造、發明以及合作的新方式;未來的10年,人們將這些經驗應用于現實世界中。”這是安德森關于變革趨勢的一個基本判斷。對于傳統制造業來說,變革真的會來得如此之快嗎?
“創客運動”
記者:您剛剛宣布離開《連線》雜志,對您來說,這是一個困難的決定嗎?
克里斯·安德森:不是。我現在經營著自己創業的公司3D Robotics,主要制造遙控飛行器(UAV)及相關零部件,目前已經有40多位員工,收入也達到數百萬美元,我本人對這個新事業充滿熱情。另外,此前,我承擔了太多的工作,而且還要撫養5個孩子,我的確已經沒有足夠的精力同時把這么多事情做好。
明年就是《連線》雜志20周年了。我本人擔任這本雜志總編輯達12年之久,也是時候讓一位新人來擔綱這個職位了。因為《連線》的定位就是一本革命性的雜志,要勇于承擔風險,勇于嘗試和開創新領域,它每隔一段時間久應該讓一位新的總編輯帶來新的視野、思路和創新的機會。而且,整個媒體行業目前也正處在從印刷介質向數字移動終端介質過渡的關鍵時期,雖然迄今為止《連線》在這方面的表現還是業內領先的,但是我們需要更快的創新步伐,來實現雜志概念的變革,以及與社交網絡的整合。
記者:您在《創客》一書中描繪的“創客運動”的前景非常激動人心。您做出預測的主要根據有哪些?對于傳統制造業來說,變革真的會來得如此之快嗎?
克里斯·安德森:根據首先來自制造本身的變化,現在制造業越來越走向數字化,實體物品已經成為屏幕上的設計,同時這些設計文件都可以在線共享。過去幾十年,工廠和工業設計工作室已經經歷了數字化的變革。現在,變革進一步蔓延到客戶的電腦和地下室里。而最大的變化還不是制造過程本身,而是誰在做。只要任務可以在電腦上完成,就意味著人人可以參與。
今天,技術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發明或產品設計上傳給一家服務商,將自己的想法變成現實,產品生產的數量也可以任意選擇。設計者也可以選擇利用3D打印機等功能強大的數字桌面制造工具,自己動手完成產品的制造。潛在的創業者和發明家不再需要仰仗大公司來實現自己的夢想。
變革的速度或許會超過你的想象,在發展速度上,它已經可以能夠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相媲美。例如,目前全球已經有1 000個可以分享生產設備的“創客空間”,其中僅上海一個城市就有100個。為創客提供服務的網絡市場Etsy也在逐漸完善并為更多人熟知:2011年,將近100萬賣家在這個網站平臺上銷售自己的產品,銷售額超過了5億美元。有數千個創客項目在Kickstarter等“眾投”網站上募集資金,僅2011年一年,就有將近1.2萬個成功的創客項目募集了將近1億美元(2012年預計能夠達到3億美元)。每年有10萬人聚集到圣馬特奧的“創客博覽會”分享成果,借鑒經驗。全球有數十個類似的“創客博覽會”。
C時代
記者:作為高度互聯的C時代(the Connected Era)的觀察者和思考者,您認為這個時代的本質特征是什么?
克里斯·安德森:工具的民主化,讓平常人得到了工具,讓他們得以去做更多的事情。技術革命重要的不是技術,而是人,讓個人去改變世界,放大人的能量。工具的歷史,就是人獲得更大潛能的歷史。互聯網是最新的工具,讓人們獲得更大的潛能。
同時,人們從消費者轉變為生產者。工業時代,我們不懂得和不掌握生產工具。例如廣播,我們只是廣播的消費者。現在的互聯網使得職業人士和業余人士都可以做同樣的事情,無論是付費還是免費、無論是業務還是享樂都使用同樣的網絡,它們之間沒有清楚的界限。卡爾·馬克思提出的“生產工具”,現在已經在人人手中,這充分釋放了人們的創造性潛力。
記者:在您看來,誰是數字時代最重要的商業思想家,或者說數字時代的彼得·德魯克?
克里斯·安德森:一個時代的重大思想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孕育產生,彼得·德魯克的作品也是在工業革命三百年后寫出來的。如果非要現在回答,對我來說,有兩個人很重要,一個是凱文·凱利(KK,《連線》雜志創始總編輯),另一個是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創始人和名譽主席,也是《連線》雜志的早期投資人和專欄作家)。
而從思想本身而言,只有三個思想算得上是數字時代以來的重大思想:點對點(peer-to-peer)、開放源代碼(Open Source)和網頁排名(PageRank)。
社交網絡和學習
記者:您對社交網絡怎么看,是一個重度用戶嗎?
克里斯·安德森:很多人都覺得自己需要更多的社交網絡,我卻覺得自己需要更少的社交網絡。因為我覺得自己早已經“社交過度”了。我在用Twitter,因為這樣別人就可以跟蹤(follow)我。我不用LinkedIn;我也算不上是Facebook的用戶,只是偶爾登錄,主要是為了看看我的孩子們最近在干些什么。我不會去查看Facebook的收件箱,因為我日常用的郵箱每天都會收到500封郵件,這已經快讓我瘋掉了,我再也不想給自己增加一個新的收件箱。
虛擬的社交網絡越多,面對面的社交就愈加顯得重要。我的每一個創意的產生,都是來自于與他人面對面的交流,而不是來自網絡上。
記者:除了面對面的交流,您還有什么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例如看書?
克里斯·安德森:我看的書也很少,每年大約6本。大約有10多年沒有看過科幻小說了,現在又開始看,今年看了Neal Stephenson的一本舊小說,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別人對未來的預測和設想。
我要看的是那些有真正深刻的洞見,能夠從根本上改變我們世界觀的書,這種書大概兩年能夠涌現出一本。例如,《居家》(At Home: A Short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by Bill Bryson)和《思想的未來》(The Future of Ideas: The Fate of the Commons in a Connected World by Lawrence Less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