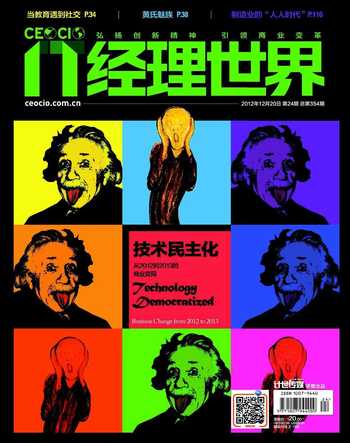創(chuàng)新:環(huán)境為王
克里斯蒂娜·霍莉


25年前,我效力于制造航天飛機(jī)主引擎的高級(jí)團(tuán)隊(duì),當(dāng)時(shí)看到一名同事努力地想引入一項(xiàng)新技術(shù)。他負(fù)責(zé)研發(fā)一項(xiàng)激光焊接技術(shù),以取代過分繁瑣的電子束技術(shù),后者在損耗價(jià)值上百萬美元的部件。但由于車間工人反對(duì)這項(xiàng)技術(shù)變化,他那個(gè)可能更好的方法結(jié)果被拋棄了。那是我頭一次看到創(chuàng)新工作因環(huán)境而失敗,我永遠(yuǎn)不會(huì)忘記。
自那以后,尤其是在兩所大學(xué)領(lǐng)導(dǎo)研究項(xiàng)目商業(yè)化的工作期間,我一再看到圍繞大多數(shù)創(chuàng)新工作的合作伙伴、資源、基礎(chǔ)設(shè)施和文化規(guī)范組成的復(fù)雜系統(tǒng)在如何影響創(chuàng)新結(jié)果。在如今這個(gè)復(fù)雜的、迅速變化的時(shí)代,如果創(chuàng)新者忽視了環(huán)境,將會(huì)自陷危險(xiǎn)。今年的創(chuàng)新類最佳商業(yè)書籍有助于緩解這個(gè)風(fēng)險(xiǎn),它從三個(gè)不同但互為補(bǔ)充的視角分析了環(huán)境。
創(chuàng)新生態(tài)系統(tǒng)
索尼公司曾交付第一款真正切實(shí)可行的電子閱讀設(shè)備,卻沒有易于訪問、內(nèi)容完備的電子書商店,可以說因?yàn)楹鲆暛h(huán)境而嘗到了苦果。正如達(dá)特茅斯塔克商學(xué)院的戰(zhàn)略學(xué)教授羅恩·阿德納(Ron Adner)指出的,得益于與眾多圖書出版商結(jié)為合作伙伴,加上出色的內(nèi)容平臺(tái),亞馬遜晚來一步、質(zhì)量較差的Kindle迅速超越了索尼的電子書閱讀器,成為市場霸主。
阿德納在其《廣角鏡頭:新的創(chuàng)新戰(zhàn)略》(The Wide Lens: A New Strategy for Innovation)一書中提供了一種方法和一套工具,幫助企業(yè)免于重蹈索尼的覆轍。這本書的風(fēng)格和格式頗似其他圖書,比如杰弗里·摩爾所著的《跨越鴻溝》,以及吉姆·柯林斯所著的《從優(yōu)秀到卓越》,條理清晰的章節(jié)穿插著無數(shù)個(gè)案例研究,旨在幫助讀者們從全新的視角考慮企業(yè)自身——這里是指企業(yè)創(chuàng)新所在的生態(tài)系統(tǒng)。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描述了環(huán)境方面的兩個(gè)常見盲區(qū):“共同創(chuàng)新風(fēng)險(xiǎn)”(co-innovation risk),即不考慮將解決方案投放市場必不可少的供應(yīng)商及其他合作伙伴;另一個(gè)是“采用鏈風(fēng)險(xiǎn)”(adoption chain risk),即不考慮需要哪些廠商,才能確保最終用戶能夠充分獲得該解決方案帶來的價(jià)值。
接下來第二和第三部分重點(diǎn)介紹如何避免這些盲區(qū),首先采用阿德納所說創(chuàng)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價(jià)值藍(lán)圖”。這個(gè)藍(lán)圖確定了最終客戶、項(xiàng)目交付成果、開發(fā)解決方案所需的供應(yīng)商、提供解決方案所需的中介商和“互補(bǔ)商”,以及系統(tǒng)存在的漏洞。
盡管大家忍不住想成為創(chuàng)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領(lǐng)導(dǎo)者,但阿德納提醒企業(yè)切勿過快地踏上這條布滿風(fēng)險(xiǎn)的道路。成為領(lǐng)導(dǎo)者通常需要巨大投入,而且很遲才能獲得回報(bào),更不用說許多公司缺乏成為領(lǐng)導(dǎo)者所需的那種影響力或平臺(tái)。他深信不疑地指出,先行優(yōu)勢(shì)其實(shí)是誤解;快速跟進(jìn)對(duì)許多公司來說可能有意義得多;例如,蘋果就有意在頭個(gè)競爭對(duì)手面市多年后才發(fā)布iPod這款后來一炮打響的產(chǎn)品。
除了像Kindle和iPod這些耳熟能詳?shù)某晒Π咐猓⒌录{還舉了幾個(gè)不大知名的例子,介紹它們旨在克服環(huán)境方面障礙的創(chuàng)新型解決方案。比如說,高質(zhì)量的數(shù)字電影在電影行業(yè)似乎是理所當(dāng)然的選擇,尤其是對(duì)每家影院耗資3000美元沖印和發(fā)行影片的電影公司來說更是如此。但是影院老板們買不起放映數(shù)字影片所需要的新設(shè)備。這導(dǎo)致電影數(shù)字化推遲了10年;在這此期間,電影公司繼續(xù)支付不必要的成本,觀眾也沒有享受到觀看數(shù)字電影的好處。最后,電影業(yè)策劃了一項(xiàng)“虛擬拷貝費(fèi)”計(jì)劃,來打破這種僵局。這套體系為整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引入了一個(gè)新角色:“數(shù)字影院集成商”,它購置新的放映設(shè)備,采用先租后買的模式,安裝到各影院。電影公司為自己發(fā)行到影院的每部影片向數(shù)字集成商支付1000美元的虛擬拷貝費(fèi),以此分?jǐn)偝杀尽_@種三方共贏的解決方案為數(shù)字電影掃清了道路,并且為三維電影等其他創(chuàng)新建立起了一個(gè)平臺(tái)。
《廣角鏡頭》一書在兩個(gè)方面不盡如人意。首先是沒有提到小公司的視角,它們?cè)趶?fù)雜的創(chuàng)新生態(tài)系統(tǒng)里面很少有機(jī)會(huì)扮演領(lǐng)導(dǎo)者角色;這些公司獲得的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只能主要靠推斷而來。其次是在規(guī)劃和統(tǒng)一公司的創(chuàng)新生態(tài)系統(tǒng)方面缺乏詳細(xì)指導(dǎo)。阿德納在第一部分末尾處添加了關(guān)于這個(gè)話題的簡短章節(jié),但環(huán)境方面的內(nèi)在陷阱理應(yīng)得到更大程度的關(guān)注。
拋開這些瑕疵不說,創(chuàng)新生態(tài)系統(tǒng)顯然給社會(huì)帶來了廣泛的影響。尤其是在醫(yī)療保健領(lǐng)域,由于監(jiān)管部門、保險(xiǎn)公司、醫(yī)生和醫(yī)院的利益經(jīng)常相互沖突,因而使原本有望挽救生命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得不到采用。阿德納以電子健康檔案(EHR)為典例,作為改進(jìn)醫(yī)療質(zhì)量、降低醫(yī)療成本的一個(gè)重要組成部分,EHR照理多年前就需要在美國普及開來,但事實(shí)上沒有,這主要是因?yàn)閱?dòng)這套系統(tǒng)需要大筆投入。在得到美國聯(lián)邦政府推行的新激勵(lì)措施的支持后,電子健康檔案只是現(xiàn)在才開始流行起來。
能源行業(yè)是另一個(gè)領(lǐng)域,因?yàn)閯?chuàng)新的好處對(duì)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現(xiàn)存者來說還不夠吸引人,因而無法推動(dòng)大規(guī)模變化。阿德納深入剖析了仍是新興產(chǎn)業(yè)的電動(dòng)汽車行業(yè),為推動(dòng)這個(gè)行業(yè)發(fā)展出謀劃策,這些都值得稱道,也值得政策制定者們關(guān)注。
移植創(chuàng)新
在《反向創(chuàng)新》(Reverse Innovation: Create Far from Home, Win Everywhere)一書中,瓦杰·戈文達(dá)拉揚(yáng)(Vijay Govindarajan)和克里斯·特林布爾(Chris Trimble)提出了一個(gè)令人信服的觀點(diǎn),認(rèn)為公司不僅要放寬鏡頭(拓寬視野),還要把目光轉(zhuǎn)向全然不同的環(huán)境:發(fā)展中經(jīng)濟(jì)體的環(huán)境。許多公司對(duì)新興市場的機(jī)會(huì)清楚得很,但它們也明白適用于芝加哥和波士頓的機(jī)會(huì)并不總適用于上海和班加羅爾。
這導(dǎo)致一些高管得出錯(cuò)誤的結(jié)論:應(yīng)該等到這些市場比較成熟,準(zhǔn)備接受自己的產(chǎn)品和服務(wù)時(shí),再進(jìn)入新興市場。但作者提醒,這種觀念會(huì)導(dǎo)致許多公司錯(cuò)失獲得增長的寶貴機(jī)會(huì)。它們甚至可能面臨更大的風(fēng)險(xiǎn):在本土市場被來自他們所忽視的新興市場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一舉超越。
兩位作者表達(dá)的主題思想是,在未來幾十年,發(fā)展中國家將是創(chuàng)新的誕生地,倒不是由于那里的人力成本較低。他們提醒讀者:“主要競爭對(duì)手并不是多年來你一直追趕的對(duì)象,而是你之前聞所未聞的對(duì)象。”他們列舉了許多案例,比如巴西航空工業(yè)公司(Embraer)、墨西哥西麥斯集團(tuán)(Cemex)和印度的汽車制造商馬恒達(dá)(Mahindra & Mahindra)等,這些公司正在發(fā)達(dá)市場迅速拓展。
幸運(yùn)的是,作者沒有長篇累牘地描述世界末日的場景。相反,他們概述了一種務(wù)實(shí)的方法,讓發(fā)達(dá)國家的企業(yè)能夠獲得“反向創(chuàng)新”的好處——也就是說,這種創(chuàng)新先在新興經(jīng)濟(jì)體開發(fā)出來,然后“上溯”到比較成熟的市場。
兩位作者一開始描述了新興市場里面蘊(yùn)含著大量創(chuàng)新機(jī)會(huì)的五個(gè)“需求缺口”(needs gap):性能、基礎(chǔ)設(shè)施、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監(jiān)管問題和文化偏好。比如說,新興市場的客戶們常常愿意犧牲性能,以換取較低價(jià)格。因此,如果公司提供的產(chǎn)品,性能比其為發(fā)達(dá)國家設(shè)計(jì)的產(chǎn)品低5%%,但價(jià)格便宜15%,就有望獲得大好機(jī)會(huì)。不過,僅僅提供現(xiàn)有產(chǎn)品的精簡版無法獲得大好機(jī)會(huì);這需要從頭開始的創(chuàng)新工作。
而反向創(chuàng)新是這樣開始的:由于公司竭力在新興市場彌補(bǔ)上述五個(gè)缺口,它們開發(fā)的產(chǎn)品最終能顛覆發(fā)達(dá)市場,用哈佛商學(xué)院教授克萊頓·克里斯滕森的話來說就是“創(chuàng)新者的窘境。”不妨看看每個(gè)孩子一臺(tái)筆記本電腦計(jì)劃(OLPC)如何為上網(wǎng)本的問世賦予靈感,GE醫(yī)療集團(tuán)在印度為當(dāng)?shù)厥袌鲩_發(fā)的售價(jià)500美元的MAC便攜式心電圖設(shè)備如何讓自己能夠開發(fā)出一款美國醫(yī)生希望的價(jià)位合理的設(shè)備。
當(dāng)然,面對(duì)一種新的文化讓人畏懼。幾年前,在德什潘德基金會(huì)(Deshpande Foundation)資助下,南加州大學(xué)史蒂文斯創(chuàng)新中心將學(xué)生團(tuán)隊(duì)派到了印度南部地區(qū),這項(xiàng)活動(dòng)的目的是拿出解決社會(huì)問題的變通辦法。但是學(xué)生們一到那里發(fā)現(xiàn),所有的東西都與他們的預(yù)期大相徑庭。當(dāng)?shù)鼐用裨谂?yīng)對(duì)農(nóng)業(yè)、衛(wèi)生、教育、醫(yī)療等方面的眾多問題——這些在美國已不再是問題,他們只好在不同的文化環(huán)境下開展工作。
不過令人高興的是,學(xué)生們能夠充分利用與幾十年前大不一樣的技術(shù)。在新興市場,滿懷抱負(fù)的創(chuàng)新者現(xiàn)在可以運(yùn)用21世紀(jì)的技術(shù)來處理20世紀(jì)的問題,而不必受制于發(fā)達(dá)市場的舊有基礎(chǔ)設(shè)施。因而,一支學(xué)生團(tuán)隊(duì)得以開發(fā)出一個(gè)文本短信系統(tǒng),低成本地將公眾健康信息分發(fā)到當(dāng)?shù)氐尼t(yī)療工作者——這也是我在四川或斯里蘭卡得到的手機(jī)信號(hào)可能優(yōu)于在硅谷腹地沙丘路得到的手機(jī)信號(hào)的原因。因此,新市場和技術(shù)環(huán)境為創(chuàng)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作者承認(rèn)在新興經(jīng)濟(jì)體創(chuàng)新的困難,并為克服那些困難提出了切實(shí)可行的解決辦法,這源自于他們對(duì)已成功實(shí)現(xiàn)反向創(chuàng)新的多家公司開展的研究。比如說,他們建議設(shè)立專門的本地研發(fā)成長小組(LGT)。 他們寫道,LGT是一支“設(shè)立在新興市場的小規(guī)模、跨職能部門的創(chuàng)業(yè)團(tuán)隊(duì)。”由于LGT的任務(wù)是不斷實(shí)驗(yàn),所以衡量成果的標(biāo)準(zhǔn)應(yīng)該是它學(xué)到的東西,而不是它創(chuàng)造的經(jīng)濟(jì)效益。這對(duì)習(xí)慣于以收入為衡量標(biāo)準(zhǔn)的公司來說可能是個(gè)挑戰(zhàn)。
考慮到原有的體系,讓跨國公司接受和實(shí)行反向創(chuàng)新,可能要比小公司和新興公司困難得多。但兩位作者認(rèn)為,只要大公司的試驗(yàn)取得成功,其強(qiáng)大的網(wǎng)絡(luò)會(huì)讓其最有條件在發(fā)達(dá)國家充分利用試驗(yàn)成果。
《反向創(chuàng)新》一書簡明扼要、條理清晰,但提出來的概念不完全是新概念。作者在附錄中簡要提到了幾個(gè)先驅(qū)者,但沒有提到約翰·哈格爾三世(John Hagel III)和約翰·西利·布朗(John Seely Brown),他們兩位在2005年首創(chuàng)了創(chuàng)新回流(innovation blowback)這個(gè)術(shù)語,描述了來自發(fā)展中國家創(chuàng)新的可能性。盡管存在這個(gè)疏忽,但對(duì)于想利用發(fā)展中國家的環(huán)境作為寶貴的創(chuàng)新發(fā)源地的公司而言,《反向創(chuàng)新》一書還是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觀點(diǎn)和切實(shí)可行的路線圖。
云計(jì)算環(huán)境
較之于《廣角鏡頭》和《反向創(chuàng)新》,托馬斯·科洛布洛斯(Thomas M. Koulopoulos)的最新著作《云沖浪:以一種新的角度考慮風(fēng)險(xiǎn)、創(chuàng)新、規(guī)模和成功》(Cloud Surfing: A New Way to Think about Risk, Innovation, Scale, and Success)的主題其實(shí)不是創(chuàng)新,而是影響創(chuàng)新環(huán)境的一種深遠(yuǎn)的全球性的變化——即數(shù)字云網(wǎng)絡(luò)的出現(xiàn)。想在未來幾年有所創(chuàng)新,并從容應(yīng)對(duì)技術(shù)變革,我們都得明白這種根本性的變化。
科洛布洛斯是技術(shù)研究和咨詢公司德爾福集團(tuán)(Delphi Group)的CEO兼創(chuàng)始人,他給云所下的定義是“一個(gè)不斷發(fā)展的、智能的、可無限擴(kuò)展的、隨時(shí)可用的實(shí)時(shí)集合體,涵蓋可根據(jù)需要隨時(shí)獲取的技術(shù)、內(nèi)容和人力資源”。眾所周知,云擅長提供計(jì)算基礎(chǔ)設(shè)施,讓快速發(fā)展的公司能夠幾乎立即擴(kuò)展,又不用操心大筆的前期資本支出。
但正如作者解釋的那樣,云計(jì)算只是整個(gè)故事的一小部分,云計(jì)算的范圍和影響還沒有完全呈現(xiàn)出來。科洛布洛斯解釋了這個(gè)網(wǎng)絡(luò)在如何迅速擴(kuò)展,它很快就會(huì)提供任何資源——不僅僅涉及計(jì)算資源,還涉及內(nèi)容、合作伙伴、部件、人力和來自50億個(gè)移動(dòng)設(shè)備的數(shù)據(jù)等,就像你只要撥動(dòng)開關(guān),電網(wǎng)立馬就會(huì)高效地傳輸電力。
梅特卡夫定律告訴我們,網(wǎng)絡(luò)的威力隨著節(jié)點(diǎn)數(shù)量呈指數(shù)級(jí)增長。今天,云網(wǎng)絡(luò)的節(jié)點(diǎn)數(shù)量已經(jīng)接近人類大腦中的神經(jīng)元連接點(diǎn)數(shù)量。這個(gè)巨大無比的全球大腦對(duì)我們的將來而言意味著什么?科洛布洛斯認(rèn)為,云計(jì)算將重建信息和社會(huì),會(huì)以全新的方式把人和資源聯(lián)系起來。的確,云已經(jīng)在我們帶來精益創(chuàng)業(yè)公司、“大數(shù)據(jù)”和SaaS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云在治理、隱私及信任、成本結(jié)構(gòu)及價(jià)值鏈、消費(fèi)者保護(hù)主義、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所有權(quán)以及工作性質(zhì)等方面具有更深遠(yuǎn)的影響,只不過這些影響還沒有被完全理解。
書中最值得關(guān)注的章節(jié)之一探討了云計(jì)算對(duì)商業(yè)的影響。云計(jì)算帶來了聯(lián)系更緊密、更全球化的價(jià)值鏈。科洛布洛斯還贊同阿德納的生態(tài)系統(tǒng)觀點(diǎn),他寫道:“一家公司或一個(gè)行業(yè)能否生存,與別的公司或行業(yè)能否生存休戚相關(guān)成功取決于我們剛開始明白的合作和共建。”比如說,不像在上個(gè)世紀(jì),許多公司通過垂直整合的、專有的供應(yīng)鏈獲得競爭優(yōu)勢(shì),如今競爭力取決于速度和靈活性,現(xiàn)在公司可以使用云計(jì)算來享用幾乎沒有限制的、靈活的供應(yīng)基礎(chǔ)。如今涌現(xiàn)出像E2open Business Network這樣的交易平臺(tái),不僅可以根據(jù)需要供應(yīng)部件,還能根據(jù)從云端獲得的信息來預(yù)測全球需求,并相應(yīng)調(diào)整。云計(jì)算正促使大規(guī)模生產(chǎn)向科洛布洛斯所說的“大規(guī)模創(chuàng)新”轉(zhuǎn)變,它讓大大小小的公司都能夠在全球商業(yè)活動(dòng)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云沖浪》闡明,云計(jì)算將徹底改造許多行業(yè),同時(shí)造就全新的行業(yè),但是關(guān)于創(chuàng)新的章節(jié)還不夠深入。它主要著眼于用新的“云包”(cloudsourcing)方法來解決問題,但云計(jì)算在有待發(fā)現(xiàn)的關(guān)鍵前沿領(lǐng)域有望帶來更廣泛的影響,該書卻未就此進(jìn)行探討。比如說,學(xué)術(shù)研究領(lǐng)域已開始將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從生物學(xué)擴(kuò)大到利用大數(shù)據(jù)治療疾病,從太陽能擴(kuò)大到利用智能電網(wǎng)解決能源問題。云計(jì)算給研發(fā)前沿領(lǐng)域所帶來的影響將決定我們的未來。
另外,科洛布洛斯還可以更明晰地討論云計(jì)算在如何帶來經(jīng)營模式方面的創(chuàng)新。比如說,新出現(xiàn)的共享經(jīng)濟(jì)帶來了一類全新的同行市場,用于租賃個(gè)人車輛、借用個(gè)人物品以及根據(jù)需要獲取服務(wù)。云計(jì)算正在推動(dòng)諸如此類的眾多根本性轉(zhuǎn)變,帶來了眾多的創(chuàng)業(yè)機(jī)會(huì)。
不過,畢竟本書重點(diǎn)介紹的是創(chuàng)新的新環(huán)境,意在激發(fā)讀者的想象力。這就是為什么我選擇《云沖浪》作為本年度最佳創(chuàng)新類商業(yè)圖書的原因。它不是一本“實(shí)用指南”,而是“假設(shè)分析”,大膽勾勒了未來藍(lán)圖,并提供了激發(fā)創(chuàng)新想法所需要的基礎(chǔ)。
創(chuàng)新在什么環(huán)境下進(jìn)行是許多國家和公司饒有興趣的探討話題。教育、醫(yī)療、能源及其他許多領(lǐng)域都存在創(chuàng)新方面的許多重大挑戰(zhàn),這些挑戰(zhàn)需要?jiǎng)?chuàng)新者知道如何應(yīng)對(duì)復(fù)雜而不斷變化的環(huán)境。上述創(chuàng)新類最佳商業(yè)書籍為力求讓環(huán)境為己所用的領(lǐng)導(dǎo)者指點(diǎn)了迷津。
(作者Krisztina “Z” Holly是工程師和創(chuàng)業(yè)家,曾任美國南加州大學(xué)負(fù)責(zé)創(chuàng)新課程的副教務(wù)長,這之前曾任麻省理工 Deshpande技術(shù)創(chuàng)新創(chuàng)始執(zhí)行主任。本文原載《戰(zhàn)略與經(jīng)營》季刊,由博斯公司授權(quán)刊載。沈建苗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