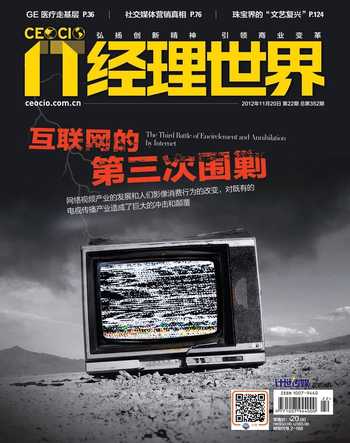何處換領道德許可證
李天田
任何被我們道德化的東西,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道德許可效應”的影響。
紐約一群無聊的研究人員發現了這樣一個事實:當飽受垃圾食品指責的麥當勞開始在菜單上增加一些健康食品時,反而引起了巨無霸、薯條等等傳統“垃圾食品”的銷量暴漲。為了搞清楚這是怎么一回事,這群研究人員模擬開設了一家餐廳,給人們提供不同的菜單,來觀察人們的反應。他們發現,當菜單里有健康沙拉可供選擇時,人們就更有可能選擇那些最不健康的食物。為什么?
斯坦福大學的教授凱利·麥格尼格爾指出,研究人員在進行一些平行的心理學、行為學研究時,發現了奇怪但是相類似的行為軌跡:比如,和那些記不起自己曾經做過善事的人比起來,有行善經歷的人在慈善活動中捐的錢要少60%;甚至僅僅是考慮向公益機構捐款,而不是真的付出了現金就足以讓人們產生去商場購物的沖動了。而在另外一項針對環保理念的研究中,人們發現選擇購買環保商品的人更容易在之后的測試中撒謊,以便因回答正確而拿到獎金,他們也更容易從裝報酬的信封里面偷錢。那些因為花了錢去種樹以中和自己碳排放的人,反而比一般人更容易選擇大排量的汽車。
不不不,借我一副狗膽我也絕不敢與環保主義者、慈善家們為敵。我們不是在說慈善或者環保或者健康,我們要說的是心理學上的一種現象,叫做“道德許可”。這在某種程度上很好地解釋了人們為什么不能做到“知行合一”的心理機制。簡單來說,當你認為自己在做善事(或者好事)的時候,你會感覺良好。這就意味著,因為你認為自己品德高尚,所以不會質疑自己的沖動,反而比一般人更可能相信自己的沖動,而沖動恰恰會致使你做壞事。任何讓你對自己的美德感到滿意的事,即便只是想想你做過或者將要做的善事,都會讓你不自覺地給自己一點“獎勵”。比如說,你因為花錢種樹做環保而自我感覺良好,因此,你就更容易在買車時選大排量的,因為你會在潛意識里給自己的善行一點“獎勵”。任何被我們道德化的東西,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道德許可效應”的影響。什么叫道德化呢?就是脫離行為本身,人為地給事情賦予“善”、“惡”或者“好”、“壞”的正反標簽。
當站在麥當勞柜臺前的人們看到、想到了健康沙拉,那么他們就覺得自己已經獲得了一種餐桌上的“道德許可證”,他們就會立即給自己一點“小獎勵”:放縱自己的沖動,去吃垃圾食品。
道德許可效應是如此的影響廣泛,所以,我建議中關村的辦證小廣告里應該把辦理“道德許可證”趕快納入業務范疇。既然是“想一想”就能發揮作用,那么,我們就更應該對各式各樣的“理念”特別是理念提出者保持警惕,因為他們已經充分地“想”到了自己的美德,接下來就是他們放縱沖動、謀求補償的時候了。
比如,看到有的互聯網企業老大發出公開信,要求在公司里提倡狼性文化,引起一片嘩然。為什么?我認真拜讀了這封信,發現其中最主要的篇幅是在講創新、保持活力、提高整體競爭力等等,這些都是很好的目標。但是,一旦用“狼性”這個理念,壞了,這就拋棄了目標本身,而是把工作行為和工作方式道德化了,有了“好”、“壞”的分別和對立。接下來,就是“道德許可效應”發揮作用了:因為強調了某種貌似強大積極的理念,因此,就允許自己開始“自我補償”——比如把手伸的太長,嚴重干預員工的私生活;比如放縱自己在商業模式上的作惡。
與此相類似的,還常見某些公司提倡感恩文化。但是據我觀察,凡是老板酷愛宣傳感恩文化的公司,往往卻是不大容易合作、上下級關系不太和諧的公司——因為自認為在感恩方面做得好,因此就給自己換領了道德許可證——許可自己對他人刻薄一些、怠慢一些。
如何防范這種帶著美好愿望卻總是導致作惡的道德許可效應呢?心理學家們認為至少有兩點是值得企業管理者高度注意的:
第一是關注目標本身,而不是包裝目標的理念。目標是具體的、有標準、可衡量的,是就是,非就非。但理念卻是灰色的,輕易被人們貼上善或惡、對或錯的標簽。本來追求實現目標無可厚非,但一貼上理念的標簽,往往就會把各種手段道德化。目標反而扔在一邊,類似整風運動的公司政治盛行。
第二是關注行為,而不是糾結動機。公司是一個“半公開場合”,不同的人們聚集在這里一起工作,就像是修建一座商業巴別塔。人們真正可被觀察和改變的,是他們的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行為即結果。但動機則是極私密的,對行為的評價是有效或者無效,對動機則很容易因為文化差異而標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