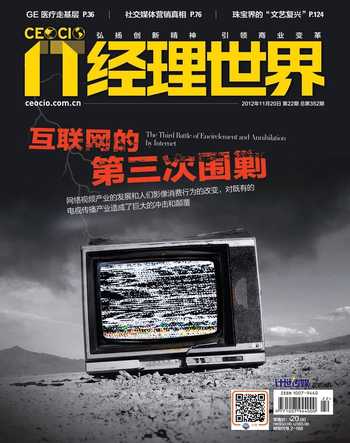激光妄相
閆鑫荻



看起來(lái)真實(shí)存在,走進(jìn)去卻虛無(wú)一片,各種新材料帶來(lái)的奇妙效果是李暉的拿手好戲。《金剛經(jīng)》言: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李暉相信好的藝術(shù)和禪宗一樣“直指人心”、無(wú)需解釋。創(chuàng)作于他而言是心無(wú)旁騖的修行,作品于觀眾而言也是換個(gè)角度看再熟悉不過(guò)的陌生世界。
一輛包扎嚴(yán)密的汽車,因?yàn)槌鲞^(guò)車禍所以傷員一樣地纏滿白色繃帶,全身煙霧氤氳,像是要燃盡自己。沒(méi)有火,沒(méi)有氣味,沒(méi)有灰燼,明亮如輪回之光的煙霧始終升騰繚繞,不生不滅,不增不減。這件激光裝置作品本來(lái)想叫“無(wú)題”,每個(gè)人對(duì)它都有自己的解讀,是涅槃,是新生,是訴泣,是靈魂出竅……后來(lái)創(chuàng)作者李暉還是給了他一個(gè)名字——《游離》。
《游離》在德國(guó)曼海姆美術(shù)館和美國(guó)邁阿密都展出過(guò),盡管西方觀眾不了解李暉的背景和風(fēng)格,但無(wú)一都有所觸動(dòng),而國(guó)內(nèi)的觀眾更是在網(wǎng)絡(luò)上傳播這件神奇的作品,無(wú)動(dòng)于衷的不多。其實(shí)“懂”是一個(gè)極其自然的狀態(tài),無(wú)需掉書(shū)袋,無(wú)需知典故,更無(wú)需像評(píng)論家那樣能夠?qū)ψ髌诽咸喜唤^,任何語(yǔ)言、文字在“心領(lǐng)神會(huì)”面前都顯得多余。
“我覺(jué)得打動(dòng)人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你做出的東西他覺(jué)得很陌生,從形式到內(nèi)容都感覺(jué)到新鮮,眼前一亮必然心頭一動(dòng);還有一種是在他已知的范圍內(nèi)你能做到極致,極致在這里可能是形容一種真實(shí),你也會(huì)震驚甚至接受不了。比如你們雜志《后人類想象的時(shí)代》里藝術(shù)家做的那些似人似獸的怪物,其實(shí)我們?cè)陔娪袄锟赡芏家?jiàn)過(guò)類似的生物,但藝術(shù)家把它做得極其真實(shí)地放在你面前,光看雜志我相信就有很多人驚著了。現(xiàn)實(shí)和想象其實(shí)差距非常大。每個(gè)人的腦子都是一個(gè)方盒子,里面裝了很多東西,當(dāng)你遇到了你盒子里沒(méi)有的東西時(shí),就想容納進(jìn)來(lái),這一瞬間是很打動(dòng)人的。”李暉對(duì)本刊記者說(shuō)。
他說(shuō)出“動(dòng)人”的時(shí)候,我忽然覺(jué)得這是一個(gè)很古典的詞匯,在近20多年中國(guó)當(dāng)代藝術(shù)里,我們?cè)谀切┓?hào)或?qū)憣?shí)的藝術(shù)作品面前體驗(yàn)過(guò)犀利、猙獰、叛逆、拷問(wèn)、冷漠等等,如果沒(méi)有和藝術(shù)家同時(shí)代的背景經(jīng)驗(yàn),我們很難輕易理解作品的真正內(nèi)涵。
不能否認(rèn)的是,國(guó)內(nèi)當(dāng)代藝術(shù)一直以來(lái)普遍的詬病是“艱澀”,藝術(shù)家似乎總想在肉體和精神之間找到最短的溝通路徑,卻始終擺脫不了自我的拗口和符號(hào)化的情緒。1977年出生的李暉已經(jīng)帶著新生代的態(tài)度了,反映現(xiàn)實(shí)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一部分,卻也是某種束縛。
李暉稱自己這一代“是脫離現(xiàn)實(shí)的,這往往能表現(xiàn)出一種本質(zhì)性的東西,因?yàn)楝F(xiàn)實(shí)是假象,每一個(gè)瞬間都在變化,現(xiàn)實(shí)會(huì)讓我們一葉障目,所以表現(xiàn)現(xiàn)實(shí)的作品都是不深刻的”。如果說(shuō)“物隨心轉(zhuǎn),境由心造”的話,眾生無(wú)邊無(wú)盡的欲念和妄想倒也很契合眼下這個(gè)日新月異且碎末化的時(shí)代。
并未深入研習(xí)過(guò)宗教和哲學(xué)的李暉在聽(tīng)到自己的觀點(diǎn)和佛經(jīng)論述有相同之處時(shí),略顯得詫異。“最高的智慧在古代哲學(xué)體系里早就成熟了,我在主題上其實(shí)更回歸了過(guò)去,中國(guó)自古以來(lái)就不是寫(xiě)實(shí)主義的,我們這一代得更多地琢磨這些事,我覺(jué)得這些是偏永恒些的。”
李暉最終給作品起名叫《游離》,意在更多的智慧層面的思考,當(dāng)觀眾被作品打動(dòng)之后再看到名字,就會(huì)和藝術(shù)更有默契。這也是盡管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出自于體悟的靈感,都可以叫“無(wú)題”,但他還是會(huì)沉下來(lái)認(rèn)真給它們起個(gè)名字的原因。
按照當(dāng)代藝術(shù)的國(guó)際化趨勢(shì),作品的區(qū)域分割、思維方式的分割越來(lái)越淡化,人類面對(duì)的越來(lái)越是同一個(gè)問(wèn)題。“我看西方大師的作品,都是用我的思想我的視角,其中沒(méi)有任何妨礙,同樣我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做展覽,得到的反饋也幾乎沒(méi)有地區(qū)性的差異,我很少對(duì)作品做解釋。”
2003年,即將從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雕塑系畢業(yè)的李暉,利用報(bào)廢的汽車做了件雙頭車——《改裝吉普——順流逆流》,在當(dāng)代藝術(shù)圈嶄露頭角,作品今天看起來(lái)還有些驚心。當(dāng)時(shí)他的下一步要么是繼續(xù)做汽車系列的解構(gòu),很吸引眼球,但被李暉認(rèn)為只有死路一條,要么重新開(kāi)發(fā)思路。當(dāng)年市場(chǎng)上涌現(xiàn)了亞克力、LED等很多新材料,于是有了李暉的下一步坐標(biāo)式作品《琥珀》系列。作品都是透明的,很有空間感,采用里外兩個(gè)造型,“這兩個(gè)形是一種對(duì)話,也是一種沖突。”
2006年李暉在迪廳發(fā)現(xiàn)了激光,一束綠光掃過(guò)來(lái),“我當(dāng)時(shí)就覺(jué)這束光特別理性,跟一根棍子似的,這一定能做作品。”隨后出了《籠子》,用綠色激光做成監(jiān)獄似的籠子,“看上去是實(shí)際的固體,但你又摸不著,一摸就消失了,很受歡迎,好多人在里面玩。”后來(lái)李暉一直思考這種材料,發(fā)現(xiàn)煙霧和激光能產(chǎn)生一種更迷離的感覺(jué)。“這時(shí)我已經(jīng)跳出了材料的屬性,想表達(dá)一些精神的東西了。”隨后有了《游離》。
李暉是國(guó)內(nèi)不多見(jiàn)的在新技術(shù)新材料領(lǐng)域苦心鉆研的藝術(shù)家,他曾說(shuō)過(guò)“科學(xué)完全能做到讓藝術(shù)更永恒、更偉大”。但是他的作品并不會(huì)拘泥在技術(shù)中,“一切都在服務(wù)于我的表達(dá),當(dāng)一些技術(shù)問(wèn)題實(shí)現(xiàn)不了的時(shí)候,就可以向創(chuàng)作妥協(x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