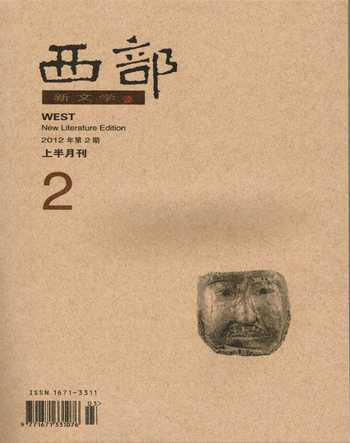魔術工業(yè):約瑟夫.布羅茨基
2012-04-29 09:04:02德里克.沃爾科特
西部
2012年2期
德里克.沃爾科特
一
“八月,”一位俄羅斯移民詩人向我解釋,“是一個說俄語的男人,”“因此當你在詩里說‘女仆,八月……他抱怨。”在俄語里,月份有性的區(qū)分。名詞有陽性或陰性詞尾,但除非在擬人的情況下,月份只是名詞。當然,在田園生活傳統(tǒng)中,月份有傳統(tǒng)的化身。五月是陰性的,一位身著白衣的白皙女子站在開滿白花的草地里;六月的玫瑰在雷聲中顫動,葉片舒卷,向她的情人敞開心扉;十二月是個毛發(fā)灰白,胡須如冰柱的老人。但這些化身只是月歷意象,并非語法的。在俄語里,如果八月是一個男人,對這位流亡詩人來說,他是做什么的呢?革命招貼畫中一個手執(zhí)干草叉,長著淺黃色頭發(fā)的工人?
我把八月視為一個女廚師,她黑檀木似的頭顱包在白方巾里,在臨海的一座房中從曬衣繩上抽打床單,這種方式就像暴風雨在颶風的月份從加勒比海的地平線驅趕航船一樣。在這個月的刺耳聲里,有干草的沙沙聲和洗好的衣服突然抖動的聲音,以及浪花拍岸的絲絲聲,但是如果這個英語單詞可以將它的陰影轉變成俄羅斯的風景,轉變成被想象的夏天,我就可以把它擬人化為男人或女人。八月,這個男人,本應成為契訶夫戲劇中那些厭倦的,無聊的知識分子之一,用一種像樹葉一樣令人平靜,甚至催人入眠的聲音說話,但八月也是《海鷗》中的尼娜,一個菜粉蝶似的姑娘,系身于特里戈林的肘上,在一個受驚的湖畔。對我來說,理解米哈伊爾的痛苦或對月份名字的惱怒是不可能的,但它是隨著翻譯而產(chǎn)生的廢墟之一。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