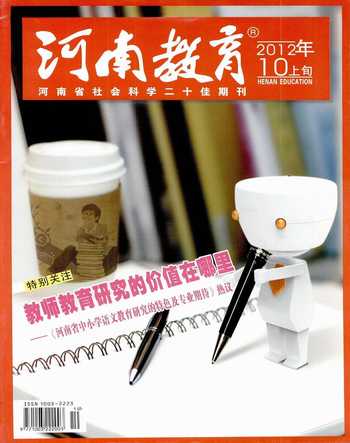語文課應有學術含量
毛榮富
提到“學術”,有人便會覺得那是高校的事,其實正如于漪老師所說“任何一個領域都是有學術的”。所謂學術含量,亦即思想含量、文化含量、知識含量。語文教材包羅萬象,本身就蘊含學術,對其進行研究,便可有獨特的發現和新的認知。日本、臺灣就明確要求中小學教師應是善治學、有學問的“學者型”人物。上海市徐匯區早在2007年就在普教系統提出“讓教育充滿思想,讓教學蘊含學術”,而且至今已辦了五屆“學術節”。在語文教學飽受詬病的今天,蘊含學術當是語文教學的不二選擇。
一
上個世紀50年代末,我上初中,語文老師姓鐘,人稱“老夫子”——人雖老,但精神矍鑠,有學者氣質。一次,他給我們上杜甫的《石壕吏》,以講故事的方式講起了杜甫之死。
“你們知道杜甫是怎么死的嗎?”他上來這么一問,就把我們給吸引住了。
——告訴你們,被稱為“詩圣”的他是餓死的,或者說是吃得太多而撐死的。可以說,饑餓伴隨了杜甫一生。在流離失所的歲月里,他拾過橡栗、挖過野芋,輾轉掙扎到四川時,已經一身是病。離開四川后,他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圍困,連續餓了9天,接近生命的底限,只是因為有了水,生命才得殘喘。然后一位頗有人情味的縣令送來了美酒和烤牛肉,對于餓極了的杜甫而言,可謂是難得的佳肴了,于是他暴飲暴食,啖肉飲酒,結果,當晚而卒,時年59歲。世人皆嘆他死相難看,那縣令好心辦壞事。依我看,人固有一死,他死得極有福氣啊。死神來帶走杜甫的時候,他大概是撫髯長笑,了無遺憾。
鐘老師還說,杜甫7歲學詩,15歲揚名,一生不得志。即使努力經營,做的小官也不足以養家,小兒子也慘被餓死,正因飽嘗生活之苦,他憂國憂民,詩風沉郁頓挫,影響深遠……
這番話激起我心靈的波瀾,一個真實的杜甫仿佛出現在我的眼前,這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上大學后,讀的書多了,方知鐘老師關于杜甫之死的說法與許多杜甫研究者的看法基本一致。現在想來,這大概要算是我最初聽到的具有學術含量的課了。
語文課上,恐怕再沒有人會這樣向學生介紹杜甫了,取而代之的是概念化的千篇一律的所謂作者介紹,這正是語文課的悲哀。在課堂上提供一些相關的新鮮、感性的知識給學生,不僅不是灌輸,還具有啟發意義。
二
我國香港就一直要求中小學教師“善治學,學識豐富”。
我曾隨上海市語文教師代表團去香港講課。我們一行人也聽了他們的一堂課,上的是朱自清的《背影》,授課的是位資深教師。
《背影》開篇就說:“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事也交卸了。”講課的宋老師上來就說,“父親”的差事因何而“交卸”,“祖母”又因何而“死”,文中沒有交代。其實倒是應該弄清楚的。
他說,朱自清父親朱鴻鈞在徐州當榷運局長的時候,娶了兩房姨太太。原先老家的潘姓姨太太得知此事,便跑到徐州大鬧。這一鬧就把朱鴻鈞的“差事”給鬧得“交卸”了,朱自清的“祖母”也因此一病不起。
宋先生說,出于“為尊者諱”,朱自清自然對這些事欲言又止,但若想更深刻地理解散文名篇,更深刻地理解其中包含的人生的沉重與感傷,就不可不對這些背景材料加以重視。朱自清與父親感情的疏離,不只是由于父親的情感“出軌”,還在于父親對其原配夫人的態度。朱自清的原配夫人是揚州名中醫的獨生女武鐘謙。朱自清寫于1923年的小說《笑的歷史》中的“少奶奶”就是以武鐘謙為原型的。“少奶奶”年少時就特別愛笑,但嫁到婆家來還“愛笑”,可就成了“不守婦道”的證據,尤其是當家庭開始衰敗,你還“愛笑”,則為公婆所不容。一個原本活潑之人,變得性情抑郁,人也瘦了,“身子像一只螳螂——盡是皮包著骨頭……哭是不會哭,笑也不會笑了”。據說,朱自清父母讀了這篇小說,“很不高興”。武鐘謙后來于1929年死于肺病。
問題的關鍵是,為什么朱自清在寫《背影》的時候,竟原諒了父親,并開始感念他的“好”?寫《背影》時的朱自清處于怎樣的人生階段,又面臨什么樣的人生困境呢?查看朱自清當年日記:“晚與房東借米四升……又向榮軒借六元……三弟來信催款,詞甚鋒利,甚怒,骨肉之情,不過爾爾……向吳微露借款之意,他說沒有……當衣四件,得二元五角。連日身體頹唐,精神也惶惶不適,甚以為慮……向公愚借六元,愧甚。”朱自清先生不善于操持生計,加以子女多,生計上左支右絀,十分艱難。這似乎也使他絕少能體會到兒女繞膝承歡的天倫之樂,更多的是厭煩,這種感覺在他的散文《兒女》里不難找到。
宋先生說,朱自清正是在體味了生存之艱難,對生活感到無力的時候,開始了對父親的諒解與感念,并在《背影》里以藝術的方式表達出來。“他少年出外謀生,獨立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這樣的句子里有對父親能力的深佩,更有朱自清自己的深愧、自責與嘆息。最后,宋先生強調說,區區千把字的《背影》之所以厚重,之所以感人至深,不能簡單地概括為“父子情深”,而在對父親諒解與感念的背后,一個中年男人的愧悔與嘆息,是面對生活的無力感與滄桑感,是人生的沉重與感傷。
宋先生講得很動情,分明是在讓聽課者分享他的知識、他的感悟啊!現在的語文課堂上討論成風,好像不討論就不能上課,而我認為,課堂討論有時看似熱鬧,其實只是徒耗時間和精力而已。沒有知識的支撐,沒有廣泛的閱讀作為基礎,泛泛的討論終究是淺層次的。宋先生的課并沒有讓學生去討論,卻講得很有深度和感染力,等于給了學生一把理解課文的鑰匙。
下課之后,我稱贊他的課講得好,他復印了有關資料送給我,交給我的時候說了一句:“這都是心血啊!”我很理解他所說的。圍繞課文用心收集有關資料,這應是語文教師日常要做的事。幾十年來我就是這樣做的,遇到有價值的材料,會有如獲至寶之感,運用于講課之中,課也有了趣味。
三
多年前學校招聘教師,應者甚眾,其中有一博士,試講的課文是魯迅的《<吶喊>自序》,他的課被認為是失敗的,因而被淘汰。其實,我覺得他的這堂課具有一定的學術含量。
他的課有一段堪稱精彩的“題外話”,轉述如下。
從文章中可以看出,魯迅是受了幻燈片事件的刺激而決心棄醫從文,拿起文藝的武器,喚醒國民,療救國民精神創傷的,但還有沒有其他的因素影響著他作出這一選擇呢?
我們先從魯迅到仙臺學醫的經歷說起。魯迅1902年被保送公費留學。此前的他沒有接觸過醫學。少年時,為治父病,他和中醫打過多年的交道,當初他不是為了學醫而留學,而是為了留學而學醫。這兩者是有區別的,至少可以這么說,魯迅到日本去還沒有抱定要學醫的決心。
同年的3月魯迅到了日本,先入弘文書院補習日語。1904年9月免試免費轉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學習現代醫學。該校地處偏僻鄉下,離東京300公里,是一所二流學校。魯迅選中這里,一個原因可能是他對一些留日學生俗不可耐的做派的厭煩,希望獨自過一種別樣的生活;另一個原因可能他看中的是這里沒有中國學生。至于選擇學醫的原因,他自己解釋說:“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這時魯迅的思想是把學醫當成一門手藝,將來去當一名醫生。即使是這個愿望,也談不上多強烈、多迫切。對于自己是不是適合學醫,學醫是不是一個最好的出路,他顯然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在仙臺,魯迅感到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是藤野先生。藤野先生在聽說魯迅去世半年后,寫過一篇《謹憶周樹人君》的文章,其中提到:“周君上課時雖然非常認真地記筆記,可是從他入學時還不能充分地聽、說日語的情況來看,學習上大概很吃力……在我的記憶中周君不是成績非常優秀的學生……周君在仙臺醫學專門學校總共只學習了一年,以后就看不到他了,現在回憶起來好像當初周君學醫就不是他內心的真正目標。”從藤野先生的這段話可以看出,魯迅棄醫從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的志趣并不完全在學醫上,也就是說他在確立專業時沒有考慮成熟。
我們再來看看魯迅當年的學習成績。魯迅當年的同班同學小林茂雄,保存了一份魯迅在1905年春季升級考試的“成績報告單”,單上所列各科成績如下:解剖學59.3,組織學73.7,生理學63.3,倫理學83,德語60,化學60,物理60,7門功課平均分65.6,在142人中名列第68名。而唯一不及格的解剖學,正是藤野先生教的。客觀地講,在一百多名同學中名列中等,應該說成績還是不錯的。須知,魯迅當時學習上最大的障礙是語言,老師授課、所用教材肯定都是日文,即使他非常認真努力,筆記仍有“漏記、記錯的地方”,學習仍感比較吃力。如果換了一個混文憑的學生,這種中等成績完全可以說得過去,但是作為魯迅能接受嗎?在一所二流學校得到二流成績,這不能不讓他重新審視自己的選擇——醫學是他最感興趣的嗎?是最有出路的嗎?他已經26歲了,放棄學醫而從事自己最感興趣的文藝,這才是最明智的選擇。可以說,學醫無望是他決定棄醫從文的直接誘因。
在仙臺醫學專門學校,當時只有魯迅一個中國留學生,身邊極少朋友,處處受到排擠,其苦悶和孤獨是可想而知的。即使這種成績,仍然引起一些日本同學的嫉妒。他們甚至懷疑藤野先生漏題給了他。在這種遭受歧視和屈辱的環境中,魯迅自然憤恨難忍,他本是一個內心抑郁敏感自尊的青年,又遠離家鄉,孤身在外,沒有同胞朋友,日語水平不及同學,年齡又偏大,學習成績中等,處處受到排擠。可以說,對環境的不適應是他放棄學醫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其實,他的氣質性格、知識結構、興趣愛好更適合于向文藝方面發展。
這位博士所講的至少可以讓我們清晰地看到留學日本時魯迅的真實內心。他的課體現了學術最可貴的品質,那就是培根所說的“追本溯源,探求真相”。
在分數至上者的眼里,學術是沒有尊嚴的。但我想告訴他們:學術的本質是非功利的。韓愈說,做學問“勿誘于勢利,勿望其速成”;晚清思想家魏源也說“學術之敝乃敝于利祿”。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也說:“在進行科學研究時,如將其自身作為目的來追求而不帶有任何功利企圖,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種種新的發現。”
四
那么,怎樣才能使語文課具有學術含量呢?我有如下建議。
(一)跳出窠臼,找到別樣的角度對課文進行深度解讀
比如《荷塘月色》一文,就完全可從心理角度來作審讀。作者起初“心里頗不寧靜”,但負面情緒逐漸散去,進入一個純美的自然情境,沉醉于絕美的荷塘月色之中,荷花的縷縷清香猶如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塘中的光與影組合得非常和諧,正如梵婀玲上奏著的名曲。從現實情境進入審美情境,作者的心靈得到了一種慰藉和滋潤。可見,審美是醫治情緒不適、精神不振的一味良藥。月色下的荷花顯得那樣圣潔迷人,是因為它們還閃爍著作者心靈的光澤。
學生年紀雖小,但心理壓力頗大,他們聽了我的這堂課,說《荷塘月色》使他們懂得了散步可以親近自然,審美活動則可以使心靈獲得撫慰和陶醉。有的學生甚至還感悟出:人生固然要有崎嶇小路上頂著烈日的攀登,但也應有荷塘邊披著月色的漫步。現代人的心靈常處在煩躁、焦慮和不安之中,所以更要懂得善待心靈,也應尋找自己心中的“荷塘”。
(二)舍棄面面俱到,堅持突破一點,讓教學上一個高度
講魯迅的《〈吶喊〉自序》,我曾煞費苦心地制作了一個多媒體課件,把魯迅的“夢”用一組畫面表現出來,然后分析魯迅思想發展的歷程,結果效果并不佳。后來我抓住文中“這寂寞又一天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于我太痛苦。”……由語中的“寂寞”一詞生發開去,我作了如下闡發:
古來圣賢多寂寞。愛國詩人屈原有“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寂寞;亡國之君李煜有“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寂寞;李白也有“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的寂寞。沒有寂寞,李白成不了詩仙;沒有寂寞,李煜成不了詞帝;沒有寂寞,屈原留不下名傳千古的《離騷》;沒有寂寞,魯迅也寫不出振聾發聵的《吶喊》。寂寞反映著不甘沉淪的內心苦斗和掙扎,寂寞是一種深刻,是一種探索,是一種對理想自我的尋求,它可以教會我們正確認識自我,調整自我,升華自我。耐得寂寞是眾多人杰特有的品質,是取得成功必備的心理承受能力。生活中,誰都會有感到寂寞的時候,甚至是無盡的寂寞。應該讓寂寞成為精神休養生息之平臺。——與其呼朋喚友到豪華舞廳、卡拉OK廳盡情瀟灑,還不如用讀書來排遣寂寞。因為曲終人散,依然會被寂寞包圍著。與其在寂寞中耗費青春,放縱自我,還不如在寂寞中與自己對話,學會反思反省。
(三)有疑必究,不要輕易放過教學中出現的疑問
在上《燈紅酒綠中的一潭靜水——記施蟄存先生》這篇閱讀課文時,有學生問,燈紅可以理解,而酒為什么是綠的呢?我覺得這的確是個問題,于是查閱資料,請教專家。
古詩詞中多有“酒綠”或“綠酒”:“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陶淵明)“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杜甫)“勸君綠酒金杯,莫嫌絲管聲催。”(晏殊)
其實,古代酒的顏色與現在并無多大差別,只是古代釀法比較粗糙,酒糟也沒有濾出,所以,古代把酒稱為“濁酒”,所謂“一壺濁酒喜相逢”,也就是這個道理。
因為酒糟沒有濾出,酒面上便浮有一層淡綠色的糟沫。就是這層糟沫,讓美酒有了“綠酒”之稱。三國曹植在《七啟》中說:“盛以翠樽,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這里說的“浮蟻”就是這層浮沫,因為它是綠色的,所以也稱為“綠蟻”,大致是因為這層浮沫細碎,就像一層螞蟻漂在上面,所以稱作“綠蟻”或者“浮蟻”了。這就是“酒綠”的來歷。
白居易的《問劉十九》詩中就用“綠蟻”來稱道美酒:“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在我國古代,“酒綠”就是一個實指,不含貶義色彩。但自從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三十三回中創出“燈紅酒綠”一詞后,“酒綠”從此也就蒙上了一層貶義的色彩,人們很少把它與心目中的美酒再聯系到一起了,燈紅酒綠便成了奢侈糜爛的代名詞。
當我把這些講給學生聽的時候,為他們解了惑,亦為自己增添了新知。
(責 編 涵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