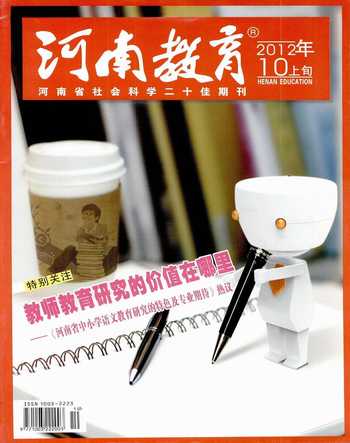教育的底線是深不可測的
王君
李迪老師閱讀我的淺薄小文,并且還寫出了真誠的商榷文章,令我非常感動。我以前也讀過李迪老師的書,對李老師是喜歡且敬佩的。但是,人與人的生命經歷和教育經歷不一樣,行走的方式不一樣,思考的角度不一樣,可能會造成教育價值觀和教育行為的迥異。讀了李老師的文章,說心里話,我是頗為震驚的。為什么呢?因為我從這篇文章中讀到了這些年來我反思最多、批判最激烈的東西:隱形的教育專制和教育粗暴。這種專制和粗暴被溫情脈脈的教育民主和愛心遮蔽著,學生看不到,老師自己也看不到。不僅看不到,而且師生還往往陶醉其中,深以為榮。
一、“法要容情”的成功案例
關于“情”和“法”,在基礎教育階段,我堅持我的看法:“情”重于“法”,“法”必須要容情。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孩子,是未成年人,是正在成長的人。我先講幾個真實的小案例。
【案例一】
校園的花房里開出了一朵很大的玫瑰花,許多人前去觀看。清晨,蘇霍姆林斯基在校園里散步,看到一個4歲的小女孩拿著那朵大玫瑰花往外走。他很想知道小女孩為什么摘花,于是彎下腰親切地問:“孩子,你摘這朵花是送給誰的?你能告訴我嗎?”小女孩害羞地說:“奶奶病得很重。我告訴她校園里有這樣一朵大玫瑰花,可她有點不相信。我現在摘下來送給奶奶看,看過后,我就把花送回來。”聽了小女孩天真的回答,蘇霍姆林斯基的心顫動了。于是,他牽著小女孩,從花房里又摘了兩朵玫瑰花,說道:“這一朵是獎勵給你的——你是一個懂得愛的孩子;這一朵是送給你媽媽的——感謝她養育了你這樣的好孩子。”
我的質疑
如果按照李迪老師的推論,我們是不是應該批評蘇霍姆林斯基“情大于法”——因為不能摘集體的花肯定是校園之“法”,是必須不折不扣地去執行的。我們是不是更應該為那個小女孩擔憂:因為她這次受了縱容,所以她長大后見到自己和家人喜歡的東西就會去占有。我們是不是更應該為其他的孩子鳴不平:與小女孩兒得到的包容和理解比較起來,他們是不是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蘇霍姆林斯基的這個學校會不會因此沒了章法、亂了規矩?
會這樣嗎?當然不會!
【案例二】
這是我自己的故事。
小學四年級時,我是個乖巧懂事的小姑娘,是老師最信任的大隊干部。當時我負責管理班費,總數目大概有十來塊錢,就是這筆錢讓我犯了個大錯誤。在那個物質極其匱乏的年代,我沒有抵擋住零食的誘惑。等到班主任胡老師催我上交班費的時候,剩下的錢已經寥寥無幾。如果交不出錢來, 我這個大隊長、好學生就要身敗名裂。我想盡一切辦法躲著胡老師,每天上學比赴刑場還要難過。
為了彌補虧空,我決定拾荒掙錢。我學著大人翻檢土沙細細尋找廢棄的鋼筋,然后像螞蟻搬家一樣往廢品收購站運。一個多月后,我終于掙夠了錢。把錢交給胡老師的那一刻,胡老師沒有說什么,只是深深地、深深地看了我好一會兒,然后才有些神秘地笑著走了。從此,我在錢的問題上再不敢大意。后來雖然經手的錢越來越多,但我再沒有挪用過一分。
我的質疑
毫無疑問,“不得占用集體財物”,貪者必罰就是“法”。如果按照李迪老師的理論,胡老師必須明確跟我攤牌,告訴我問題的嚴重性,嚴厲補催罰款并實施懲罰。否則,胡老師自己就“違”了“法”;否則,故事中的“我”因為僥幸沒有受到懲罰長大成人后就有可能成為貪污犯;否則,這就對其他有類似行為的同學不公平,班級就會大亂。
這樣了嗎?當然沒有!
【案例三】
這個故事,發生在上學期期末,主人公是我現在的校長。
期末考試之后,出了一件怪事:明同學找到他的語文老師,要求作文加分。原因是他期末考試的作文分數比期中考試還低,而他自己覺得,他后半學期學習很努力,作文字數也比期中考試時多,可是分數反而比期中得的少,這不公平。
這當然是無理要求。整個年級都是密封流水閱卷,兩次改作文的老師都不同,怎能比較?且分數已經入冊,怎么可能修改?但孩子不依不饒。于是“官司”從他的語文老師打到備課組長那兒,又打到我這個教研組長這兒,然后又鬧到學生處主任那兒,最后孩子干脆闖進了校長辦公室。校長跟明同學談了一會兒,居然拍板說:“好,就給你酌情加分吧。”校長讓我們另外給他備案一個分數。孩子流著淚高高興興地走了,我們都傻了眼。
我的質疑
按照李迪老師的理論,校長不是瘋了嗎?首先分數不能改,校長這么做是違規;其次這個要分的孩子會因為這次“得逞”而得寸進尺,從此更加不思進取,甚至帶著這樣的思維習慣和行為習慣走向社會,撞得頭破血流; 最后,因為規矩被破壞,這個學校陷入混亂,學生紛紛仿效明同學,以致局面不可收拾。
是這樣的嗎?當然不是!
事實上,經歷了這次事件后,明同學反而懂事多了。要分的事情全校再也沒有發生過。
以上都是“法要容情”的案例。類似的故事還太多太多,幾乎每一天、每一刻都在我們的校園中發生著。
“容情”也能有好的教育效果,也能成就學生。這其中的奧妙在哪里?為什么我認為李迪老師的“法不容情”的理論看起來極其符合民主社會的要求,其實在具體的教育實踐中是行不通的呢?我和她的分歧到底在哪兒呢?
二、分析我們的分歧
第一,我們對基礎教育階段教育目標和教育手段的認識不同。
我反復強調我所任教的是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學生多數不到18歲),我的言論,都是針對基礎教育階段而言。基礎教育的目標是給學生的終身成長打底子。但是,打底子并不是“打成型”,而是建立一個塑造真正雕像的“轉盤”。教育是基礎,是學生未來社會生活的準備。因此,學校不是公安機關,更不是執法部門,而是一個教化機構。它的使命就是把學生看成未來社會的公民進行培養。學生不是因為變成了公民才來學校的,而恰恰是因為不具備公民素質才來學校的。學校的任務在“教”在“導”,而不在“執法”。
第二,我們對基礎教育階段“法”的認識不同。
社會之法是“成人之法”,校園之法其實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否則法律也不會規定十六周歲之后才承擔法律責任)。校園之法其實是一種“規矩”。守規矩非常重要,但再重要它也并非教育的本質。教育的本質應該是一種培育和喚醒。這并不是說,守規矩的教育就不可以喚醒人性,而是說,把守規矩當成了目的就是對喚醒人性責任的無視。
所以,中小學基礎教育,當然要有民主,要有法制。但是,這兒的“法制”,是一種民主生活的學習和訓練,是讓學生漸漸明白,一個人應該為自己認可的東西付出努力和代價。所以,基礎教育階段的“執法”,其主要作用不是為了對學生的行為進行裁決,它更是一種學習和訓練。而且這種學習和訓練需要經歷很多階段,需要不斷地體認和內化,是一個很復雜的細水長流的過程,絕非一位老師、一個事件、一個早晨就可以完成的。這一點,導致了我和李迪老師的分歧之三。
第三,我們對學生成長路徑的認識不同。
李迪老師之所以要不折不扣地“執法”,其思維方式和成長理念在她的案例分析中表現得很鮮明,從對豪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李迪老師認為:1.一旦老師“法要容情”包容了孩子,他就會和法律法規終生對立,導致耐挫能力差,甚至會脆弱到經不起一點風浪。這里有兩個潛臺詞:一是除了法律法規的約束,孩子沒有自我體認、自我矯正、自我成長的能力。二是一個單獨的教育事件就會讓孩子成型,否定成長的多樣性、復雜性、豐富性、可能性。2.只有“外在的懲罰”帶來的“痛感”才會促進孩子成長。不懲罰,孩子就不會成長。孩子沒有自我懲罰、自我反思的可能和能力。
我覺得,這個分歧直接導致了我們對軍事化管理的認識分歧。
第四,我們對軍事化管理的認識不同。
我以為,軍事化管理和軍訓是兩個概念。學生在某段時間參加軍訓,我覺得是合理的。通過軍訓,學生會感受到一種節奏穩定、高效率、絕對服從的生活,是對他們生命體驗的有益補充。但是,日常生活不是軍旅生涯,我們培養的公民也不是軍人,而是善良、從容、幸福的自由人。“軍事化”是社會的倒退,而絕不是進步。“服從就是一切”“奉獻就是一切”等軍事化的理念,也是在根本上和社會民主、自由的發展方向相悖的。所以,一個政府,當其提倡的主流價值觀遭到挑戰的時候,其矯正方法首先就是軍事化管理,因為這樣可以最方便地對思想進行控制。總之,管理一旦“軍事化”,其背后必然隱藏著專制和暴力——不管你如何涂脂抹粉地掩飾。
那為什么軍事化管理大有市場呢?
因為簡單,因為快速!
這種管理方式,帶有正大光明的壓迫性質。你不需要問為什么,你也不能問為什么。上級要求的個性就是所有人的個性,上級提倡的目標就是所有人的目標。你只需去服從和跟隨。這種管理方式大大減少了管理者的麻煩。在戰爭中,這也許是必須的,但對于個體的成長來說這是殘酷的。
軍事化管理能夠塑造真正的人嗎?我表示懷疑。
李迪老師說學生經過軍事化管理后會很有“愉悅、自豪”感。不知道她是否經過嚴謹的調查分析,有真實、科學的數據來證明。反正,我是不相信的。學生在一段時間的軍訓之后會有新異感和成就感,這我相信。但是,一旦“軍事化”成為未成年人的一種生命常態,其扭曲人格、壓制人性的負面作用就會慢慢顯現,“愉悅、自豪”感從何而來?
我認為,軍事化管理出來的人難免有這樣的特質:他們會在有人監督時嚴格執行規則,但無人監督時會沒有規則。日本軍隊當年堪稱軍紀嚴明。可是,進了南京城,最文雅的士兵也會強奸婦女。他們嚴明的軍紀只對軍隊生活有效,而面對手無寸鐵的婦孺時,他們連人性都沒有了。
比較中西方的教育而言,中國的孩子從小夠“軍事化”了:手要背好,背要挺直,放學走路都要排隊,在數不盡的“課堂常規”中長大。而西方的孩子呢,上課躺著趴著倒著都可以,課堂看起來極其松散,跟“軍事化”邊都沾不上。可實際上現在大家都認識到中國的孩子是最不懂規矩的。所以說,“軍事化”并不能夠真正從靈魂上塑造人!通過軍事化管理,孩子們苦練苦學,完成了家長和老師定下的目標。按照規則,他們似乎成功了。可是,他們通向幸福了嗎?他們通向民主、自由了嗎?我不知道。
基礎教育中的“法不容情”是典型的“軍事化”思維。妄圖齊步走、一刀切的管理模式一旦作祟,教師的管理行為就會變形。
第五,我和李迪老師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我認為“法不容情”往往會導致教育中的假民主、真專制。
為了證明自己“法不容情人有情”的觀點,李迪老師舉出了一個依據班規罰自己跑步的案例。我認為這個案例體現了一種“軍事化思維”。
我實在不明白一個有著民主氣氛的班級怎么會定出“同學們相互監督不準上課睡覺,有一個同學在課堂上睡覺,課外活動時全班同學都將被罰跑步”的班規。這樣不符合人性、不符合常理的班規能夠通過,只能說明一點:這個班級的學生,沒有什么自由、民主的意識。李迪老師說:“民主其實是最強硬的,有時候民主也會犯錯誤,但民主本身具有糾錯能力。”“民主”要真的發揮教育效力,靠的絕不是“強硬”,而是“公平、正確、人性”。錯誤的民主會具有糾錯能力嗎?我看不會!而且還會錯上加錯!
在這樣的班規下,班里出現幾個上課睡覺的學生是理所當然的。當“民主”穿著華麗的外衣粉墨登場,干的卻是破壞民主的事時,后果自然是這樣。這不是學生“鉆空子”,而是學生對假民主、真暴力的消極反抗。
看到李迪老師罰自己跑步、全班學生跟著跑時,我感到絕望:教師為一條錯誤的班規埋單,居然得到了全班同學的“追隨”,并自己評價說“這是一個循環,一個美麗的圓”!是的,這里邊有學生對教師的敬愛,但絕不是所有的敬愛都值得贊美。真假不辨、善惡不分的敬愛比不敬愛更可怕。這樣的追隨,使我想起了“文革”時全國人民對“偉大領袖”的追隨,當年法西斯軍隊對希特勒的追隨,殺紅了眼睛的日本軍人對天皇的追隨……這個“圓”越圓滿,其弊端就越大,貽害就越大,中國離公民社會就越遙遠。
一個社會,沒有人對不合理現象說“不”,說了也沒有人敢堅持,這個社會就是畸形的社會。同理,這樣的班級也是畸形的班級。
在中小學里進行的民主教育,其核心是喚醒學生的民主意識,是告訴學生:民主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集體的強權。每個學生對民主、規則、法律這些好東西有一個基于自己成長個性的體悟過程。假如不尊重這種個體差異,在基礎教育階段也不給予學生這種體悟的足夠時間和空間,那么,所謂民主就會如同專制一樣,不過是一種由學校和教師這些“龐然大物”所秉持的不容置疑的壓迫性力量。學生雖然參與了規則的制定,但是,他們依然身處于規則之外。甚至,他們的境遇告訴他們:他們不需要體悟,他們只需要認可、服從。這樣的人,不是公民,而是奴隸。
三、教育的底線是深不可測的
李迪老師引用了很多理論,我很佩服。對這些理論我也有所耳聞。重新細細理解這些理論,我覺得恰恰證明著“法不容情”的可笑。
柯爾伯格“人的道德可以分為三個水平、六個階段”的理論告訴我們:完成這個過程,需要那樣多的水平演變,需要那樣多的階段。這絕非一朝一夕之事。從“前習俗水平”到“普遍道德原則的定向階段”,要讓受教育者體認水平提高,需要漫長的等待。在我上篇文章的案例中,我給豪這樣的期待,避免了他的逆反,并不是最終毀了規則,而是要讓豪自己從“前習俗水平”向“普遍道德原則的定向階段”進發。假定連這個“前習俗水平”都不能容忍,遑論完成“普遍道德原則的定向階段”?
基礎教育是要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來完成這一過程的,而不是用一學期、一兩周、一個早晨來完成。我們教師的困境也許是,我們在三年級或者六年級,初一或是初二,高一抑或高三,總在重復一件事:每一次有了問題都在“執法”(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三基本方式一樣),結果孩子們還和五歲的時候一樣不懂規矩!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每一回出問題,都有人想要在自己那一段兒“結束戰斗”,想要在自己那一次讓學生知道規則的厲害。可是,我們浪費了多少機會?我們等不及,我們總等不及!
蘇霍姆林斯基等得及,所以他在那個階段只保護孩子的愛心,而不去馬上告訴孩子摘花是破壞性的行為。他相信孩子到了另一個階段自然會懂得這個道理。我的校長等得及,所以他愿意給明加分,褒獎孩子的學習積極性,讓那小小的自尊之火苗熊熊燃燒起來。他相信在成長過程中孩子自然會知道“討要分數”是不可以的。如果李迪老師等得及,她就會在學生制定出“全班罰跑”的班規時及時告訴學生即使有“短平快”的效果,但這樣的班規還是不合法、不科學的,效果再好也是不能采用的。
“法要容情”不是褻瀆法律法規,而是在基礎教育階段充分考慮到各種各樣學生的成長需要,進行因材施教,個性化管理。
我的校長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在基礎教育階段,教育的底線是深不可測的。”隨著教育經歷的不斷豐富,我越來越認可這句話。
其實這句話和柯爾伯格的理論是相呼應的。人道德發展的第六階段是普遍道德原則的定向階段。處于這一階段的個體,其認識超越了法律,認為除法律以外,還有諸如生命的價值、全人類的正義、個人的尊嚴等更高的道德原則。
所有的法律歸根結底都是為人服務的。在孩子還未成年的基礎教育階段,正如李迪老師所說:“后習俗水平”應該是我們所有班主任都追求的道德水平,老師在執行那些生硬的班規、校規的同時,更應該明白如何去尊重個體生命的價值、全人類的正義、個人的尊嚴。
我深信,有了“個體生命的價值”和“個人的尊嚴”,才可能有“全人類的正義”。我想,以此為標尺,我和李迪老師會找到一個最好的交匯點。
(本欄責編 盧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