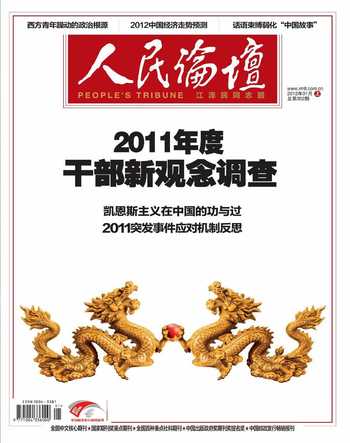話語束縛弱化“中國故事”
張維為
評述由頭2012: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近10%,經濟從一度瀕于崩潰的邊緣發展到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的奇跡。于是,中國逐漸走到了世界的前臺,成為了世界的“主角”之一。但是,由于“中國故事”內容豐富、場面宏大、情節復雜,使得“中國發展文本”的現代解讀紛繁龐雜,這其中既有“崩潰論”的噪音,也有“奇跡論”的奢談。那么,我們應如何理性地認知和客觀地分析中國的“發展文本”,全面地解讀“中國故事”的豐富內涵呢?面對西方的“奉承”或者“罵殺”,2012年應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呢?
中國的崛起是很精彩的故事
今天的中國正在進行著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的實驗。中國相對成功的經濟改革已經勾勒出了中國政治改革的大致路徑,即通過漸進、試驗和積累的方式來完成中國的政治改革。
中國人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動蕩、戰亂和革命,又經歷了30多年相當成功的改革開放,大多數中國人愿意繼續走行之有效的中國模式之路。這個模式有自己的缺點,但可以不斷完善,因為它已經比較好地結合了中國自己數千年的傳統和文化。中國人有自己的歷史傳承,中國經歷了20多個朝代,其中至少7個朝代的歷史比整個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都長。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模式對于外部世界的影響可能會越來越大。中國的經驗本質上是中國自己國情的產物,其他國家難于模仿。但是,中國模式所包含的某些理念和實踐,可能會產生相當的國際影響,如實事求是、民生為大、漸進改革、不斷試驗、“良政還是劣政”比“民主還是專制”更重要等。
中國這樣的國家崛起的規模、速度,人類歷史上沒有過,走到這一步很不容易。在歐洲,這樣的崛起時代已經打了至少100場戰爭, 當然很多是在歐洲以外的地方打的。中國沒有任何一場戰爭。我做過統計,從1840年到1978年的140年間,中國最長的太平時間沒有超過9年。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是第一次打破了這個怪圈,所以中國取得了今天的成績,很不容易。再給中國10年的穩定,中國還會給世界更大的驚喜。
一個政治體制的品質,不能只是程序的正確,而更重要的是內容的正確
眾所周知,由于種種原因,中國的崛起在西方總是很有爭議。在過去的20多年里,西方媒體經常把中國描述成一個國家政權與人民對立的國度。一些歐洲人,例如在奧斯陸的一些人,甚至認為中國就是一個放大的東德或放大的白俄羅斯,正等待著一場“顏色革命”。
這種觀點使許多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自信地對中國做了很多悲觀的預測:他們先是預測1989年天安門風波后中國要崩潰;蘇聯解體后,他們又認為中國也會步蘇聯后塵而分崩離析;鄧小平去世前后,他們又預測中國將出現大動蕩;香港回歸前,又預測香港的繁榮將一去不復返;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又預測中國將走向崩潰;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后,又預測中國將大亂。但最后這些預測都被證明是錯誤的。中國沒有崩潰,而中國崩潰論卻崩潰了。
這種反復的預測失靈提醒我們有必要學會更加客觀地研究中國這樣一個復雜的大國。如果能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那么我們會發現,過去30多年在中國大地上所發生的事情大概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經濟和社會變革:約4億人擺脫了貧困。這場變革對中國和世界都產生著深遠的影響。甚至可以這樣說,過去30年中,中國所取得的成績大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績的總和,因為世界上70%的脫貧是在中國實現的。中國所取得的成績大于所有過渡經濟國家成績的總和,因為中國經濟總量在30年中增加了約18倍。如何解釋這種成功?有人說這是外國直接投資的結果,但按人均吸引外資的數量來看,東歐國家吸引的外資比中國多得多。有人說,這是由于中國勞動力便宜,但印度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比中國便宜很多。有人說,這是因為威權政府的作用,在亞非拉地區,在阿拉伯世界,都有許多威權政府,但他們無法取得中國這樣的成就。
如果這些理由都無法解釋中國的成功,那么我們就需要新的思路。從根本上講,一個政治體制的品質,包括其合法性來源,不能只是程序的正確,而更重要的是內容的正確,這個內容就是要實現良好的政治治理,并要以人民的滿意度來檢驗。“良政還是劣政”遠比“民主還是專制”更重要,如果“民主”指的只是西方所界定的“多黨競選制度”的話。我們強調內容正確高于程序正確,這本身是中國政治傳統的一部分,目的是為了通過良政為導向的實踐來創建和完善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各種程序。
要通過自己原創的研究,擺脫西方話語的束縛
今天的世界秩序正在經歷一種變革,從一種縱向的世界秩序逐步轉向一種橫向的世界秩序。縱向秩序的特點是西方把他們的理念和實踐凌駕于其他國家之上,而橫向秩序的特點是各國在理念和實踐方面既有平等合作,又有良性的競爭。這將是一種更為民主的世界秩序。
我們有必要繼續發揚歐洲啟蒙時代那些知識巨人的精神,特別是那種開放包容的精神和尋求新知的勇氣。我們有必要以這樣的精神和勇氣去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治國之道,無論這一切對于西方許多人看上去是多么異樣。
如果這樣去行事,我們就可以避免由于意識形態驅使而誤判中國,我們也能因此而豐富我們集體的智慧,從而更好地共同應對人類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如消除貧困、反恐、氣候變化、防止文明沖突等。
事實上,對于國際上很多對中國不公正的指摘,我們除了需要有理論上、事實上的陳述之外,還要有一種比較簡易的、別人能聽懂的表述方式。實際上中國崛起是一個很精彩的故事,但我們還沒有講好。這方面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們現在要做的重要的事,就是要形成自己的話語體系。比如我們在非洲做了這么多的好事情,但西方卻一下子把我們污蔑得一塌糊涂,說我們在跟違反人權的政權打交道。我們現在官方的回應是,中國“不干涉內政”。這也是一種話語,但效果比較弱。無論在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中,有道德優勢的話語才是強勢話語。所以我們可以說,根據中國人的理念,消除貧困就是促進人權,而且是第一位的人權,因此中國幫助非洲消除貧困,就是促進非洲的人權,任何國家不能以任何借口阻礙別的國家幫助非洲消除貧困。這樣的話語就強勢得多。
我們的學者要通過自己原創的研究,擺脫西方話語的束縛。西方的話語體系其實有很多問題,比如為什么政治權利一定要比其他權利重要,如果你去多數國家的民眾中做個民調,一定不是這個結果。在這方面我們的學者要進行獨立的開發和研究,一旦突破就會海闊天空。而所有這些都還是戰術層面的,在戰略層面,最重要的仍然是一個國家的實質性崛起。歸根到底,西方是承認實力的。我們的最終目的,是把解釋中國的任務交給西方。中國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們都會來研究,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的教授都會來研究中國的成功故事,而這個趨勢現在已經開始了。
(作者為瑞士日內瓦外交與國家關系學院教授)
責編/馬靜 肖楠美編/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