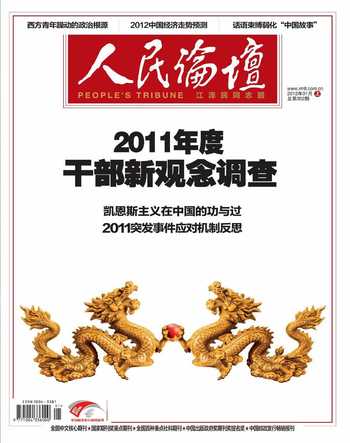凱恩斯主義在中國的功與過
許光建
我們國家在公共投資上的空間很大,但這并不否認在一些地方或領域已經出現了所謂的公共設施過于超前或者“貴族化”傾向,超出了國力的承受能力,帶來了新的不公平問題
初顯功效:戰勝亞洲金融危機
凱恩斯主義在中國的命運可以說是非常曲折的。遠的就不提了,從改革開放之后來看,也經歷了一個逐步引入和被社會接受認可的階段。在上世紀80年代,人們對凱恩斯主義的態度,基本上是作為一種重要理論來介紹和評論的,還不認為這種理論與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有多少關系。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我們實行的是計劃經濟為主的體制,發展市場經濟還沒有成為共識。在那種背景下,凱恩斯主義對我國經濟生活和經濟政策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從上世紀90年代初我們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之后,凱恩斯主義對宏觀經濟調控決策的影響開始逐步增加。但是,凱恩斯主義對宏觀經濟調控實際發生影響還是從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開始的。
1997年7月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不久,我國便出現了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的跡象。在非常復雜的國內國際經濟環境下,中央政府及時調整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方向:一方面,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及時采取了降低銀行存貸款利率等貨幣政策手段;另一方面,于1998年開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就是所謂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當年增發10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 之后幾年一直連續增發,大規模增加對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實踐證明,1998年之后一段時期實行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增長。
我國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轉型經濟特點,包括政府投資重點主要集中在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上,就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客觀要求,還有我們的決策機制比較靈活及時,可以提高財政政策的效果。但是,從理論上說,我國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宏觀經濟政策屬于凱恩斯主義的范疇,也可以視為凱恩斯主義在我國的第一次實驗。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我國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所取得的成效可能不完全甚至不主要是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功勞,有可能主要是加快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功勞。有專家還認為應主要歸功于那個時期實行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業迅速發展。但是,和1998年之前的十年相比,積極財政政策所發揮的作用確實是很大的,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妨將其視為凱恩斯主義在中國的首場實驗,并且成效顯著。
再上戰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
發源于美國次貸危機的此次國際金融危機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為劇烈的一次全球范圍的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要比十年之前的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大得多。為了應對這場危機,我國政府所采取的應對措施的規模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2008年底開始出臺實施總規模4萬億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采取了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十分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前一次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措施相比,這一次的力度更大,方式更多,效果更加顯著,對國際經濟的影響更大。同時,從理論上說,凱恩斯主義的印記更深。
我們知道,凱恩斯主義的主要政策主張是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且很強調采取擴大政府支出的政策來直接刺激需求。其機制就是在企業、家庭等微觀經濟主體由于對經濟前景信心不足或者悲觀而導致私人投資和消費或者“有效需求”出現顯著下降的條件下,通過政府投資規模的擴張來彌補私人投資和消費的不足,從而促進需求擴大、增加就業和促進經濟增長。但是,這就需要具備一個前提,即存在著政府投資的空間。如果政府的投資是替代企業投資,那么就會導致國進民退的現象,有效需求不可能增長。政府投資的領域應是企業不愿投資的公共基礎設施或公共服務,這樣才能起到創造有效需求的作用。
盡管1998年以來,我國在上一輪擴大內需、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投資建設了不少基礎設施,但是由于我國底子薄,不同地區之間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很大,基礎設施的缺口還是很大的,繼續擴大基礎設施投資是很必要的,不存在過剩的擔憂。在醫療、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上,我們面臨的缺口更大,亟需政府和社會的持續大規模投入。因此,在我國,通過擴大政府支出的方式來擴大有效需求是有必要的,是符合我們所處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
當然,也應指出,近幾年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所取得的成效也不能都歸功于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各個領域的改革深化和進一步拓展外需的政策作用也不容忽視。
是藥三分苦:認清凱恩斯主義的缺陷和適用性
自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對凱恩斯主義的懷疑和批評就一直是學術研究的一個重點。人們早已提出了實施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的經濟前提和可能發生的副作用。實際上,就在我國通過積極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回升的過程中,貨幣供給增長過多的問題已經逐步顯現出來,由此產生的通貨膨脹問題更是為社會關注。特別是在我國目前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政府職能轉變還遠不到位,某些地方政府還存在著嚴重的投資饑渴癥,自我約束的能力嚴重缺失等大背景下,政府投資規模過大,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力度過大,不可避免地會導致通貨膨脹、政府債務負擔加重、公共財政風險積累等問題的產生。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對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力度和時機如果把握控制不好,就很有可能產生一些問題。包括,擴大政府支出規模必然會導致財政赤字大大增加和通貨膨脹。在這里特別要關注公共債務問題,從目前的官方數據來看,公開的正規的財政赤字并不是個大問題,和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赤字規模并不是個問題。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們還有相當復雜的,很難界定厘清的地方債務規模問題。這是這一輪經濟刺激計劃和擴大內需所產生的新問題,頗具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不可掉以輕心。還有一個問題是公共投資的質量和效果問題。同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國家在公共投資上的空間很大,但這并不否認在一些地方或領域已經出現了所謂的公共設施過于超前或者“貴族化”傾向,超出了國力的承受能力,帶來了新的不公平問題。這種擴大投資不是擴大有效需求,而是創造過度需求,是應當避免的。
打組合拳:中國宏觀調控的法寶
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由于這兩種宏觀政策的運行機制不同,需要相互協調。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的協調有多種方式,從政策取向來看,一般有四種搭配方式:雙松、雙緊、一松一緊和均為穩健。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前期,尤其是2008年底到2009年底,我國采取的是雙松搭配,就是兩種政策都是擴張性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從去年年中開始,為了抑制通貨膨脹,貨幣政策開始轉向,從寬松轉向穩健,兩種政策呈現出一松一穩的搭配。由于國際經濟又出現了新的不確定性,二次探底的風險存在,財政政策退出需要慎重,很可能需要持續一個時期,因此這種搭配可能還會保持一段時間。在財政政策方面,也需要統籌考慮,綜合運用政府支出和減輕稅負等不同手段,在繼續保持一定規模的政府支出的同時,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適時適當地減輕企業和居民的稅收負擔,增加企業盈利能力,促進經濟增長。
我們還要注意到,我國還處在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有一些領域的改革的任務還很重,例如鐵路和其他壟斷性行業的改革還很不到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差距過大的問題還沒有緩解,政府的職能轉變還需要加快,等等。如果沒有經濟改革的積極推進,光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國民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是很難實現的。因此,要把宏觀調控和改革緊密地結合起來。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責編/馬靜美編/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