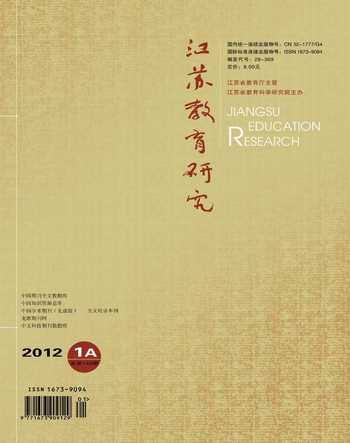課堂教學傾聽的常見誤區及歸因分析
陳彩萍 李如密
摘要:長期以來,課堂都是教師主導的舞臺,“言說”往往被看作教師的“權力”,而“傾聽”則是學生的“本分”。隨著教育觀念的更新,教師不但意識到學生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體,需要被傾聽,而且學生也是一種可貴的課程資源,值得被傾聽。盡管如此,教師在教學中具體運用“傾聽”這一方式時,由于諸多原因仍頻頻發生失誤現象。本文試從教學中教師傾聽運用的失誤現象入手,著重分析其背后的影響因素,希望對教師有效地運用傾聽藝術有所啟示。
關鍵詞:教師;課堂教學;傾聽;失聰;泛化;讀圖時代
中圖分類號:G421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9094(2012)01-0016-04
何謂傾聽?《現代漢語詞典》將“傾聽”解釋為:細心地聽取(多用于上對下)[1]。這里的“傾聽”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聽”。聽是用耳朵接受各種聽得見的聲音的一種行為,是只有聲音,沒有信息、被動的、無意識的行為,它主要取決于客觀;而傾聽是主動獲取信息的一種行為,有信息、需要專心關注,是一種積極的有意識的行為,它主要取決于主觀意識[2]。簡單地講,“聽”是耳朵功能的一部分,是健全的耳朵先天具有的一種能力,它不需人刻意去追求和習得;而“傾聽”卻恰恰相反,它是人們后天有意識養成的一種品德素養,它借助更多的不是人的器官而是主觀意識。打個比方說,一個聾啞人他可能喪失了“聽”的能力,但他不一定也喪失了“傾聽”的能力。只要他能走進言說者話語、文字、作品、藝術等的內心世界,并與它們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那么他就具有傾聽的能力。本文要探討的“傾聽”主要指對有聲話語的傾聽,具體指一種有意識的積極獲取信息的主觀行為。
在教學中,傾聽和言說是溝通師生之間情感的紐帶,傳統教學過于強調“師道尊嚴”,忽視了教學中教師傾聽的價值,從而導致了在課堂中學生生命的“缺席”。一旦教師轉向開始傾聽學生,不僅意味著教師對學生個體生命的尊重與接納,而且也意味著對學生學習的負責與關愛。同時,伽達默爾也說過:“沒有理解的純粹傾聽是不存在的。顯而易見,也不存在某種沒有傾聽的理解。”[3]因此,教師要想真正地和學生展開對話,必須彎下腰,走近學生,傾聽學生,否則其言說必然是低效的、甚至是無效的。
一、課堂教學中教師傾聽的常見誤區:“失聰”與“泛化”
在日常教學中,教師運用傾聽的誤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學生的言說有意無意地遺漏,發生失聰現象;另一方面是對學生的言說全盤接收,發生泛化現象,具體分析如下。
(一)“失聰”。
失聰現象主要表現在三方面。
一是病態的傾聽。教師在傾聽過程中有意識地選擇那些能滿足其自我需要的聲音,對那些可能對自我不利的聲音卻加以排斥和壓制[4]。教師的傾聽帶有很強的選擇性和目的性,他有意無意地誘導學生往自己預設的標準答案靠攏,接近標準答案的言說就傾聽,遠離標準答案的言說就選擇性失聰。有教師執教《解決問題的策略》(蘇教版,五年級下冊)的習題課時,書中有一個關于李白喝酒的思考題,原題是:“李白街上走,提壺去買酒。遇店加一倍,見花喝一斗。三遇店和花,喝光壺中酒。借問此壺中,原有多少酒?”學生拿到這類無具體數字的文字題一般都不知所措,于是教師重點指導學生怎樣審題,怎樣挖掘有效信息。在教師的悉心指導下,終于大部分學生可以運用逆推思想進行列式運算了,可正當教師自鳴得意時,忽然后排舉起了一個胖乎乎的小手。又是那個小手,好幾次因為它,教師都沒有完成教學任務。于是,教師很警惕地叫那個小手的主人回答問題。而他也開始慢聲慢語地解釋起來,他認為“三遇店和花”不應只是筆者解釋成的“遇店遇花——遇店遇花——遇店遇花”,還可以是“遇店遇店——遇花遇花——遇店遇花”或“遇店遇店——遇店遇花——遇花遇花”等情況。教師承認他的解釋不無道理,但教案并沒有提供這樣的方法,而且結果也完全跟教案提供的數值不同。于是,直接否定了他的回答,理由是“三遇店和花”不是隨機排列組合的,在這就是指三次遇到“店和花”。課后,聽課專家跟這位教師講,其實這位學生的回答很精彩,他講的要點正是教案忽略的地方,這道題的答案就應該是多元的。還有些教師喜歡拿自己跟別的教師對比,喜歡聽學生奉承和贊美的聲音,這使得學生的聲音充滿了欺騙和謊言,同時也助長了教師的虛榮心,不利于師生雙方面的健康發展[5]。可以說,這種行為不僅扭曲了師生的健康心理,而且也扭曲了人們對教育本真的看法。雅斯貝爾斯曾說過:“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識的認識和堆積。”[6]如果為人師表的教師自身尚且都貪慕虛榮、表里不一,那么又怎么能寄他以厚望來雕鑄純潔美好的兒童心靈呢。
二是虛假的傾聽。教師表面上擺出一副傾聽的姿態,貌似在聽,實則“左耳朵進,右耳朵出”,根本就沒有進入學生的話語世界。最糟糕的是有的教師連一只耳朵也不打開,呆呆地坐在那里,對學生的發言不置可否,不加點撥,未能讓孩子的聲音在自己的內心激起任何漣漪。這樣的人,與其說他在傾聽他人,不如說是在傾聽自我[7]。有一位年輕女教師執教的《統計》(蘇教版、五年級下冊)公開課,課中教師為了給學生具體的復式統計圖印象,特意列舉了接近學生生活的例子,如京滬的降水量統計圖、春夏的氣溫統計圖、股市漲跌走勢圖、男女生身高統計圖……正當教師要順利轉入下一個環節時,突然有位學生舉手說剛才老師列舉的股市漲跌走勢圖不屬于復式統計圖。年輕女教師一陣臉紅,然后示意讓學生解釋原因。學生解釋得很吃力,年輕女教師也聽得很不耐煩,她不時地看看手表,顯然這一環節已經超時了,于是還未等學生完全說完,年輕教師就迫不及待地插話道:“這個問題,我們課后慢慢探討,現在我們來看書本”,然后就硬生生地責令這位學生坐下來了。課后,指導老師跟年輕女教師講股市漲跌走勢圖確實不屬于復式統計圖,因為它不符合復式統計圖的概念范疇。股市漲跌走勢圖,它的連接線不是線段,而且自身具有不可預測性,而這些恰恰是鑒別復式統計圖最基本的兩個特點。如果剛剛這位女教師能利用好那位學生的回答,那將是一個多么好的素材,是多么有利于學生加深對概念的理解啊,錯就錯在教師早就關上了自己的耳朵,學生的心聲根本就進入不了教師的內心。
三是錯誤的傾聽。語言學家索緒爾(F.D.Saussure)認為語言不僅應從它的歷史,還應從它的現存結構來研究,語言是符號系統,它由能指和所指所組成。意義并非形成于語詞和事物(能指和所指)之間的一致性,而是形成于符號和能指之間的關系以及其他符號和能指之間的區別[8]。語言博大精深,一個詞或一個句子往往語境不同、語調不同,語意就會發生改變。教師如果不認真傾聽學生,遺漏了學生言說中的重要信息,那么教師往往只能聽出學生“所指”的表層含義,而不能聽出“能指”的深層意義。因此,教師不僅要認真傾聽學生,還要積極思考、有效判斷,透過語言準確把握學生聲音的內涵、方向和潛在意義,從而做出正確反應和評價。
(二)“泛化”。
在教學中,有些教師有真誠傾聽的愿望,然而卻不知道傾聽什么,怎么傾聽,缺乏相應的技能技巧,于是導致“一鍋端”,把學生的聲音全都納入自己的“聽力場”,結果不知道如何辨別和取舍有效的信息,導致傾聽的泛化現象。泛化現象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方面是教師聽學生獨白,不給予任何反饋。“傾聽”是置入式的,沒有絕對的主體,是雙方打開胸懷,互相接納、互相理解的過程。因此,“傾聽”是一種雙向的交流過程,它的作用不在于“聽”的本身,而是通過“聽”能進入對方的心靈世界,與對方展開真誠的對話。成尚榮教授曾說過,對話是從傾聽開始的,傾聽是對話的前奏,沒有傾聽就無法對話,也就無所謂教育,無所謂教學[9]。課堂短短40分鐘,時間很有限,如果教師接受學生的全部聲音,那試問還有多少時間教師能進行獨立思考和問題反饋?更何況,學生口語表達的聲音本身就很抽象,是稍縱即逝的。如果教師不善于抓住學生話語的關鍵詞、潛臺詞和弦外之音的話,就難以在瞬時之內準確地捕捉學生所言說的內容,就難以把握學生言說中細膩的情感,就難以判別學生觀點的正誤,從而很容易錯失引導學生認真思考的良好時機,也很容易造成學生言說完之后的課堂“冷場”。有一位實習老師試上《讀書節》專題課,上課伊始,用PPT出示了各種各樣的讀書成語,具體有:懸梁刺股、鑿壁借光、積雪囊螢、負薪掛角、韋編三絕等。實習老師要求學生根據出示的成語具體說說故事的來源。面對陌生的面孔,學生們顯得很不配合,面面相覷下居然沒有一個人主動舉手。在實習老師的再三鼓勵下,好不容易墻角舉起了一個小手,實習老師像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樣欣喜。誰知,被叫起的小男孩卻一臉不屑,他說這些故事他小時候就熟悉了,接著便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小男孩從懸梁刺股一直講到了韋編三絕,不可否認他講得相當精彩,但其間仍然有很多細節出現了問題,比如把具體時間給搞亂了,把人物名字給讀錯了,把成語的出處給少記了等。可惜的是,實習老師并不懂得傾聽藝術,他在聽完學生的所有語言后,只是示意性地用PPT再次呈現成語故事,并未就細節問題進行及時糾正,顯然他早已忘記了這些問題。課后,指導老師叫那個小男孩再次講述剛才的成語故事,發現之前犯的錯誤,現在還是照樣犯,并未有所改進。由此可見,教師掌握傾聽藝術對教學而言是多么的重要啊。
另一方面是教師錯將“跑題”理解為“生成”。新課改反對傳統教學的一味強調課前“預設”,主張要重視課堂中的“生成”。這使得有些教師為了跟風,盲目追求“生成”,把“生成”的外延擴大化,甚至把 “跑題”也容納了進來,以致某些教師誤認為在課堂中,除自己“預設”以外,學生提的問題全都是“生成”,既然新課改重視“生成”,那么教師就要迫使自己傾聽學生所有的聲音。這一行為導致教師聽了很多,卻很少與教學內容有關,其中大部分都游離于教學目標之外,最終耽誤了教學任務的完成,也阻礙了學生的發展。其實,“生成”和“跑題”不是一個層次上的概念,“生成”是基于教學目標的,是對“預設”的動態調整和發展;而“跑題”是純粹脫離教學目標的,是學生對教學內容的誤解,是需要教師點撥和糾正的錯誤思維。如果教師自身對兩者的概念都存在異議,那么最終導致的“教學任務完不成、學生不良發展”的后果似乎也不足為奇了。因此,作為教師需要多學習教育理論知識,從基本的概念源頭就把不必要的失誤扼殺于搖籃之中。
二、教學中教師傾聽走入誤區的歸因分析
(一)“讀圖時代”重視視覺文化,弱化了教師的傾聽能力。
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和數字媒體的發展,我們迎來了以“視覺化”為主要特征的“讀圖時代”。眼睛隱喻下的“凝視”功能,越來越受到追捧,“耳朵”隱喻下的“傾聽”功能,卻越來越遭受漠視[10]。圖像是直觀的,它是視覺化的載體,代表了當代消費社會的享樂主義意識形態,表現為追求感官的刺激與快感[11]。而聲音是抽象的,它需要言說者和傾聽者彼此潛入對方的心靈世界,領悟對方的內心需要,進行思維的碰撞和情感的交融,從而生成意義。“讀圖時代”的到來使得人們的思維方式從“符號思維”走向了“圖像思維”,一定程度上帶來了人們感覺的鈍化,[12]同時也嚴重扼殺了人們的想象力。在教學中,形形色色的PPT、 FLASH、視頻……充斥課堂,這使得教師上課機械化,學生也出現了嚴重的審美疲勞。教師一味地依賴圖像,也使得自己天生的聽覺能力趨于衰弱。實際上,柏拉圖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他曾說過,當我們發明出一種技術以擴大我們的知覺能力時,我們天生的能力反而會因此萎縮和改變。這些帶有極端性的觀點提醒我們,對技術的過分依賴和沉迷會損害聽的能力,會迷失聽本身[13]。就拿音樂來說吧,如果不把音樂做成MTV、電影、視頻等,僅以音樂本身的形式呈現給世人,那么我們就不會依賴于圖像給的直觀印象,而會用心去傾聽音樂背后所要傳達的本質的東西,從而與音樂融為一體,達到情感的升華。然而,圖像的出現,使得一切感官都變得形象化了,一切感受也趨于同一化了,解讀音樂的豐富性消失了,人們的想象力也逐漸被扼殺了。
(二)傳統教學觀念,阻礙了教師傾聽學生。
在傳統教學中,教師往往被看作是“道”的代表、“禮”的化身,是知識的擁有者、真理的掌握者。將自我邏輯和權力融為一體的教師,覺得自己的知識經驗、社會閱歷遠比學生豐富,表現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不愿屈尊去傾聽學生,因為任何對學生卑微式的傾聽,都有可能是對其權力意志的威脅和挑戰。而學生在教師這種權威的壓制下,也逐漸喪失了自我,喪失了話語權,成了“理想的聽話人”。教師無視學生的心理需求和內心體驗,一味地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學生,用嚴厲的方法平息學生的疑問,結果導致學生失去了表達的興趣和勇氣,最終不愿意、也不習慣表達自己的想法了。其實,這樣的現象在生活中還是屢見不鮮的。就拿我們最熟悉的課堂提問現象來說吧。走進小學課堂,你會發現學生高舉的小手如林,一個個都熱情高漲地要回答問題;到了中學的課堂,你會發現課上豎起的手稀稀散散,大部分學生都紅著臉蛋、低著頭,揣摩著教師的答案;而到了高中課堂,你會發現樹林消失了,學生幾乎清一色地耷拉著腦袋,看著教師,直接等待著其宣布正確答案。為什么隨著年級的增高,舉手的人會越來越少呢?那是因為學生原初的好奇心和回答問題的勇氣,隨著時間的推移,全都被教師的權威給消解了。縱觀這樣的課堂,實在令人悲哀,我們的教學主張以學生為本,而教師一味地在課堂上唱獨角戲,又會把學生置于何處?
(三)教學實踐中以“教”為中心,影響了教師傾聽學生。
傳統教學強調以教師的“教”為中心,而“教”的代名詞是“講和說”,因而課堂要由教師主宰,教師要盡講的責任,而學生要盡聽的義務,這使得課堂聽說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課堂中充滿了教師的話語霸權,教師的“說”風盛行,而“傾聽”缺失。而學生作為教學被動的一方,不是作為一個“生命”的存在,而是作為一個“教師心目中理想的學生形象”而存在。這樣,教師聽到的永遠只是自我的聲音,而關注的也永遠只是如何灌輸知識,完成自己的教學任務。教學是一個雙向的交往過程,是教師和學生共同生成意義的創造過程。沒有學生的聲音,課堂變得呆板而死寂,也失去了應有的教育意義。學生作為一個鮮活的生命體,他有自己的困惑和感受,這需要教師用心傾聽;同時“后喻時代”的到來,使得學生成為了一種可貴的教學資源,他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想法,這值得教師認真傾聽。當然,不可否認,隨著新課改的推行,一些學校意識到了傾聽的重要性,并且在大力實施中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大部分學校的實施效果并不能如愿以償。歸根結底,雖然最初愿望是美好的,但在實施的時候卻往往變味了,傾聽成了校方衡量教師、教師評價學生的指標。這樣的“傾聽”未免讓人心寒,要知道傾聽是為“理解”而生的,而不是為“評價”而活的。
總之,教師“言說”權的維護不能以“傾聽”權的喪失為代價,我們應該重新審視教學中教師“傾聽”的教育價值,還課堂應有的“傾聽”空間,還學生一個本真的存在世界,因為“傾聽”乃教學改革不能忽略的關鍵詞之一。
參考文獻:
[1]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2]康青.管理溝通[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3]【德】伽達默爾.論傾聽[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1).
[4][5][7][13]李政濤.傾聽著的教育——論教師對學生的傾聽[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1(7).
[6]【德】雅斯貝爾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91.
[8]【美】帕特里克·斯萊特里著,徐文彬,孫玲譯.后現代時期的課程發展[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9]成尚榮.傾聽,教育的另一種言說[J].人民教育,2004(24).
[10]王海英.“凝視”與“傾聽”——感官社會學視野下的師生觀[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5(11).
[11][12]葉黎明,陶本一.“讀圖時代”語文閱讀教學的危機與走向[J].教育學報,2007(3).
Common Misunderstanding of Classroom Listening and Analysis of Attribution
CHEN Cai-ping & LI Ru-m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urse and Teach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264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philosophy, teachers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students are independent individuals needed to be listened to and worth listening to. Nevertheless, much misunderstanding is brought about for various reasons. This essay starts with teacher's improper application of listening i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then analyzes the factors behind the phenomenon in hopes of providing revelations for teachers.
Key words: classroom teaching; listening; loss of hearing; gener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