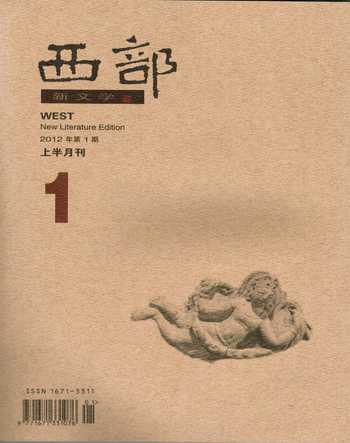杜鵑侵巢的儀式
2012-04-29 08:21:51陳東東
西部
2012年1期
關鍵詞:語言
陳東東
當弗洛斯特說,詩就是經過翻譯而喪失的那部分……的時候,他大概沒有想到,他在也許拒絕詩被翻譯的同時,卻已經代表詩人——在將一件詩作從一種語言變換成另一種語言的交易中作為出產商的詩人——賦予了翻譯家改裝其產品的權力。既然另一種語言的讀者不可能去感受原作者提供的那被稱作為詩的東西,讓他們去感受原作者提供的詩,就成了翻譯家擔當的任務。然而,詩又是不能被翻譯的,那么翻譯家在翻譯一首詩的時候,要做的事情就不僅是翻譯了。翻譯家還得依據原作者提供的詩,用另一種語言去寫出新詩。被翻譯家寫出的那首新詩,大概只約等于原作者的那首詩,大概只相當于一棵白楊樹的水中倒影,它對于那個原作者也許有意義,其實已沒什么意義,就像岸上的白楊樹無法在乎水波對其形象的歪曲。
翻譯詩的意義,在于能夠從中感受其詩的另一種語言的讀者,在于用另一種語言創造出翻譯詩的翻譯家,在于用以翻譯的那另一種語言的文學及其傳統。站在另一種語言的文學及其傳統的立場上,也不妨說,那個總是憂心于他的詩未能被忠實翻譯的原作者,他的文學背景,特別是他用外語寫下的詩,是不重要的。在翻譯文學、特別是翻譯詩的活動中,真正重要的當然是那個翻譯家和被他翻譯過來的詩,是那個被翻譯家用另一種語言塑造的另一個詩人。套用維特根斯坦有關世界之神秘的那句名言,——對于一個翻譯詩的讀者,值得探究的不是這首詩(和它的作者)原先是怎樣的,而是它現在是這樣的。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華詩詞(2023年8期)2023-02-06 08:51:28
文苑(2020年4期)2020-05-30 12:35:30
小學生作文(中高年級適用)(2018年3期)2018-04-18 01:24:47
瘋狂英語·新策略(2017年8期)2017-05-31 08:13:46
新聞傳播(2016年10期)2016-09-26 12:15:04
玉溪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1期)2015-08-22 02:51:58
少兒科學周刊·少年版(2015年4期)2015-07-07 21:11:17
語文知識(2014年10期)2014-02-28 22:00:56
中學生英語高中綜合天地(2009年10期)2009-12-29 00:00:00
作文周刊·小學一年級版(2008年51期)2008-12-31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