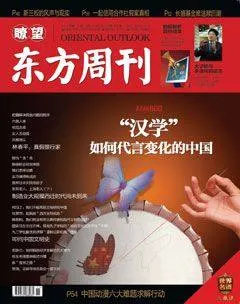美國漢學家安樂哲:孔子不是博物館
第一次聽說孔子是1966年,我才18歲,在香港。那時候中國內地的“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我本來是在香港中文大學學詩歌,室友給了我一本《四書》,我一下子就被迷住了。這也是我決定畢生研究中國哲學的開始。
當時,哲學界是黑格爾的時代,中國文化普遍被認為是疲倦、古老、保守、沒什么希望的。在西方哲學家看來,孔子是一個“可以使時間靜止”的人物,代表遙遠的古代,沒什么現實意義。
“你講的不是中國的孔子,是個華僑”
1985年,我第一次來到中國大陸,去上海復旦大學演講。那里曾是“批孔”的發源地。我那時只有30出頭,年輕氣盛。
教室里,老師坐在后排,年輕的學生坐在前面。我講了自己對孔子的理解,說孔子是世界級的思想家,對歷史的貢獻不亞于黑格爾。
講完后,一個學生站起來說:“安教授,你講的不是中國的孔子,是個華僑。”
我回答:“國際意義上的孔子并不是你知道的那個孔子。”
他又問:“你難道懂得比我們老師還多嗎?”
我回答:“中國有一句話叫‘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你們老師解釋的孔子是一種理解,但孔子作為一個國際性的思想家,中國以外的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
當時孔子在中國被完全邊緣化,中國人自己喪失了對本國文化的信心。當時有一部紀錄片叫《河殤》,表達的就是這樣一種情緒。中國文化被中國人認為是低一等的文化,外國文化被認為是先進的。當時在中國大學的哲學系里,研究中國哲學的地位都比較低,當領導的都是學西方哲學出身的。
一直到2001~2002年,我在北京大學訪學時,仍然感覺,即使是北大哲學系的學生對孔子也沒什么興趣,認為他過時了,他們感興趣的是“新”的東西。
孔子和儒學將變成一種世界級哲學
但后來,2006年和2008年,我再次到北大訪學的時候,發現學生們開始重新對孔子發生了興趣。
現在在中國國內,政府和學界都在推動一場“國學熱”。幾乎所有中國重點大學都投入重金推廣孔子的學說和文化,中國教育部也在過去10年間,在世界各個角落建立了300多所孔子學院,而且這個數字還在增長。我曾經跟語言學家出身的許嘉璐交流過對于國學的看法,他有很深的見解。
我覺得孔子學院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夏威夷大學是最早一批建立海外孔子學院的大學之一,而當時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學等名校都拒絕了孔子學院。這時有一個《紐約時報》的記者打電話問我,你會不會擔心孔子學院是中國政府利用你的學術聲譽來進行“宣傳”。
我回答說,我為什么要擔心?我曾在武漢大學做過富布賴特學者。富布賴特項目已有60年歷史,也是美國政府出的錢,日本也有日本海外基金會,韓國也有韓國項目,這不是很正常的事嗎?每個國家都希望在海外樹立自己的正面形象。為什么一到中國你們就格外敏感呢?
我相信,在未來的十至二十年里,這個世界上將會出現一種全新的文化秩序,其中孔子的地位將上升到一個前一代人完全不敢想象的高度。換言之,當今世界的文化大變革將把孔子和儒學變成一種世界級哲學,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有重要一席。
美國人把孔子和耶穌歸為一類
中國現在的國際政治經濟地位都已經達到了一定高度,但中國文化在西方人眼中仍然是個謎。西方人不理解中國文化。
夏威夷大學在比較哲學方面是很領先的,因此我的同事和學生們對孔子的理解比較深。但對于一般的美國人來說,他們只知道孔子是中國人,是一位古代的思想家。但他們對于孔子的身份認知是模糊的,有時把他和耶穌、釋迦牟尼放在一起,有時又與柏拉圖和蘇格拉底歸為一類。
有趣的是,在他們腦中,孔子被賦予了中國沒有的宗教聯系。在美國的書店和圖書館里,《論語》是被放在“東方宗教”一欄的。他們把孔子“基督化”,比如孔子講的“天”和“地”會被聯想為基督教里的天和地,“義”會被理解為“遵循上帝之道”。
忠于孔子,就一定要不斷“改寫”他
與其他文化中的大思想家相比,孔子的特殊之處在于,他的教誨都是集中于日常生活中的平常小事。他教你怎么做一個人,怎么培養自己的修養。他的思想不是拒人于外、與普通人無關的,他不是上帝,他教你的東西,就像是祖父與孫女的對話。
中國人重視教育也是來自于孔子。孔子的整套學說就可以總結為關于教育的哲學。
忠于孔子,就一定要不斷“改寫”他。孔子自己就是以繼承周公并發揚光大為己任的。孔子自己也說“述而不作”,真實地展現孔子,就一定要使之與現代生活和現代人有關。
孔子不是博物館,只能參觀,孔子應該存在于現實之中。
我聽說現在中國國內有很多關于解釋孔子的爭議,比如于丹講的孔子、李零寫的孔子。我覺得,有爭議是一件好事,每個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理解孔子。學術的理解和大眾的理解這兩種方式可以并行不悖。

希望孔子不要變成政治口號
我對現代重提孔子唯一的擔心是,它會變成一種政治口號。
不久前,我在德國漢堡參加了德國漢學研究100周年的研討會。會議邀請的都是像我、杜維明這樣對孔子持正面態度的學者。為什么呢?因為德國人都不喜歡孔子。這又是什么原因呢?這種態度其實來自于二戰。納粹統治的經歷使德國人對于任何國家統一思想的東西都感到格外不舒服。
因此,我希望孔子是以一種文化遺產,而不是以社會系統教化的方式被繼承。我希望孔子不要被政治化。
中國人一直說自己有一種“信仰真空”,因此才有了物質主義和拜金主義泛濫。能夠對孔子爭議是一件好事。中國人需要重新樹立對自己文化的信心。
(安樂哲(Roger Ames)是目前海外中西比較哲學界的領軍人物,現為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曾長期擔任夏威夷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代表作包括《孔子哲學思微》、《漢哲學思維的文化探源》、《先哲的民主:杜威、孔子和中國民主之希望》等。)
(來源:2010年1月25日《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