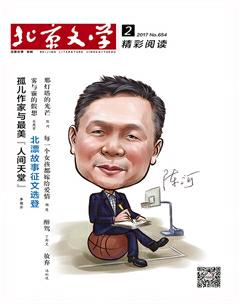短詩一束(組詩)
2017-02-13 00:39:15陳黨繼
北京文學 2017年2期
陳黨繼
延安小米
一粒小米有多重
抓一把黃土
指縫間漏下的血和火
喘息著
說給我聽
杭州雷峰塔
被長滿青苔的世事糾纏著
只得縮在這里念佛……
一陣一陣地
牙痛
牙
自從那天
揀到野狼丟失的門牙
裝在自己嘴里以后
這只山羊
便開始厭煩
青青的草了
夜半
偷偷把牙取出來
在石頭上磨
什么時候
抓個人
嘗嘗
紅葉
這一腔血
咯給誰啊
就是秋了……
手掌伸開
站一串
硬硬的
鳥聲……
無題
掐住了小鳥的咽喉
你就是勝者了?
……小鳥掙扎著
想
問這話的
是傻子
貝殼
你們硬要說我是大海的耳朵
只是為了讓自己覺得
這個世界還不是死寂的……
雖然我已經死過多少次了
責任編輯 杜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