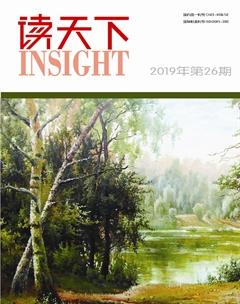淺析新時期如何做好幼兒師范學校班主任工作
摘要:班主任是一個班級的核心,一個班級的管理質量與班主任有著重要的關系。幼兒師范學校是培養幼師的學校,班主任的工作將為學生提供一個良好的典范。班主任的工作不僅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情況,還會影響到學生的心理成長。因此,班主任必須做好班級里的工作,讓學生接受到專業的學前教育。本文主要研究新時期如何做好幼兒師范學校班主任工作。
關鍵詞:幼兒師范;班主任;新時期
班主任在教育中是非常特殊的一個職位。班主任的工作質量不僅關系到學生的學習情況,而且還會影響到學生能否樹立正確的教師觀念。新時期下,各種信息的沖擊使班主任的工作也受到了挑戰。因此,班主任更要重視自己的工作,使學生能夠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班主任在工作的過程中,要增加與學生的溝通,及時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和心理狀態。班主任要合理規劃好班級里的工作,為學生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氛圍。最重要的是班主任要為學生做好榜樣的工作,讓學生為以后的幼師工作打下基礎。
一、 我的班級我做主
在班級里往往是一個班主任面對幾十個學生,班主任很難顧忌到班級里的每個學生。為了使班主任能夠隨時掌握每個學生的學習情況,班主任可以在班級里選舉班干部,來幫助共同管理班集體。學生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上課,與班主任接觸的時間也比較有限。班干部是與學生接觸最多的,當學生遇到問題時,往往最多的是向班干部尋求幫助。在一個班級里往往有多個班干部,來分別管理班級里不同的事物。班長是班干部里的負責人物,代替班主任向班級里傳達各種信息。班干部的人選也是具有一定的要求的,首先要自愿。班干部相比較于其他的學生來說,工作會相對多一些,辛苦一點。所以,必須是一些自愿為大家服務的學生。
為了使選舉的班干部使每個學生都能夠滿意,班主任可以采用民主選舉的方式。讓大家自由進行競選,然后再進行選票。為了保證選舉的公正性,所有的環節一定要公正、公開。使每個學生都能夠感覺到班級里的公平性。班主任要讓學生自己做決定,讓學生感覺到民主。同時,為了讓每個學生都有機會為班級里服務,班干部可以進行輪流當選。班主任要為當選的班干部規劃好工作,讓整個班級里的工作都能夠順利進行。
二、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無規矩不成方圓,班級里必須要有一定的規章制度才能提高班級里的教學質量。一個班級里要具有核心凝聚力,必須要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班主任首先要為班級里的學生制定一個規章制度,需要學生的遵守。規章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為了約束學生而是為了給學生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氛圍。最基本的規章制度包括學生的遲到早退、上課紀律、衛生值日等。班主任在制定一系列的規章制度后還要有一定的獎懲措施,否則規章制度就對學生沒有意義。同時,班主任也要為學生制定一個總的目標,讓所有的學生朝著共同的目標努力,將班級凝聚起來。班主任在學期開始,讓每個學生都要制定自己的小目標,主要包括學習和生活上的目標。為了了解每個學生制定的目標是否合理,班主任要與學生進行交流,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了解學生在學習上的優勢和劣勢,從而為學生制定的目標提出合理的建議。
班主任也要為學生的生活制定一定的制度。現在幼兒師范里的學生很多都是寄宿生,學生在生活中也要有一定的規律,才能保證自己有一個良好的學習狀態。班主任在制定相關的制度時,最好做到民主決策,可以充分爭取學生的意見,并且要把制度進行細化,分給每個班干部遵照執行,制度一旦制定下來,必須實行,否則一切都如紙上談兵沒有意義。最重要的是,合理的規章制度,需要實施民主監督,畢竟實施制度的是學生本身,學生只有接受了制度,相互監督,嚴格遵循,這個制度在學生心中才會形成一定的約束力。
三、 德才兼備兩手抓
在傳統的班主任管理工作中,教師可能更加看重的是學生的學習成績。學校里會根據學生的學習成績對學生進行排名,從而來決定班主任的管理工作。雖然,學生的學習成績對學生來說很重要,但是,學生的心理發展更加重要。幼兒師范學校里的學生正處于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關鍵階段。班主任在管理工作上既要重視學生的學習成績,也要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觀念。在學生的學習方面,班主任要做好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溝通橋梁。班主任在課下的時候要與學生進行交流溝通,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根據學生的學習狀況為學生提出一些學習上的建議;班主任也要及時與各科任課教師了解情況,關心班級里的學生的學習情況,并將學生的情況反饋給各科教師,讓各科教師能夠及時調整教學方式。在學生的心理方面,班主任要注重每個學生的心理情況,保證每個學生都能夠健康成長。新時期下,社會上的各種信息的沖擊以及來自各方的誘惑和壓力,使學生的心理很容易就會崩潰。班主任要安排好學生的心理教育課程,而且還要親自與每個學生進行交流。發現學生心理上有問題,班主任要及時對學生進行疏導,并且在日常的生活中也要格外關注這類學生。做好學生的學習與心理兩方面工作,才能使學生健康茁壯地成長。
四、 共建和諧的師生關系
良好的師生關系是班主任做好工作的基礎。班主任要與學生建立一個良好的關系,學生才會更加配合班主任的工作。新時期下,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幼兒師范的學生正處于叛逆的時期,也給班主任的工作帶來了一定的挑戰。處于叛逆期的學生,會從心理上來反對班主任的管教。所以,班主任一定要與學生建立良好的關系,與學生成為朋友關系。為了與學生之間建立關系,班主任要做好以下幾點工作。首先,班主任要放下自己的架子。傳統的班主任管理方式,總是以班主任的位置自居,對學生完全是命令式的語氣,這樣的相處模式,非常容易使學生對班主任產生不好的印象。所以,新時期,班主任要放下自己教師的架子,與學生站在平等的位置,尊重學生。學生只有感受到了來自班主任的尊重,才會對班主任的安排服從。其次,班主任要真心地關心學生的生活,不能僅僅是做表面上的工作,更要認真了解每個學生的家庭情況,當學生遇到困難時,要及時幫學生進行解決。班主任要將自己的學生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看待,從細節上關心學生。學生只有感受到了來自班主任的關心,才會把班
主任當做自己的朋友。班主任與學生之間良好的關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形成的,需要班主任一點點地付出。而且,班主任千萬不要帶著目的去關心學生,要出于自己的本意,不能為了與學生建立關系采取關心學生,而是要把關心學生當作自己的本職工作。
五、 立德樹人,以身作則
幼兒師范學校的主要教學任務就是為了培養將來的幼師人才。學生將來從事的職業與班主任的工作具有相同的工作性質。為了使學生對幼師教育工作產生熱愛,班主任要為學生做好榜樣。班主任現在的工作態度和教育方法,一定程度上間接或者直接地影響到學生將來的工作狀態。班主任要為學生做一個良好的榜樣,讓學生樹立正確的職業觀。學生從幼兒師范學校畢業后,為了更好地服務幼兒,她們需要擁有更多的耐心,若是現在班主任的工作方式影響到了學生,有可能會使學生放棄幼兒教師這個職業。環境對一個人的成長具有重要的作用,班主任要努力為學生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氛圍,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感受到教師的偉大,從而愛上自己幼師的職業。班主任要以身作則,以自己良好的形象影響著學生。班主任一定不要讓學生感受到自己的負面情緒,要為學生傳遞一個積極樂觀的心態。班主任的榜樣工作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首先就是班主任教師的形象。要為學生樹立一個良好的教師形象,為學生以后做好教師工作打下基礎。其次是教師的處理事情的方式,學生將來從事教師職位后,當面臨同樣的問題時,可能會采取同樣的解決方式。最重要的就是班主任的人格,班主任具有良好的人格對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具有重要的作用。立德樹人是教育的中心環節,教師要以身作則。總之,為了提高班主任的工作質量,班主任一定要做好榜樣,從自身方面去影響學生,為學生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礎。
六、 總結
幼兒師范學校的班主任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班主任不僅要關心學生的學習成績,而且還要注重學生心理健康的成長。為了提高班級的教育質量班主任要做好以下的工作,民主選舉班干部,并且為班級里制定好相關的規章制度。將學生的學習成績與學生的心理健康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與學生之間建立一個良好的師生關系,并為學生做好榜樣。總之,班主任要盡心盡力為學生服務,幼兒師范學校里的教育質量才能提高。
參考文獻:
[1]楊仁俊.新時期如何做好幼兒師范學校班主任工作[J].考試周刊,2014(45):182-183.
[2]毛湘穎.論幼兒師范學校開展班主任工作的有效性[J].課程教育研究,2014(14):202.
[3]肖紅.幼兒師范學校班主任工作認同的問題與對策[J].金色年華:教學參考,2012(1):137-138.
[4]班主任管理方式對學生參與班集體建設積極性的影響——以河北石家莊幼兒師范學校為例[D].保定:河北大學,2013.
[5]張成強.初探幼兒師范類專科院校班主任隊伍的管理——以濟南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為例[J].教師,2016(17):113-114.
作者簡介:
賀瀟,河南省鄭州市,河南省幼兒師范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