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jié)構(gòu)性減稅虛實
邢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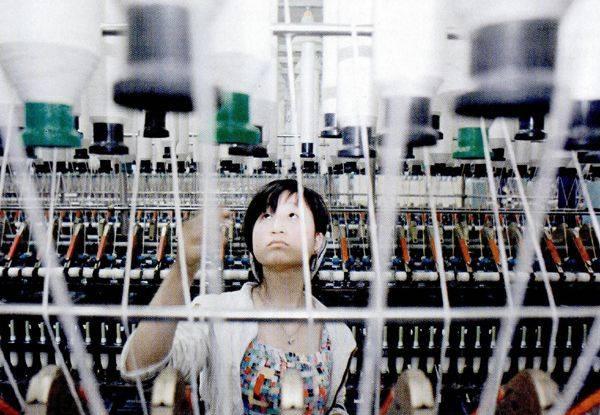
如何在概念上轉(zhuǎn)移民眾注意力是一種“管理的智慧”,在稅政中,亦如是。比如,減少直接稅的征收,加大間接稅的征收,可以使納稅人的“稅負痛感”處于“植物人狀態(tài)”。
在過去的4年中,為應(yīng)對經(jīng)濟環(huán)境變化以及民間強烈的減稅呼聲,“結(jié)構(gòu)性減稅”的稅改方案被推出,在概念上,它是以“減稅”為導(dǎo)向的,但與此相悖的是,4年來,政府稅收收入和財政收入?yún)s保持了高速的增長,民間對稅負減輕的感受不大。
如此一來,結(jié)構(gòu)性減稅的真實意義和這一稅改方案的真實含義備受質(zhì)疑。
口號與現(xiàn)實
2008年12月底首次提出了“結(jié)構(gòu)性減稅”的口號,這是在金融危機影響下中小企業(yè)生存壓力加大,為鼓勵投資、刺激消費、促進就業(yè)的背景下出臺的。
結(jié)構(gòu)性減稅指的對是部分稅種和部分納稅人群“有增有減”的結(jié)構(gòu)性調(diào)整,4年來,其具體措施大概如下:企業(yè)所得稅兩稅并軌、增值稅轉(zhuǎn)型、停征利息稅、降低股市交易印花稅、提高個人所得稅中工薪收入免征額及改進稅率設(shè)計、提高小微企業(yè)增值稅和營業(yè)稅起征點、營業(yè)稅改增值稅試點等。
根據(jù)財政部模糊的表態(tài),結(jié)構(gòu)性減稅政策實施之后,每年對企業(yè)和居民的實際減少稅負都在幾千億元。在各級稅務(wù)部門的工作報告中,普遍都能看到關(guān)于全面落實結(jié)構(gòu)性減稅,為企業(yè)減負多少多少的表述,不過,在這些報告中,最終這些稅務(wù)部門都完成了稅收增長的目標和任務(wù)。
實際上,結(jié)構(gòu)性減稅最終在減輕企業(yè)稅負上的真實性是令人懷疑的,但因它是“結(jié)構(gòu)性”的,因此很難去做籠統(tǒng)的統(tǒng)計。而來自企業(yè)界的直觀感受,或許更能說明問題。
“這幾年感覺沒有什么變化。”廣州一家小型廣告公司的總經(jīng)理對《南風(fēng)窗》記者說。在他的公司,如果按照正常繳納的稅種和稅率,一年稅費的支付要占公司利潤的一半。雖然他們通過定期給稅務(wù)部門的人員私下打點進行“避稅”,但增值稅、所得稅和城建費、堤圍費、教育附加費等各種費用加起來,稅費支出也占公司利潤的20%多。“要按照正常交,就該關(guān)門大吉了。”
在記者接觸的多家企業(yè)中,“沒有感覺”是一個幾乎相同的答復(fù),“現(xiàn)在鋪租一個月都幾千塊錢了,起征點調(diào)到2萬塊對我們來說沒什么意義,一個月營業(yè)額兩萬,就只能等著喝西北風(fēng)了。”廣州一位個體戶說。2011年11月,國稅總局將個體戶營業(yè)稅起征點從月銷售額1000~5000元調(diào)高到了5000~2萬元。
增值稅轉(zhuǎn)型對不同企業(yè)的影響并不一樣,“其實,小微企業(yè)的實際稅負往往比大企業(yè)還高。比如,我們買原材料經(jīng)常是根據(jù)訂單情況進行零星采購,向大企業(yè)采購的話,人家要批量大才賣,而且要現(xiàn)金,我們只能向小企業(yè)甚至是個體戶采購,而他們一般沒有增值稅進項發(fā)票,無法用來抵扣成本,無形中增值稅就會多交10幾個點。”中山一家服裝廠的老板說。
營業(yè)稅改增值稅是結(jié)構(gòu)性減稅的一個重頭戲。今年1月,上海開始試點營業(yè)稅改增值稅,以避免重復(fù)性征稅問題。根據(jù)上海市財政系統(tǒng)的統(tǒng)計,1~5月份,納入營改增試點范圍的13.5萬戶企業(yè)中,稅負下降的企業(yè)為12萬戶,占比近90%。從交通運輸業(yè)稅負來看,下降的企業(yè)占比為79%。前5個月,營改增帶來整體稅負下降超過80億元。
不過,物流運輸企業(yè)反映稅負“不降反增”的聲音不少,據(jù)2011年3月中國物流與采購聯(lián)合會對上海65家大型物流企業(yè)的調(diào)查,2008~2010年3年年均營業(yè)稅實際負擔(dān)率為1.3%,其中貨物運輸業(yè)務(wù)負擔(dān)率平均為1.88%。實行增值稅后,即使貨物運輸企業(yè)發(fā)生的可抵扣購進項目中全部可以取得增值稅專用發(fā)票進行進項稅額抵扣,實際增值稅負擔(dān)率也會增加到4.2%,上升幅度為123%。
對于很多企業(yè)來說,稅負下降沒感覺,但在稅收征管上的壓力卻是很明顯,“以前隱藏部分銷售收入,做大成本,增值稅這一塊還是可以少交一些,現(xiàn)在越來越難了,增值稅發(fā)票不那么好開,查賬也比較嚴。”某大型家電企業(yè)廣州營銷分公司的財務(wù)經(jīng)理說。
在有些地方,為抵沖“結(jié)構(gòu)性減稅”帶來的影響,甚至變樣執(zhí)行。據(jù)江蘇新聞廣播報道,部分在鹽城東臺市做家具生意的商戶反映,營業(yè)稅起征點提高后,稅務(wù)部門在估算他們月營業(yè)額時,都提高到了2萬元,原來每月只需繳納180元的國稅,現(xiàn)在提高到了600元。
不降反增的緣由
來自企業(yè)層面的感受在宏觀層面上是得到驗證的,結(jié)構(gòu)性減稅幾年來,財稅收入年年高增長,根據(jù)財政部公布的數(shù)據(jù),2008年全國稅收增速18.8%、2009年為9.8%、2010年為23%、2011年為22.6%,基本以高于GDP增長2到3倍的速度增長。
“評價結(jié)構(gòu)性減稅政策4年來的效果,是結(jié)構(gòu)性調(diào)整有,但減稅沒有,名不副實。”上海財經(jīng)大學(xué)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蔣洪對記者說。
在沒有增加新稅種,沒有提高稅率的前提下,宏觀稅負為什么會出現(xiàn)如此高速的增長?
在微觀層面上,企業(yè)效益增長、企業(yè)所得稅二稅合并、對外資優(yōu)惠減少、進口關(guān)稅增長都可以帶來稅收增長,同時,有些稅種稅率雖然不變,但稅收量增加了,比如資源稅,隨著資源產(chǎn)品價格的不斷升高,將征稅方式從“從量征收”變?yōu)椤皬膬r增收”,提高了資源稅的收入。
稅收倫理學(xué)者姚軒鴿認為,更深層次的原因還在于:一是政府財政支出的固化,每年財政增長的任務(wù)是固定的,地方財政有壓力,稅收增速很難降下來;二是現(xiàn)行稅制對宏觀稅負增長留有空間,90年代初稅制改革制定稅率的時候,已對法定征收與實際征收的差距進行了估算,而隨著征管技術(shù)水平的提升,“依法征收,應(yīng)收盡收”,實征的數(shù)量在不斷提高。
與此同時,在現(xiàn)有的征管組織機制下,在稅務(wù)機關(guān)的績效考核體系中,征收任務(wù)的完成是衡量稅務(wù)機關(guān)工作總體水平的最主要指標,地方政府的考核與獎勵機制也與此相關(guān),因此稅收任務(wù)的完成往往是“一俊遮百丑”。在這種情況下,很可能出現(xiàn)“預(yù)征先征”的“過頭稅”現(xiàn)象。
而政府財政收入年年以數(shù)倍于GDP增長的速度上升,除了稅收增長之外,還在于除稅之外的各種政府性基金及費用等非稅收入的征收,“現(xiàn)在有些地方稅和費的比例已經(jīng)接近1∶1了,地方政府對費的依賴性更大。”姚軒鴿對記者說。
來自財政部一季度數(shù)據(jù)顯示,全國財政收入29976.25億元,同比增長14.7%,中央非稅收入4118億元,同比增加1432億元,增長53.3%。地方非稅收入3472億元,同比增加1158億元,增幅50.1%。在天津,非稅收入占地方一般預(yù)算收入增加額的比例甚至達到72.2%。
去年以來,全國各地陸續(xù)開征地方教育費附加,以提高財政性教育經(jīng)費占GDP比例名義在全國推行的地方教育費附加,僅這一項就可以為地方財政增加1000億元左右的財政收入。
“費改稅”的工作也一直推進艱難。比如,本來是要用燃油稅取代公路收費,但目前燃油稅收了,公路費卻照收不誤,車船稅也是如此,結(jié)構(gòu)性減稅在實踐中變成了多升少降或者干脆是只升不降,使得稅負加重。
在現(xiàn)實中,結(jié)構(gòu)性減稅變異為結(jié)構(gòu)性增稅,違背了它的初衷。
稅改方向
今年以來,經(jīng)濟下滑,中央政府一再強調(diào)結(jié)構(gòu)性減稅,而企業(yè)和經(jīng)濟學(xué)家則一再呼吁全面、大幅減稅,以減稅拉動低迷的投資和消費。
“稅收的增加與減少應(yīng)相匹配,以減稅換增稅,總量和比例不能再提高,即稅收總負擔(dān)不應(yīng)該繼續(xù)上升,財政收支增幅高于GDP增幅的趨勢也不應(yīng)再持續(xù)。”蔣洪說。
只是,“從眼下的情況來看,宏觀稅負的降低前景不好判斷,結(jié)構(gòu)性減稅名不副實,而醞釀中要出臺的稅還很多。”蔣洪說。比如房產(chǎn)稅、環(huán)保稅等。
在地方層面,“今年是10年來稅務(wù)部門首次感覺到了稅收增長的巨大壓力。”姚軒鴿說。今年1~5月,全國財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長12.7%,增幅同比回落19.3個百分點,其中稅收收入增長9.4%,增幅同比回落21.4個百分點。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減稅的前景更加難以樂觀。
如何才能夠做到真正的減稅呢?
“只要稅收的主導(dǎo)權(quán)掌握在政府手中,減稅就很難推進下去。”姚軒鴿認為,“選擇性減稅,哪些增,哪些減,都是政府說了算,與納稅人關(guān)系不大,它最終會按照有利于政府和官員利益的邏輯走下去,有增無減,與民爭利。”
從結(jié)構(gòu)性減稅方案出臺的意圖來看,并沒有把稅收增長速度、整體稅負降下來作為出發(fā)點,僅把目光放在稅種和特定的納稅人群,這種“朝三暮四”的稅改政策只是采取打太極拳的方式來應(yīng)對民間的減稅呼聲,“是另一種維穩(wěn)方式”。
“政府可以說減收了多少稅,這個解釋權(quán)在他們,怎么解釋都通。”它最終導(dǎo)致征稅與納稅人權(quán)利和義務(wù)的不匹配,而“會哭的孩子”有奶吃,“沉默的大多數(shù)”則成為受害者。
“增稅、減稅不是稅改的根本性方向,只有將征稅的權(quán)力回歸納稅人主導(dǎo),所謂的增稅減稅才有意義,怎么增,怎么減,那都只是技術(shù)問題。”姚說。
1985年,第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決定,授權(quán)國務(wù)院可以制定稅收暫行條例。這一授權(quán)對稅收法律法規(guī)和政策的制定至關(guān)重要,意味著人大將稅收“閥門”轉(zhuǎn)交給了中央政府。政府若要增加稅收,可不經(jīng)人大審議批準,自行決定擴張財力。
“要實現(xiàn)總體減稅,首先稅收立法權(quán)必須回歸全國人大,稅收‘閥門必須控制在社會公眾和人大立法機構(gòu)手上。”蔣洪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