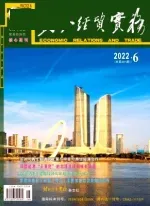我國中醫藥國際化之困境及破局思路
■ 魏格坤 桂林理工大學
一、走國際化道路是中國中醫藥貿易發展的必然選擇
近年來,隨著經濟生活國際化、低碳化的深化發展以及各國消費者保健意識的加強,國際市場中不斷涌現出純天然制品、綠色食品、生態產品等貿易商品,這使得國際植物藥市場和健康營養市場也呈現出蓬勃的發展勢頭,其貿易量平均每年以30%的速度在增長。依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當前全球約有40億人曾經或正通過中醫藥治療的方式預防和治療疾病,約占世界總人數的八成以上,中醫藥在世界中享有極高的影響力。據此推測,在未來的10年內,中醫藥在國際市場中必將具有極大的開發價值和市場潛力,這將預示著中醫藥這塊尚待劃分的市場蛋糕即將進入各國參與世界競爭的視野。我國中醫藥貿易近幾年也持續較快增長,尤其2010年以來,國際醫藥市場需求穩定,我國2010年中醫藥進出口總額高達601.9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4.57%。其中,出口397.33億美元,增長24.87%;進口204.64億美元,增長23.98%,中國中醫藥貿易已經呈現出巨大的潛在競爭能力。
目前我國的中醫藥出口主要面向華裔居多的亞洲市場、日本和韓國市場、歐美市場、非洲和阿拉伯市場,其中,亞洲市場約占我國中藥出口總值的2/3,產品銷售以東南亞國家以及港、澳、臺地區為主,中醫藥銷售總量在全球草藥市場中高居1/3的占比。隨著2010年1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啟動,在我國與東盟各國間涉及中藥類商品的關稅大幅降低,推動了中藥貿易快速增長。2010年中國對東盟中藥進出口額同比增加了28.05%,為4.22億美元,高于我國中藥進出口年平均增幅6個百分點。基于有著相似的中醫藥文化底蘊,日本和韓國既是我國中醫藥出口的主要競爭對手,但同時也成為了我國中醫藥出口的主要目標市場,我國中醫藥對其出口呈現穩步上升的趨勢,通過“兼蓄并用,自成體系”的出口策略,我國對兩國中醫藥出口總量約占全球中醫藥市場21%的比重。另外,西方市場主要包括西歐和北美各國及澳大利亞的草藥市場,在西歐國家中使用中醫藥的人口比率以德國為最高,超過58%德國人使用過中醫藥。其次,法國是歐共體第二大草藥市場,而且早在1952年法國醫學科學院就已經對針灸療法作了充分的肯定,承認它醫療行為的地位,而且,在1999年法國已經將中草藥列入國家醫療保險,當前,在法國國內,均有來自印度、中國、非洲、德國和法國本國的草藥被銷售。雖然非洲和阿拉伯國家的衛生條件較差、人們衛生意識還有待提高,但由于這些國家醫療事業發展起點低、來自發達國家同類競爭品少,是正在崛起的中草藥國際市場。我國自1960年以來,常年持續對非洲和阿拉伯國家輸出援助醫療隊,包括:索馬里、坦桑尼亞、贊比亞、莫桑比克、扎伊爾等國,通過這些醫療隊的宣傳及援助,當地不少人已經對中醫和中醫藥、針灸有一定的了解,這為我國中醫藥產品進入當地市場、取得未來中醫藥貿易的長足發展提供有利條件。
我國中醫藥出口產品主要由中藥材及飲片、提取物、中成藥、保健品四大類別構成,從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公布的數據看,其中前兩大類在我國中醫藥出口產品中占較大的比重,而中成藥和保健品出口的量比較少。依據我國商務局2010年數據顯示,提取物出口額為8.15億美元,占中藥商品出口總額的41.92%,依然是中藥商品出口的主力;提取物進口額為1.3億美元,占中藥商品進口總額的18.95%。中藥材飲片出口額為7.76億美元,占中藥類產品出口總額的39.89%。中成藥出口額為1.93億美元,進口額為2.18億美元,同比增長23.71%。
根據上述數據及其圖示可以看出,中藥材及飲片、提取物兩項產品在我國中藥出口中占高達90%的比例,但生產這兩項產品所需的工藝較為簡單、產品的附加值也不高。相反,具有較高附加值的中成藥出口在我國中藥出口中的比重僅占約10%,這樣一種產品的結構導致我國出口的中醫藥產品大多為低附加值的原材料及提取物,而附加值較高的保健品和中成藥則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更是比前兩項差很多。

二、我國中醫藥國際化困境分析
(一)我國的中醫藥出口產品的結構不合理
我國的中藥出口的基本情況是:以傳統市場為主;植物提取物的增長明顯;初級和原料產品出口占主體;中成藥的出口增長緩慢;價格呈上升趨勢。這樣一種產品的單線出口結構導致我國出口的中醫藥產品大多為低附加值的原材料及提取物,而附加值較高的保健品和中成藥出口偏低,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更是比前兩項差很多。當前,國際中藥市場的競爭在加劇,而我國許多中藥產品出口廠家存在嚴重的同類產品出口競爭的情況,甚至有些出口廠家迫于生產能力低下的限制,連中藥的加工業務都由其他廠商做。企業由于缺乏“獨有”的高附加值產品,導致出現出口企業利潤偏低、產品競爭力差的結果。要改變這種現況不改變,中國中醫藥出口難以取得長足的發展。另外,知識產權的維護問題在我國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過程中凸顯尖銳,在國內,相當一部分的珍貴中藥材被來自日本、韓國的客商低價收購買走,然后通過研發和加工,大量產出高附加值的“洋中藥”,以走捷徑的方式迅速搶占國際市場從而獲取高額利潤。例如,在世界享譽盛名的日本今村制藥企業所用的川貝母、長白山人參等都是我國最好的藥材。日本近年世界中藥銷售總量每年不低于300億美元,而日本的漢方藥就占了七成以上的比重,韓國的韓藥出口占一成左右,而我國的中藥出口僅占5%的低比例,而且其中70%的中藥出口主要是以價格低廉的中藥材為主。更令人堪憂的是,我國價格低廉的藥材出口一定程度上是以犧牲我國的生態和環境作為代價的。
(二)東西方文化差異是中成藥出口的最大障礙
由于中醫重宏觀,治療上講究辨證論治,而西醫重微觀、側重于單純病種和局部定位治療,中西醫理論的差異是中藥走向國際市場的最大障礙之一。西方國家評審藥物的法規是針對合成藥制成的,僅適用于單一成分的藥物。而中成藥以復方藥為主,藥物多達十幾味,很難解釋是哪一種成分起了作用,缺乏標準化。我國有關中醫中藥的理論博大精深,但從另一個角度上去理解也可以看出這些理論大多數都極為籠統和抽象,其中很多藥物的功效是無法用一些基本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來解釋清楚的。例如,美國對藥物明確規定其化學成分必須明確,即使是復方制劑也要求廠商明確其每種化學成分的藥效、作用,甚至包括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對藥效及毒性的影響,這樣的條件下,國內的中成藥很難通過美國FDA的認證。另外,中藥包括中成藥、湯藥、飲片和藥材,在使用上講究講究性味歸經、君臣佐使等,依據中藥學中“君臣佐使”、“相生相克”、“辨證淪治”的理論,中藥的使用必須在專業中醫師的指導下服用,否者容易產生過量用藥、藥物錯誤服用導致休克、中毒等嚴重后果,在缺乏對中藥的基本知識和了解的國家和地區,中藥的出口就難以得到推廣和使用了。
(三)中藥知識產權流失
縱觀現今的世界中藥市場,日韓占全球中藥市場90%營業額,而中國僅占2%。在全球中藥市場營業額中,日本占到百分之八十,韓國占到百分之十,而中國僅占百分之二。更令人擔心的是,由于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若干新規則,極有可能在不久后還會出現吃自己祖宗留下的中藥方子,卻要向外國人支付專利使用費的情況。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洋中藥”出現的在國際市場,紛紛在各國搶占申請專利,單看在我國境內獲批的中藥專利就高達1萬多項,占中國同類專利的八成以上。尤其近兩年來,日本的一些中藥廠商正式向世界衛生組織申請把以中醫藥為基礎的“皇漢醫學”、“漢方醫學”改稱為“東洋醫學”,設法通過改頭換面的方法把東道國的醫藥文化粉飾成為了自己的文化,在暴露出他們的經濟野心的同時也顯現出我國中醫藥出口的危機。以日本生產的“救心丸”為例,此產品本就是在我國傳統中藥六神丸”的基礎上進行研發出來的;另外,韓國的“牛黃清心液”本也源自我國的“牛黃清心丸”,而且其年產值近1億美元,已經在國際上的知名度遠超我國的“牛黃清心丸”。日韓兩國生產中藥的原材料和輔料絕大部分均由我國提供,但我國高附加值的中藥成品市場占有率卻遠低于日韓,在國際市場上,我國中藥正面臨著淪陷為“日藥”、“韓藥”的危機。而且,對于正處于朝陽產業階段的保健品生產來說,國外許多生產廠商從我國進口原材料,經過加工后成品的價格卻是我國原材料出口的價格好幾十倍,這種“為他人做嫁衣”的局面不改變,對中國中醫藥產品參與國際競爭的前景難以持樂觀態度。
(四)貿易壁壘嚴重阻礙我國中醫藥出口
近幾年來貿易壁壘的問題廣受關注,在中醫藥出口方面就更加的突出了。中醫藥想要堂堂正正進入其市場的難度非常大。自2011年4月,歐盟的《傳統藥品法案》中已經規定對中藥在歐盟區內部的銷售實施嚴格的管理,對所有進口到歐盟申請正式注冊的中藥必須有相關的應用證明,證明此中藥已經在歐盟成員國應用年限不低于15年以及在其他第三方國的應用年限不低于30年。基于各種現實原因,我國出口的種藥品很難提供這一手續證明。另外,在歐盟的《傳統藥品法案》中還規定:僅包含植物和限定的幾種礦物成分的中藥才能獲批注冊使用,事實上,目前我國出口的中藥不僅包括植物和礦物成分,有些還包括動物等其它多種成分,因此,我國中藥出口企業難以上交符合歐盟所規定的藥品檢驗報告。再者,國外高額的中醫藥注冊費用也使得我國出口企業望而生畏,目前在歐盟注冊一個藥品的費用在100萬元人民幣左右。我國的醫藥企業很難為藥品支付如此高額的注冊費用。所以我國的中醫藥一直以來被絕大部分歐美國家排斥于正規醫學之外,難以被納入醫療保險范圍,只能以替代醫療方式存在,由于中藥長期以來難以迎合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各項藥物甚至是非藥物的標準,從而造成我國中藥難以登陸他國市場的窘況。
三、我國中醫藥出口的建議及對策
(一)政府發揮“燈塔效應”促進中醫藥產品出口
政府主動發揮引導性職能,從宏觀方面的管理、引導和助力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其中應著力解決的問題有:
一要盡快制定和實施中醫藥國家標準,組織各相關方面力量,提高中醫藥產品國際競爭力,一以保證中醫藥質量穩定、可控、有效.安全。
二要盡快建立政府間的磋商協調機制,幫助加快中藥產品市場準入談判,促進各國官方對中藥產品的認可,使中藥盡早進入國際醫藥產品產流市場。
三要扶助科技先導型中藥企業成長,促進現代先進技術與傳統中醫藥的結合。未來國際中醫藥市場的競爭將會是科技與人才的競爭,要使得我國中醫藥產品出口向科技型方向發展,必須改變當前我國中醫藥生產與科研脫節的現狀,鼓勵生產出口型企業建立良好的技術轉化體制,注重提高科研投入效率、培育優良的技術創新力,促進逐步形成以市場發展趨勢為導向、以先進技術為依托、具有良好競爭力的中醫藥產業集團。
四要推動中醫藥走集群化生產的發展道路,提高企業出口競爭力。當前我國國內中醫藥生產行業普遍存在單打獨斗的情況,多數出口國際市場的中醫藥產品由一些小規模、生產集中度較低的企業提供,從國際市場競爭的參與和抗風險的角度來說這種情況是極為被動的。而國際中醫藥市場正處于蓬勃發展的上升時期,中醫藥作為向國際市場進軍的一支騎兵,抓緊機遇、加快發展是不二的選擇。對于具備一定出口規模的中醫藥企業,可以嘗試走聯合、兼并的道路,實現中醫藥產業集中度的迅速提高,從而提高企業總體信貸能力,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
五要重視培養和儲備中醫藥國際化人才資源。人才是實施中醫藥現代化國際化產業行動的關鍵,建立新型的人才培養激勵機制,采取各種有效措施防止中醫藥領域的人才流失,以鼓勵中醫藥的技術創新。
(二)建立中藥現代評價標準體系,打造“綠色中藥”的出口品牌
對中藥產業鏈實行全過程質量控制是中藥現代化最迫切的一項工作之一,中藥的質量控制應該從源頭上抓起,完善從藥品種植(GAP)、中藥材提取、飲片炮制的質量標準,到非臨床及臨床質量規范(GLP,GCP)、生產過程規范(GEP,GMP)以至銷售規范(GSP)的標準化鏈條,同時要開展對國際瀕危動植物的保護、替代性作物。目前我國商務部已經頒布了《藥用植物及制劑進出口綠色行業標準》,而且世界上部分國家和行業團體已經認同此行業標準,尤其像英國草藥供應商協會、新加坡等國對此標準就已經作了充分的肯定。依據相關的行業標準嚴格把生產和出口關,積極申請“綠色達標”認證標志,樹立“綠色中藥”的出口名牌,這些措施都將有利于我國中醫藥出口結構的改善和優化。
(三)加強我國中醫藥企業對知識產權的維護,鼓勵境外專利的申請
我國中醫藥文化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沉淀的寶藏,同時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中醫藥已經成為了中國目前最蘊含中華文化特色、最具有前景的朝陽產業,加強對中醫藥知識產業的保護顯得尤為重要。政府和行業協會應充分發揮指導性作用,及時為中醫藥企業提供世界各國中醫藥專利體系的法律狀態和技術狀態的變化分析報告,幫助企業掌握國外中醫藥專利的第一手資料,鼓勵中醫藥企業走國際化道路的同時積極在境外申請專利,維護我國中醫藥出口商品的核心技術。另外,我國中藥企業應制定嚴格的知識產權管理制度,組建一支專門的知識產權管理工作人員隊伍、建立專門知識產權機構,對管理知識產權相關事宜進行專門管理,提高相關事宜應對的效率。
(四)弘揚中醫文化,通過中醫中藥捆綁出口方式,走“以醫帶藥”道路
區別于西醫以藥為依賴對象的特點,中醫更講究醫藥不分家的原則,因此,中醫不僅在醫學理論體系方面體現明顯的整體性,而且在臨床診治和保健方面同樣體現防治一體的特點。我國中藥欲走國際化發展道路,在加強中醫的文化國際傳播的基礎上,必須通過“以醫帶藥”的模式,促進其在國際市場上取得長足的發展。首先,可嘗試性在一些文化交流基礎較好的國家興辦示范性中醫院和診所或中醫診療咨詢中心,以期加強中醫藥療效的宣傳推廣,改變當前中醫藥勞務出口較為分散的局面;其次,大力興辦境外中醫藥學校,以美國、澳大利亞、德國等國為重點,推行正規的中醫教學,培養國外的“親中醫藥派”,改善國外嚴重缺乏專業且有經驗的中醫藥人才的狀況,為中醫藥在海外實現本土化打下基礎;最后,鼓勵中藥企業走“以醫帶藥”道路,借鑒三九、同仁堂等國內知名中藥企業的海外營銷經驗,探索出一條切實可行的“名醫”、“名藥”相結合的經營模式。
(五)開拓新型中醫服務貿易方式帶動中醫藥出口
中醫藥不應該是只是一種產品,更應該是一種服務。中醫服務乃是中藥市場拓展的重要條件,只有對兩者的同時推進,中醫藥才能在世界醫學領域中真正發出璀璨的光芒。中醫服務的滯后狀態,必定制約中藥產品走向國際市場的進程。世界貿易組織的《技術貿易壁壘協定》(TBT)是世界貿易組織對技術的跨境傳播的原則性規定,但其中不包括醫療技術,世界貿易組織的任何規定都沒有對醫療技術的流動做出限制,從服務貿易的角度來看,我國可以提供中醫藥服務的產品是十分豐富的。我國中醫學內容博大精深,基于豐富的中醫學理論,經歷幾千年的臨床經驗積累,已經發展形成了疾病預防、醫療養生保健等服務人類健康的種類繁多的系列產品,象針灸、中藥旅游、中醫美容以及藥膳更是多種多樣等待著我們的深入挖掘,這些中醫藥服務方式的開拓將會為我國的中醫藥在世界上帶來光輝的前景。▲
[1]馮國忠,唐慧鑫,馬愛霞.我國中藥出口形勢及對策分析[J].中國中醫藥信息雜志,2001.11:2-3
[2]李潔:中藥出口如何跨越貿易壁壘[J].經貿縱橫,2005(7):1-3
[3]張京衛:中藥企業國際化經營障礙及對策研究 [J].商場現代化,2005.10:151-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