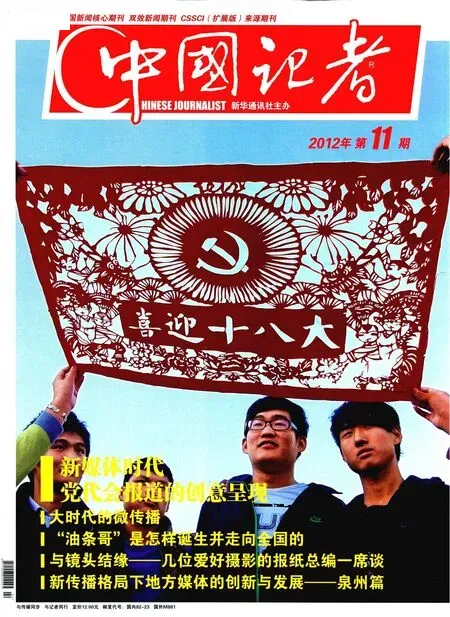報人:要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新聞攝影門外談
□ 文/張宗善
(作者是《菏澤日報》總編輯)
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由不同的人拍出的照片為何迥異其趣?為什么別人能夠發現的美我卻不能發現?是什么遮蔽了我們發現美的眼睛?怎樣才能發現美并把美的發現傳遞給他人?
莫言大熱!
因對“高密東北鄉”這片土地獨特而非凡的言說,莫言榮膺諾獎桂冠,隨之引發的轟動,一時間無人可比。大熱的不僅是他的作品,而且還有他和他的家鄉——山東高密東北鄉。現實中的東北鄉人聲鼎沸、百態聚集。高密與中國再次契合,正如莫言自己所說:我努力地要使它(高密東北鄉)成為中國的縮影。
場景、畫面——每個讀過莫言作品的人,不管他是否到過高密東北鄉,都會在腦海中呈現出這些畫面:河堤上講故事的老人,糾結于現實與內心的各色人等,隨風搖曳、一望無際的紅高粱,忍饑挨餓、生命力頑強、生長緩慢的鄉村——請注意,這里的每一句話,都能幻化成一幅活靈活現的圖畫。而所謂記憶,不就是一幅幅的圖畫嗎!
一張好的新聞圖片往往引起受眾的廣泛共鳴。在報紙版面上,即便是一幅一般化的新聞圖片,也比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更能吸引眼球。
美的影像給人“正能量”
鏡頭陪伴我已經有20多年了——這里我不說相機而說鏡頭,是因為我覺得鏡頭更能引發思考和發現——很慚愧,在攝影方面我碌碌無為,但我對攝影的喜愛、鏡頭帶給我的思考和啟迪卻并未因“無為”而減弱。
印象最深的是2011年的深秋,我隨全國晚報總編輯看新疆采訪團到南疆采風,此行給我的視覺沖擊和心靈震撼至今不曾削減。當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那雄偉壯美的身姿突然出現在我眼前,當我置身于塔克拉瑪干大沙漠中那一望無際的胡楊林,當我在烏魯木齊、喀什、和田、庫爾勒等地耳聞目睹各民族團結共譜發展曲——我被眼前的美震撼了,一時竟目不暇接、手足無措。這時,我才知道了什么叫“直擊心靈”!
雄偉的雪山,圣潔的湖泊,無際的大漠,醉人的綠洲,不屈的胡楊,民族團結和諧相處共謀發展的大好局面——這些“大美”被我一一攝入鏡頭。回憶起來,那時每一次按下快門,手都在抖動,心都在快跳!回來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沉浸其中,再看別的山水景致,竟毫無意趣。
有一種美不可言狀,有一種感受難以描述。跋涉于新疆大地,人們往往驚嘆:荒涼與豐饒,死寂與生機、淳樸與繁麗,傳統與現代是那么和諧、完美地組合在一起。這里,看不到人們瘋狂膨脹的欲望,看不到向大自然無休止索取的匆忙背影。這里,不染一絲紅塵,這份純凈的美讓人陶醉,讓人沉迷。
心中有美,眼里才有美
紅的熱烈,綠的蓬勃,白的素凈,黃的成熟,黑的凝重——美,真的無處不在。不論你見與不見,美就在那里。由此引發的問題是: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由不同的人拍出的照片為何迥異其趣?為什么別人能夠發現的美我卻不能發現?是什么遮蔽了我們發現美的眼睛?
審美能力是一種認識美、發現美、感受美、創造美的綜合能力。美是客觀存在的,但許多人身在“美”中不知“美”,其原因就在于他缺少發現美的能力。審美能力需要在不斷地認識、體驗、感受美的過程中積累。

□《靜謐》(張宗善/攝)
美是什么?美其實就是我們內心的投射。審美有客觀標準,但其最顯著的特性是巨大的個體差異。同一個人、同一件事、同一個客觀事物,人們的審美感受有可能大相徑庭,甚至有可能截然相反。
同樣一個鏡頭,同樣的拍攝環境,有的拍出的照片厚重深沉、美輪美奐,有的卻干干巴巴、乏善可陳。這是為什么?一個人的經歷、素養、學識、世界觀以及此時此刻的狀態,都會決定著客觀事物對他的觸動程度、角度和力度。因此,當你拿起相機,將鏡頭對準生活的時候,可能最需要的還不是技術技巧層面的東西!打球講究球感,游泳講究水感,攝影講究的是鏡頭感。鏡頭感更多地源于內心,所謂觸景生情,只有內在的情與外在的景在你內心的作用下契合的時候,才能生出你獨有的情。
按下快門僅需手指輕輕一動,零點幾秒即可完成,但要成就一幅優秀的攝影作品,就需要長期的積累和歷練。不是說技巧不重要,相反,技巧很重要。但僅有技巧是絕對不夠的,就像書法家與書寫匠,二者永遠是天壤之別。
技巧,永遠服務于主題;外在,永遠是內在的體現。就攝影而言,構圖、色彩、形狀、線條屬于外在的形式,而透過鏡頭觀察到的內容,則需要我們用心思索,選擇合適的形式予以表現。
有好眼光才有好圖片,發現美的眼光如何練就?這個問題不在這篇短文探討的范圍之內。不過,在物欲橫流的現代社會,很多人被世俗觀念、滾滾紅塵迷了眼,失去了發現美、創造美、欣賞美的能力,非常令人惋惜。
記得有人說過:“我的鏡頭會說話。”
的確,言為心聲,修心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