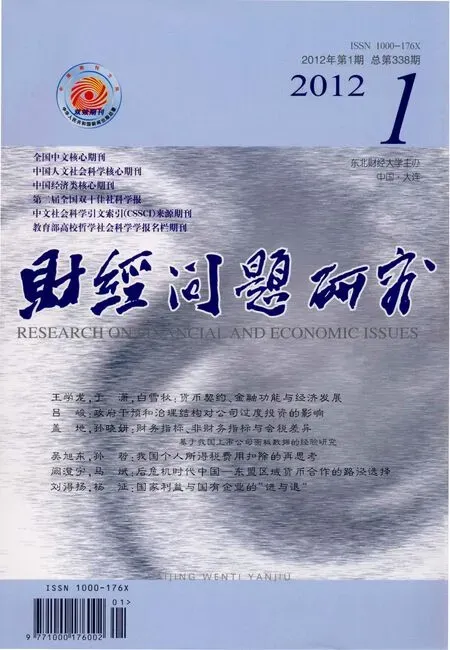透視我國高房價: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視角
范方志,高大偉,周 劍
(1.貴州財經學院 經濟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4;2.上海海洋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上海 201306)
一、引 言
自2003年開始,我國房價開始快速上漲,高居不下的房價也引起了政府的重視,不斷出臺調控措施。但是讓人們出乎意料的是,在多年的調控下,房價依然扶搖直上。諸多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的高房價進行了研究。有的從信貸角度分析,認為我國銀行信貸量與房地產價格變動正相關,同時房地產價格變動對銀行信貸也具有重要影響;有的從需求角度分析,認為需求的提高可能會帶動房地產價格的大幅提高,嚴重時就可能引起房地產市場的泡沫;也有人認為供給不足或結構性短缺也會造成房價的上揚。學者們提出了許多導致房地產價格上漲的因素,并對由此引發的嚴重后果表示擔憂。但是這些分析或者是只涉及個別因素,或者是缺乏有機聯系地羅列了多種因素。
我們認為,應該在一個理論框架下系統地分析中國房地產價格,更能夠清晰地認識房地產市場發展現狀及其不良后果。馬克思的地租理論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分析工具。
二、文獻綜述
對于中國目前的高房價現象,中外學者的研究有很多,這些文獻在研究方法、研究視角和研究結論等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曾漢生從國際貿易的角度加以分析,認為長期的貿易順差、人民幣匯率升值等因素導致了我國貨幣超發,引發投資過熱,也是高房價的重要原因。他認為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降低經濟增長的出口和投資依賴才能徹底解決高房價問題[1]。張夢實劃分了四大類引致高房價的原因:政府方面的原因、房地產企業方面的原因、需求方面的原因和外部原因。他認為政府方面的因素包括土地財政的依賴、對房地產的金融支持、保障房建設不足等;房地產企業方面的因素包括競爭不充分、稅費較多等;需求方面主要有城市化需求、投機需求等;外部因素包括人民幣升值預期等[2]。汪麗娜特別強調了高房價背后的制度缺失問題,她分析了我國的土地供給制度、住宅供應制度和住宅金融體制的不完善之處,認為必須從多方面入手進行制度建設,才能有效解決高房價的問題[3]。王弟海采取了一個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來分析高房價現象,并分析了高房價的宏觀經濟效應,他提出的政策建議是調控目標設為穩中有降、貨幣與財政政策等多種政策同時使用、消除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4]。國外對我國高房價現象的研究更傾向于實證分析,Wu等分析了中國主要的房地產市場,研究發現,房價上漲與收入上漲沒有什么特定聯系,近些年房價上漲的主要部分是土地價格的上漲,而且央企在最近幾年的土地轉讓市場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5]。Chen等分析了住房需求彈性,并以深圳市福田區和龍崗區的數據做了驗證,研究認為隨著住房單位的擴大,需求彈性也會增強[6]。Chen等回顧了1995—2005年10年間的城市住房制度變革,他們認為政府應該吸取這10年制度改革的經驗和教訓,特別是要重視高房價對人口遷移和城市化的影響[7]。Du等分析了土地政策對地價和房價關系的影響,他們發現在土地市場和住房市場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檢驗發現高房價是高地價的原因。但在2004年之后,土地市場和房產市場對沖擊的反應都比以前要慢一些[8]。國外其他還有一些針對中國房地產市場做的研究,大體上都是從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進行實證研究,并沒有直接提出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國內的研究文獻偏重于提出解決高房價問題的政策建議,國外的研究文獻則側重于研究高房價現象的量化特征和實際情況,這些都可以作為政策制定的基礎。但是,這些文獻的一個弱點是都沒有一個完整的理論框架來分析中國的高房價問題。本文就是要以馬克思的地租理論為基礎,建立一個理論框架,并在這個框架的基礎上分析高房價的一系列問題。
三、馬克思地租理論模型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非常清晰地表述了地租理論,而且對建筑地段的地租有專門的敘述。本文忠實地按照馬克思原著的敘述,用數理形式簡潔概括了馬克思地租理論的整體架構和基本原理,對于個別細節沒有過多的涉及。
1.理論前提
理解馬克思的地租理論,必須先說明一些前提性的概念和假設。
第一,地價和地租的關系。馬克思明確指出“資本化的地租表現為土地價格或土地價值……,土地價格無非是出租土地的資本化的收入”[9]。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地租的高低與地價的高低是一致的。根據《資本論》第三卷的敘述,“在英國,土地所有者把絕大部分用于建筑的土地不是作為自由地出賣,而是按九十九年的期限出租,或者在可能時,按較短的期限出租”[9]。這與我國住房僅有70年產權的制度有相似之處。
第二,市場化的界定。馬克思分析的地租是市場化的地租,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寫道:“我們假定,農業和工業完全一樣都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統治……”[9],這就意味著,農業和工業都是市場化的。“因此,它的下列條件,如資本的自由競爭、資本由一個生產部門轉入另一個生產部門的可能性、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潤,等等,都已經十分成熟”[9]。就是說,資本可以自由進出該行業,行業中的企業只能獲得平均利潤。這是一個很強的競爭性市場假定。
第三,馬克思特別指出研究地租的三個重要錯誤:“1、把適應于社會生產過程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地租形式混同起來。不論地租有什么獨特形式,它的一切類型有一個共同點: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權借以實現的經濟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權,以某些個人對某些地塊的所有權為前提。……最后,它還可以是這樣一種對土地的關系,這種關系,就像在殖民地移民和小農土地所有者的場合那樣,在勞動孤立進行和勞動的社會性不發展的情況下,直接表現為直接生產者對一定土地的產品的占有和生產。……2、一切地租都是剩余價值,是剩余勞動的產物。……3、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的獲得者決定的,而是由他沒有參與、和他無關的社會勞動的發展決定的”[9]。這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社會生產過程不同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的地租形式,中國當前的社會發展特征必然也會有自身獨特的地租形式,但是仍然逃不出地租的共同點,馬克思的地租理論依然適用;地租的量從而土地價格是由社會勞動發展決定的,不是由地租獲得者決定的。這些觀點具有重要意義。
2.基礎模型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已經非常清晰地給出了地租理論的模型,我們要做的工作,只是把模型的脈絡再梳理簡化一下,必要的地方加以銜接,并用現代經濟的方式表達出來。
馬克思說,“如果我們把一般的調節市場的生產價格叫做P,那么,P是和最壞土地A的產品的個別生產價格相一致的;也就是說,這種價格將補償生產中消耗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加上平均利潤 (=企業主收入加上利息)”[9]。由此,我們得到:

其中,P是調節市場的生產價格,K和L分別代表生產過程中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
馬克思認為“較好一級土地B的個別生產價格=P',而P'>P,也就是說,P可以補償B級土地的產品的現實價格而有余。現在假定PP'=d;因而d,即P超過P'的余額,就是B級土地的租地農場主所獲得的超額利潤。這個d轉化為必須支付給土地所有者的地租”[9]。
這樣,我們得到:

其中,R就是極差地租。
馬克思進一步分析,“現在,我們假定,對A級土地來說,地租=0,因而產品的價格=P+0這個前提是錯誤的。相反,A級土地也會提供地租=r。這時,我們就會得出以下兩個結論:
第一,A級土地產品的價格,不是由它的生產價格來調節,而包含著一個超過它的生產價格的余額,即=P+r。
但是第二,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土地產品的一般價格會發生本質的變化,但級差地租的規律絕不會因此就失去作用。既然A級土地的產品的價格,從而一般市場價格=P+r,那么B、C、D等各級土地的產品價格,也同樣是P+r”[9]。
P+r是有一個經濟限度的,“舊租地上的追加投資,外國的土地產品——假定土地產品可以自由進出口——的競爭,土地所有者之間的互相競爭,最后,消費者的需求和支付能力……”都是限制。
所以,我們得到價格的最高限制為:

其中,k是舊租地上的追加投資,q是同類產品的競爭,h是土地所有者之間的競爭,c是消費者的需求和支付能力。r就是絕對地租。
這個公式十分有用,現實中表現出來的諸多現象都可以在這里找到解釋,并且能夠清晰地說明各因素在價格形成中的性質和作用。
3.馬克思的建筑地段的地租理論
馬克思在論述建筑地段的地租時,指出:“首先是位置對級差地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其次是所有者的明顯的完全的被動性,他的主動性只在于利用社會發展的進步……;最后,是壟斷價格在許多情況下的優勢,特別是對貧民進行最無恥的剝削方面的優勢……”[9]。
馬克思強調,“土地所有權本來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剝削土地,剝削地下資源,剝削空氣,從而剝削生命的維持和發展的權利。……空間是一切生產和一切人類活動所需要的要素”[9]。
這樣,建筑地段的地租價格上限就擴展了,因為價格還包括“生命的維持和發展的權利”這一要素:

其中,z是指一個社會中人們謀求維持和發展自身的某些權利。
可以說,馬克思論述建筑地段地租時,明確指出人們謀求“維持和發展的權利”與房地產捆綁起來之后,壟斷價格對人們的危害性。這一點對當代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具有很強的解釋力。
四、運用馬克思地租理論模型分析中國當前房地產市場
將馬克思的地租模型運用于中國當前的房地產市場,能夠在一個框架之下系統地解釋當前一些重要的熱點問題,并為下一步的政策實施提供有益的啟示。
1.地方政府賣地行為
根據財政部公布的數據,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為14 239.7億元,比上年增長43.2%。占到中央政府和全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總額的兩成。其中,上海市2009年的土地出讓收入突破1 000億元,占當地財政收入的比率高達四成,政府和民眾部越來越依賴房地產行業。
地方政府因為20世紀90年代的稅制改革,將大部分財政收入移交給了中央政府。由于稅收減少,地方政府普遍采用出讓土地來彌補減少的稅收,然后將土地出讓收入用于城市開發,最后再將開發的用地出售給房地產商。2009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中,用于補償搬遷居民的比率僅為40.4%,大部分被用于了新城市開發投資。由于今后再開發地區的居民會要求更多的補償金,因此這又會成為推動房地產價格上漲的誘因。
地方政府有動力抬高地價,那么它的能力來自哪里?地方政府的行為在整個房地產體系中處于什么地位?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利用馬克思的地租理論模型:

上式中的價格P是市場化條件下的取得平均利潤的市場價格,首先競爭性的市場這一個條件,我們就達不到,目前的土地制度決定了只有當地政府才有權利批準并出讓土地用于建筑用途,這就意味著公式右邊的影響因素中,h反映的競爭程度幾乎是零,不會有兩個地方政府存在。僅這一條件,就使得價格要遠遠超過競爭性市場條件下的價格P。
再者,r的出現,意味著壟斷力量可以收取絕對地租,而絕對地租與相對地租在性質上是完全不相同的,絕對地租與土地差異無關,只與壟斷力量有關。并且,一旦形成,絕對地租就成為調節一切地價的一般價格的組成部分。
可見,這是最基礎的價格決定因素。在達到經濟限度之前,這個因素所決定的價格就是市場上所有土地的參照價格了。這個參照價格不改變,房地產價格的根基就不會動搖。
2.房地產價格與消費者支付能力的分析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發達國家的房價收入比一般在1.8—5.5倍之間,發展中國家合理的房價收入比在3—6倍之間,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2010年4月21日在北京公開表示,目前中國房價收入比已超過15倍,上海、北京和廣州等地的房價收入比則超過50倍以上,泡沫現象嚴重。房地產泡沫已成為事關中國國民經濟全局的系統性風險。
盡管房價收入比是一個國際公認的指標,但是在馬克思地租理論模型中,僅僅是房價影響因素之一,如果不結合其他因素來綜合考慮,僅從這一個指標看,不會得到準確的結論。因為在公式 (5)中,除了消費和支付能力c,每個國家在k、q、h、z四個方面是有差異的,并且很可能差異極大。
所以,僅僅通過房價收入比這一個指標判斷房價泡沫很嚴重,是不科學的。
3.高房價與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問題
反對高房價的一種觀點是,房價高昂損害了其他產業的發展。而與之針鋒相對的觀點是房地產行業拉動了其他產業的發展。
在馬克思地租理論的框架下,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這個問題:首先,馬克思指出,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的獲得者決定的,而是由他沒有參與、和他無關的社會勞動的發展決定的。就是說,其他產業的發展是房地產能夠實現高價的一個基礎。從模型看,公式 (5)可以進一步細化為:

其中,y表示收入水平。這就意味著,消費能力取決于收入,但是收入來源于其他產業,其他產業越發展,可用于購買房地產的收入就越多。而房價的上漲,也受制于其他產業的發展。
準確地說,房地產業與其他產業發展的關系,應該這樣來描述:在資源總量不變的條件下,高房價會吸引更多的資源進入房地產業,其他產業得到的資源就相對減少了,因此,這種情況下,其他產業的發展就受到了損害;在經濟增長情況良好時,其他產業的發展為房地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4.房價與生存和發展權利的關系問題
一個讓人困惑的問題是,在大家都認為房價過高的情況下,房價依然能夠持續上漲這么久,是否有其合理的因素呢?答案是有。
那就是公式 (5)右邊的z因素。在中國,房價并不僅僅是居住的功能,它與很多“維持和發展的權利”捆綁在一起。人們熟悉的學區房、購房入戶、婚房等等,都是把某些發展的權利與住房捆綁起來了。當人們購買一套住房時,買到的不僅僅是居住的功能,很可能包含著入學、戶口等多種社會功能,而這些社會功能是許多人不可或缺的,僅僅這些附著的社會功能的價值就可能遠遠超過房子純粹的居住功能。換句話說,人們買的不僅僅是住房,還有“維持和發展的權利”。
這一個因素在不同的國家、城市有很大的區別。比如,按照國際上的房價收入比指標來判斷,很可能一個有“泡沫”的房價,反而是低估的,因為,國際標準并沒有考慮“維持和發展的權利”這一部分價格。表面看來的“虛高”房價很可能是有“權利”價值做支撐的。
從另一方面來看,高昂的價格剝奪了很多人“維持和發展的權利”,這些權利本不應該標價出售的,但是通過與住房捆綁在一起,它們被“市場化”了,“價高者得”的市場原則使得窮人喪失了應有的權利。
5.房地產價格與金融支持
即使考慮“維持和發展的權利”所支撐的那部分價格,現有的房價很可能也是過高了。造成這種情形的一個重要條件是金融的支持。無論房價包括什么內容,沒有金融支持,人們的收入就是房價上漲的一個重要限制。而信用,突破了這個限制。
由于金融支持的作用,公式 (5)中的c似乎沒有影響了。房價可以不受消費者收入的限制,而只受信用條件的限制了。一旦脫離收入和消費的范疇,房地產也就不再是消費品,而是進入到金融資產領域了。它的價格將受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規律所支配了。
政府、學者和公眾都十分關注金融政策的變化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但是,只有馬克思的地租理論能夠清晰地指出,金融支持是怎樣打破界限,使得住房由消費領域進入資產領域的。這對于房地產政策的制定具有積極意義。
6.房地產價格的上限與調控措施分析
房地產價格的調控是近幾年政府和民眾關注的事情,但是調控的效果不能令人滿意。從馬克思的地租理論來看。要使得房地產價格不再過高,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使住房從資本品市場回歸到消費品市場。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用的辦法是將市場分割,一部分住房是消費品市場;一部分住房是資本品市場。作為消費品的住房不應成為謀利的工具,這是基本原則。
第二,逐步將“維持和發展的權利”與住房脫離。讓房價僅僅反映住房的價格,而不是“一系列權利”的打包價。
第三,改革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和土地制度,杜絕收取絕對地租權利的濫用。
五、簡要的結論
馬克思的地租理論簡潔而含義豐富。本文僅僅是粗略地將其模型化,這個模型還可以進一步細化,反映出更細致的理論意義。這一模型容納了政府行為、消費者行為、產業行為和金融行為于一體,結合我國當前房地產市場的諸多現實問題,能夠將許多看似雜亂無章的觀點兼容并蓄,而且合乎邏輯地表明各因素的作用,是一個很有生命力的綜合性模型。當然,由于我們并沒有進一步細化該模型,對相關問題的細致分析也只能留到將來完成。
[1]曾漢生.從長期貿易順差看我國貨幣泡沫化、通脹及高房價癥結[J]. 湖北社會科學,2011,(6):94-97.
[2]張夢實.淺談當前高房價的影響因素與政府調控措施[J]. 地方財政研究,2011,(2):25-27.
[3]汪麗娜.高房價背后的制度缺失[J].北京社會科學,2010,(2):65-70.
[4]王弟海.透視我國的高房價:一般均衡分析的視角[J]. 浙江社會科學,2010,(3):13-16.
[5]Wu,J.Gyourko,J.,Deng,Y.H.Evaluating Conditions in Major Chinese Housing Markets[R].NBER Working Paper No.16189,2010.
[6]Chen,Y.,John,M.C.,Tirtiroglu,D.Hedonic Estimation of Housing Demand Elasticity with a Markup over Marginal Costs[J].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2011,20(7):233-248.
[7]Chen,J.,Guo,F.,Wu,Y.One Decade of Urban Housing Reform in China:Urban Housing Price Dynamics and the Role of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1995—2005[J].Habitat International,2011,35(1):1-8.
[8]Du,H.,Ma,Y.K.,An,Y.B.The Impact of Land Polic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Housing and Land Prices:Evidence from China[J].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11,51(1):19-27.
[9]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04-705,694,693,714-715,843,844,872.